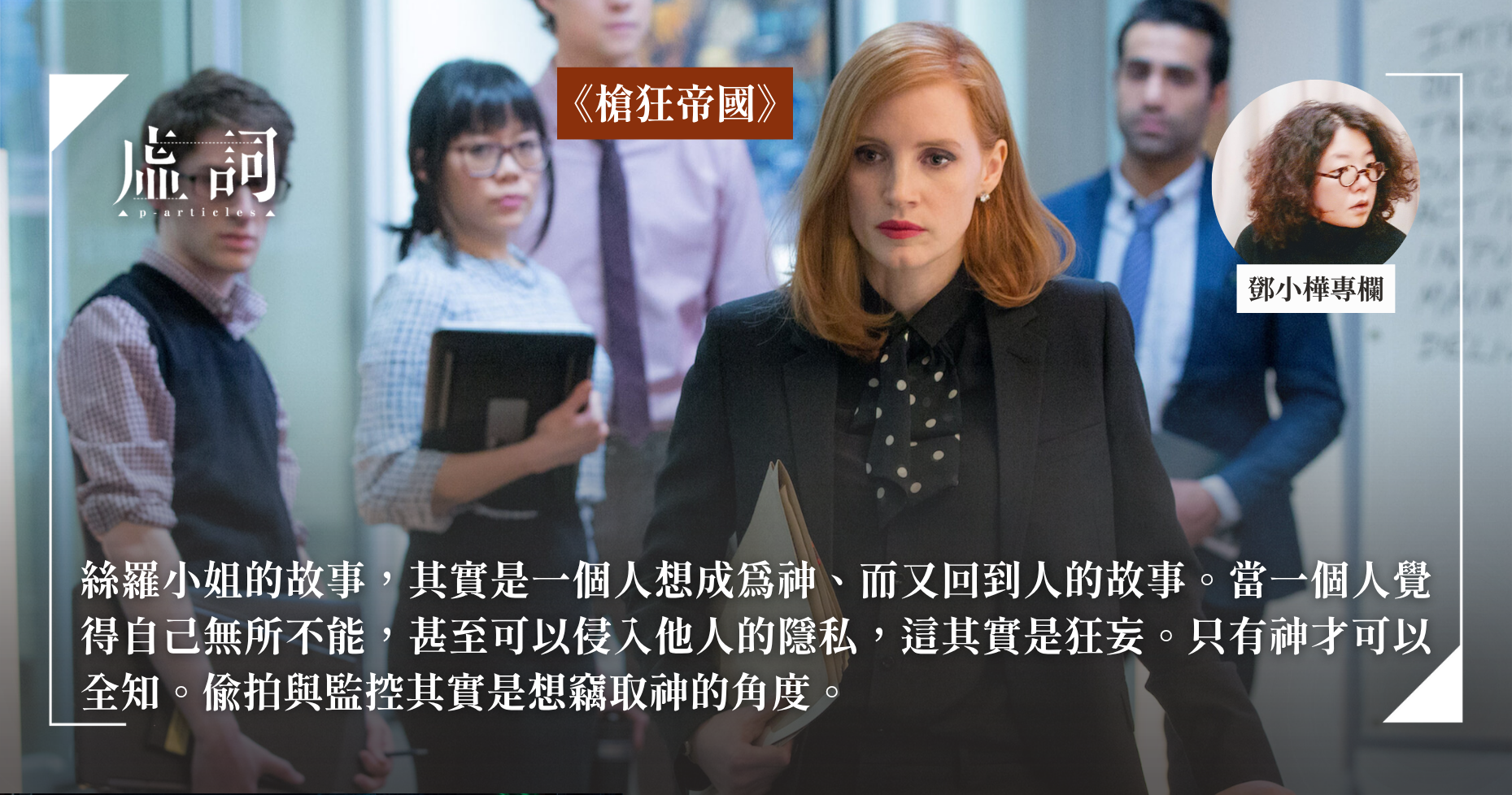鄧小樺在失眠之時,想起電影《槍狂帝國》中的絲羅小姐,一位永遠無法入睡的美國政壇說客。絲羅小姐縱橫政壇、機關算盡、強勢狠辣,仍堅守反對槍械法案的核心原則,並以自身獲罪為代價,完成一場由「神」回歸到「人」的悲劇英雄式救贖,尤令鄧小樺大受感動。鄧小樺認為絲羅小姐一角象徵狂妄的代價與高尚的定義——非為金錢而行,儘管現實中難以效仿,失眠卻拉近了兩人之間的距離。 (閱讀更多)
【邁克專欄:拍子簿】楊德昌筆記
楊德昌《一一》修復版大銀幕重映,在港在台都是盛事,而開口就敢直言不喜歡《一一》的,大概也只有邁克一人。夠膽奄尖聲悶,無非因為是資深楊粉。本文仍然需要看到最後一句。 (閱讀更多)
【鄧小樺專欄:閃爍其辭】作為遊客,美麗與哀愁
鄧小樺四月回港,正值木棉與苦楝盛放,卻只能隔著車窗遠遠嘆息。她以「遊客」身份多次回港,只為不錯過黎海寧、梅卓燕等香港重量級藝術家的表演。鄧小樺在的士與街景間感受香港的美,也聽見市井的冷語。由港人變成遊客身份,使小樺昔日批判的眼光漸遠,取而代之的是無法抑制的讚歎與哀愁,那對香港既熟悉又陌生的矛盾情感,竟是如此複雜。 (閱讀更多)
【邁克專欄:拍子簿】小巫、大巫及其它
邁克又寫張愛玲,由最新評論數到最原初版本,說是遊戲文章又太認真,說是認真文章又實在翻了太多層——怪論翩翩建基於火眼金睛版本比對之上,教人笑又唔係喊又唔係——老規矩,看到最後一句,再回味咀噣其飄忽,太早下判斷是丟自己的臉。 (閱讀更多)
【邁克專欄:拍子簿】羅馬假期筆記
邁克羅馬散步學,跟著經典去旅行,柯德莉夏萍費里尼安東尼奧尼諸如此種不在話下,連骨骸博物館都要嘴賤一番,真係chill 到爆炫耀文無誤——但邁克文章你真係要睇到最後一句。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