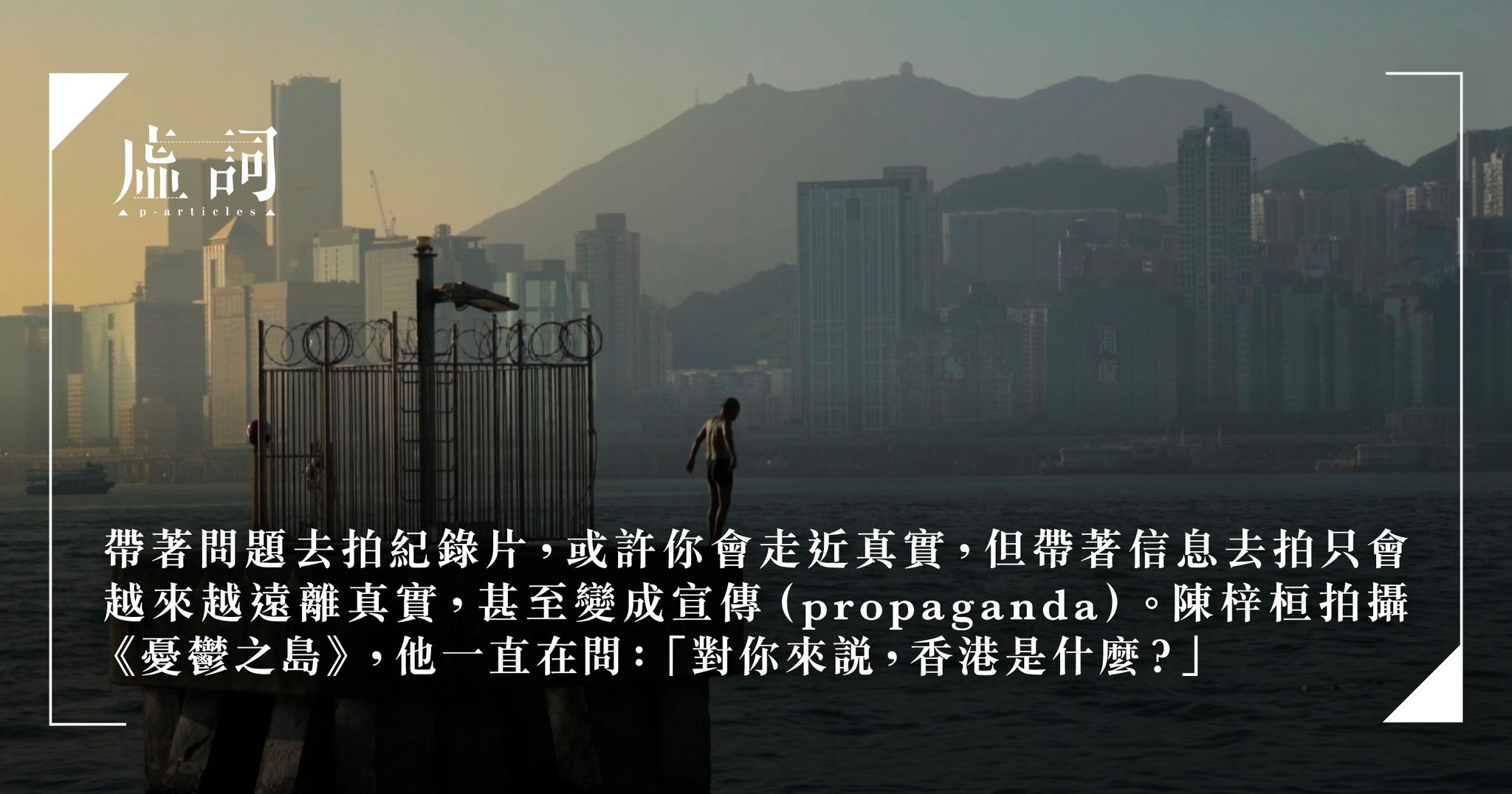從《憂鬱之島》的爭議,談紀錄片敘事上的真實與虛擬
紀錄片旨在提出問題,不在於提供答案。我一直是這樣提醒自己。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談及紀錄片,也有相近的說法而且更具體。她說,帶著問題去拍紀錄片,或許你會走近真實,但帶著信息去拍只會越來越遠離真實,甚至變成宣傳(propaganda)。陳梓桓拍攝《憂鬱之島》,他一直在問:「對你來說,香港是什麼?」
他曾經拍過《亂世備忘》,跟拍幾位年輕人參與2014年「佔中」。紀錄片手法很主流,用了不計時數的精力,以觀察式的拍攝(observational mode),跟著他們經歷了一場社會運動,以過百小時計的片量,剪成一個長片故事。今次拍《憂鬱之島》,他選了一條艱難而富爭議性的路,以重演方式(reenactment)去拍一套關於香港的紀實電影。
重演這種手法具爭議,是因為在紀錄片的敍事上會容易混淆真實與虛擬,亦會被質疑會否過分演繹。跟恩師蕭景路在製作紀錄片的那些年,我們常會討論這種手法。這種手法不新,1988年Errol Morris 的《The Thin Blue Line》已淋漓盡致地運用過,故事層層拆解一個殺警死囚是否無辜和誤判的過程。當我們在某些關要事件沒法取得視像片段時,我們會重演,讓觀者能代入情景,補遺說故事上的需要,例如一些年代久遠的歷史事件,又或者像《The Thin blue line》 裡的殺警情景。她常常提醒,真實與虛擬之間這條線矇糊了會帶來爭議,要小心處理。在電視平台上製作紀錄片多年,我們都選擇用明顯的處理方法,在片段上加上「模擬片段」字句,以示識別。這在電視上似乎是合理選擇,因為電視機旁的觀眾不一定「坐定定睇」,容易分神。但轉一個情景,在漆黑的電影院觀看,而且是長片,處理手法就變得多元。觀眾在經歷真實與虛擬的觀映過程中,靠近真實。Errol 在一篇訪談中明確地說,如果觀眾看後有這種「這就是真相嗎?」的疑惑,這就是他們製作團隊想分享的經歷:「什麼是真相?」
我仍然記得十年前在電影節看完《The Act of Killing》 之後的震撼,它拓闊了我對重演手法( reenactment) 的想像。影片的時代背景,是關於印尼1965年政客以反共和保護國家之名發動流氓殺人如麻的政治風暴。監製正是 Errol Morris,而導演Jushua Oppenheimer找來當時的殺人魔頭假戲真做,重演當時的情景,同時亦如實紀錄荒誕的拍戲現場。在虛擬與真實之間徘徊,亦真亦假,有實有虛,影片最後竟然穿透那個已經「做人阿爺」的頭目,他暗黑的內心世界。我知道映後有評論,批評影片欠缺對這血腥事件的來龍去脈給出一個交代 ,我同意,但那會是另一個製作。導演透過這影片要問的是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影片結尾的場面是在曾殺人無數的天台上,殺人魔頭忍不住嘔吐大作,但什麼也吐不出來!這情景令人極度不安: 「那是他的良心在折磨他嗎?他還有嗎?」步出電影院,這問題一直縈繞。
回說《憂鬱之島》以重演作為影片的主要敍事,透過經歷67暴動,8964, 2014佔中以及2019 反修例運動的人物去尋找答案:「對你來說,香港是什麼?」
若然一定要「秤一秤」篇幅來判定有沒有偏向一角或有不可告人的意圖,整體來說各事件所佔時間大致相若,這樣做其實沒有多大意義。反而我想說,以全片九十多分鐘,是不可能把每件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包羅萬有,況且這些事件只是影片的語境(context),人的狀態才是製作人所關心的重點。拍了紀錄片多年,我常常提醒自己如果觀眾看完片,只是記得導演,而對片中人物沒有印象,那是失敗。
《憂鬱之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位不管風雨、每朝清晨在海旁游泳的伯伯。年過七十仍然強壯的他,當年逃避文革「游水落香港」。片中,他話不多,在大型遊行中,會見到他默默無言的身影。唯一說的話就是在導演安排下重演文革批鬥大會的那場。他簡單直接地說,這演繹不真實,當時他身歷其境,參與的人沒有那麼激昂。陳梓桓把這句說話放進片中,是要提醒觀眾虛擬片段與真實是有距離的,他戲劇化了,這也是導演真誠面對自己作品的表現。我認識梓桓,當時他仍是電影碩士生,也是蕭景路紀錄片課的學生,我相信他完全明白蕭老師所說的虛實爭議。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人物是2014年參與佔中而被告上法庭和判刑的鍾耀華,片中所佔篇幅僅數分鐘。他在一個模擬法庭,重演他為自己陳詞的片段。香港法庭是不准錄音錄影,重演變得必然。他情緒激動地一字一句地念,忍不住流下眼淚。場面是虛擬,但那是真實的眼淚,看著這個片段,我流的也是。
還有一個印象深刻的場面,就是那場引起爭議的監獄對話。一方是2019年因為反修例運動而坐監的年輕抗爭者,另一方是參與過67暴動、當年也是年輕監犯的楊宇傑(別名:石中英)。這是一個明顯的虛擬場景,讓人屏息的是觀眾清楚知道雙方真正身份,在這場景下,他們會怎樣互動?這樣的刻意安排,我的理解是因為他們同樣坐過監,還有的就是他們政治取向上的南轅北轍,作為一個製作人我不傾向過份解讀。石中英是一個很會掩飾自己的人,狡猾而老練。認識他多年的長毛梁國雄在之前一個片段,輕輕地一語道破:「他不敢喝酒,喝了怕說出真話。」這樣的對話令人會心微笑。當穿上囚衣的石中英發現眼前這位也是身穿囚衣的少年他的真正身份,他馬上堆出一臉關心,又洋洋灑灑地說了一大堆連自己也騙上的假作真時真亦假的說話。我內心是一陣厭惡,也有不安。那個年輕人會被他騙到嗎?影片沒有提供答案。我帶著這種疑惑,想得更多的是歷史這回事:誰掌握歷史,誰操控未來。我們現在天天活在這危機當中,亦處於下風。過去一年多,陸續有不同的劇情片和紀實電影,為時代留下註腳。這些作品難能可貴,在低氣壓下讓人稍稍釋懷。
《憂鬱之島》是一個真誠的作品,但它不容於今日的香港,估計在一段更長的日子也沒法在香港正式上映,讓更多人參與映後討論,以至去問:「對你來說,香港是什麼?」如果你有幸能在外地進戲院看,豈能錯過?看過了,褒貶隨意,也自由表達。權力無處不在,抗衡也應如此。
〈標題為編輯所擬,原文轉載自「眾聲號」專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