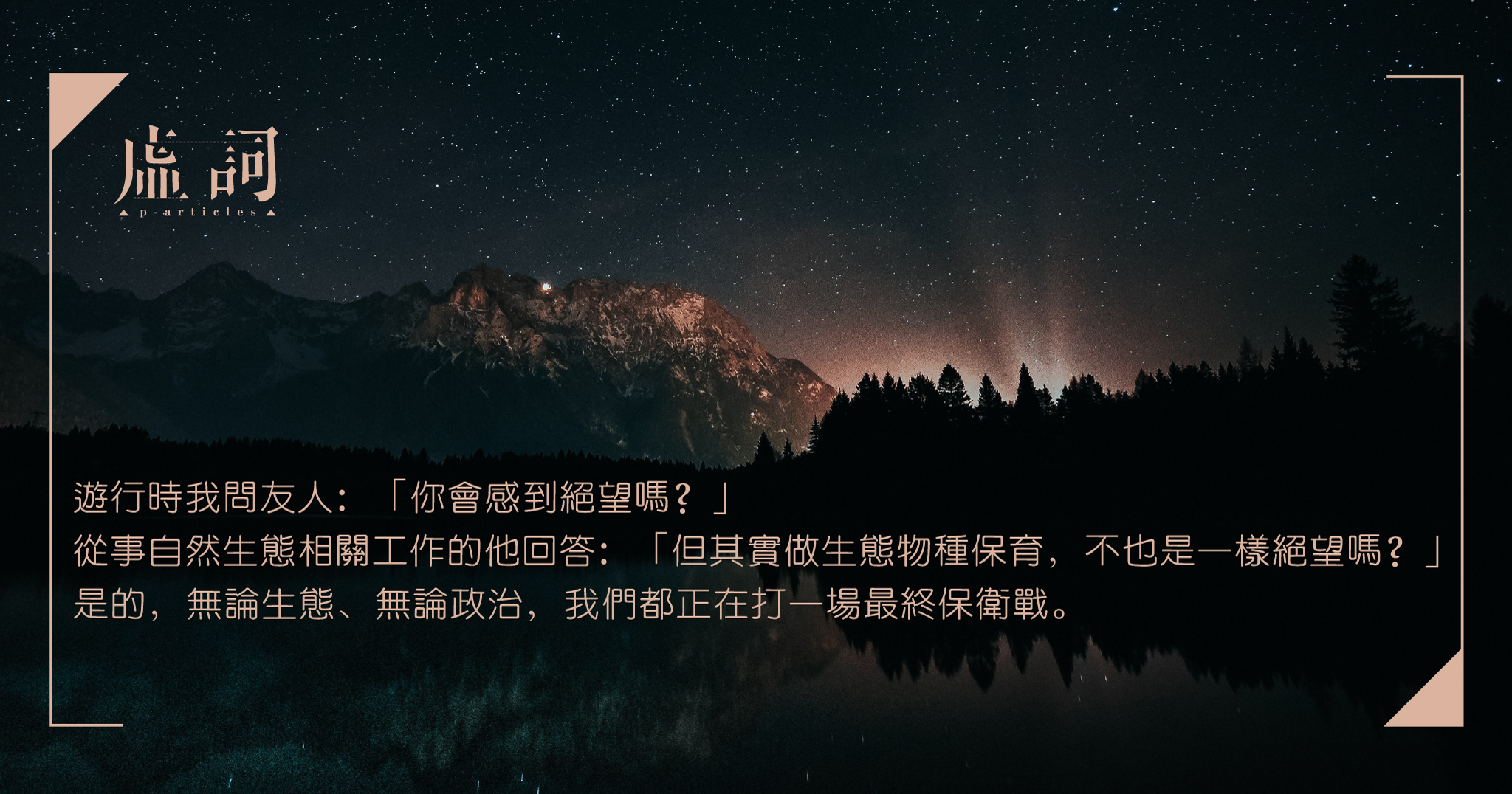【無形.Be Water My Friend】水文與生態物種
散文 | by 葉曉文 | 2021-09-23
水是地球上最常見的物質之一。當潮濕的氣團遇到山勢阻擋,便會被迫沿山坡上升;氣團上升時會降溫,降至露點溫度時,便會變成雲,然後下雨。大氣以雨及霧的姿態,降水於陸地,水沿著地表往低谷方向下流,匯集成河,入海,最終蒸發而回歸大氣,成就一個完整的水循環。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水並非一成不變,它在冰點以下化作堅硬的冰,遇熱時氣化於空中;看不見但不代表它消失了,時刻存在於我們一呼一吸之間。
我並非不喜歡城市,而是覺得山外有山,香港野外有另一番風景。我欣賞高山淨潔的空氣,原生花草讓我驚艷,人類以外的動物原來那樣「得意」。香港地方細小,卻是山水相連,蘊藏不同生境,擁有五十七種陸上哺乳類動物,接近一百二十種兩棲及爬行類動物,近五百五十種雀鳥,超過二千一百種原生植物。
水,由上而下,起點始於山。高山上都是霧濕、清氣、滿眼的綠色;急降至半山時,人類痕跡開始顯現,多是一些單層舊石屋的遺址,卻早已人去樓空。繼續往山下走,便可看見人工鋪設的水管及小堤壩,它們攔截溪流,改變天然溪水的流路;當這些被改變方向的流水滑到下游平原,那兒便漸漸出現文明。村屋露台掛著正在晾曬的衣物,田裡栽種了可吃的蔬菜,然後村狗也開始瘋狂亂吠。
不知不覺間,城市複雜的色彩呈現眼前,空氣中雜質飛升,近馬路處開始揚起一層薄薄朦朧的霧霾。河口附近店舖及村屋林立,利用河流排泄家用廢水,因此流入大海前一刻的水往往呈現奶白色,或浮著一層七彩的油光……
人類究竟為何要上山對自然進行探索,是愛還是責任?又,對於山與自然而言,人類屬甚麼角色?他們有否言行不一,一邊說「欣賞」,另一邊廂卻輕率破壞?
我十分在意那些「已在香港野外滅絕」的物種。最初我在維基搜索到「亞洲已滅絕動物列表」,後來也在香樂思的《野外香港歲時記》(一九五零年代出版)及其他書籍中,對照出一些已經消失的香港物種。我在想:為何在短短七十年裡面,這些物種會自香港野外消失?這可能由於社會發展而導致生境消失,可能由於非法捕獵,也可能因極端天氣令到物種無法適應而絕種。
我時刻擔心著,到底下一個將於香港滅絕的物種又是甚麼?又推想到今天嚴峻的社會狀況,覺得作為本地「原生種」的「香港人」這個概念,是否也即將消失?
生物及生態學中素有「原生」與「外來」的概念。原生種指沒有人為因素夾雜的自然分佈物種,外來種則指經由人為無意或有意引進的物種。當外來生物大規模入侵,進而排擠和殺死當地原生種,便會影響生態系統的穩定,最終導致嚴重的社會經濟與生態環境問題。
作為八十後,微小的我在時間的河川中隨波逐流,見證了回歸前後我城的轉變、外來人口輸入及其思想價值對本地文化的影響:八九六四之後,不少親朋戚友移民外國,幼年的我久不久就得趕到啟德機場、紅著眼睛去送別。然後九七回歸,藍黑的旗幟在暴雨中換成紅色的。然後,禽流感之後是「沙士」。然後,外來移民數目急劇上升,人口膨脹,樓價急升,生活成本高企……香港人總得面對種種生活壓力。
香港保安局於二零一九年二月時就《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開始公眾諮詢,引起立法會、商界、法律界等的廣泛疑慮;四月時,我首次參加了有關送中條例的遊行,其時已發覺氣氛不同,連粵音不正的疑似「新香港人」也出席其中,而且為數不少——這是在以往遊行中鮮見的。
人們發現多數河流的源頭都在極高的山地和峰頂,開始於一個若即若離、似有還無的開端,但隨著時間蘊釀,能量愈聚愈多。Be water, my friend,慶幸我身邊有理念相近、同上同落的朋友,我們見證6.9、6.12、6.16、7.1以至及後的事件。「是你教我和平遊行是沒用」,示威者以噴漆留下的標語,令我震撼。連作為成年人的我,萬萬預料不到政府不單無心修補撕裂,更把事情推至如斯地步。事實上,香港亦有不少已上岸人士只心繫自己的「收成期」,顛倒是非黑白,令人憤恨。對於漸行漸暗的未來,香港人如何面對?難為十幾歲的青少年,他們還有漫長的五、六十年要忍受。
遊行時我問友人:「你會感到絕望嗎?」從事自然生態相關工作的他回答:「但其實做生態物種保育,不也是一樣絕望嗎?」是的,無論生態、無論政治,我們都正在打一場最終保衛戰。
示威浪潮由六月持續至八月,至今仍未有止息的跡象;夏日如火,夜晚卻是觀看螢火蟲的好季節。香港有二十九種螢火蟲,某夜,在一片雜草叢生的濕地,我跟朋友等待著發光昆蟲的出現。天文台預測當日日落時間為十九時零二分。我們一直等,天色逐漸由藍轉黑,到了很暗的時候仍看不見蟲的影蹤,我有點焦急,說:「無可能喎,為何一隻也看不見?」原來只是天未夠黑。天黑了,上百隻螢火蟲開始發亮,有些不斷閃光,有些閃一下、休息、再閃一下。牠們「各自爬山」,用自己的方法努力發出信息。
晚風輕吹,牠們的飛翔愈來愈顯眼,就像,世道愈黑暗,愈突顯出人性美善的微光。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