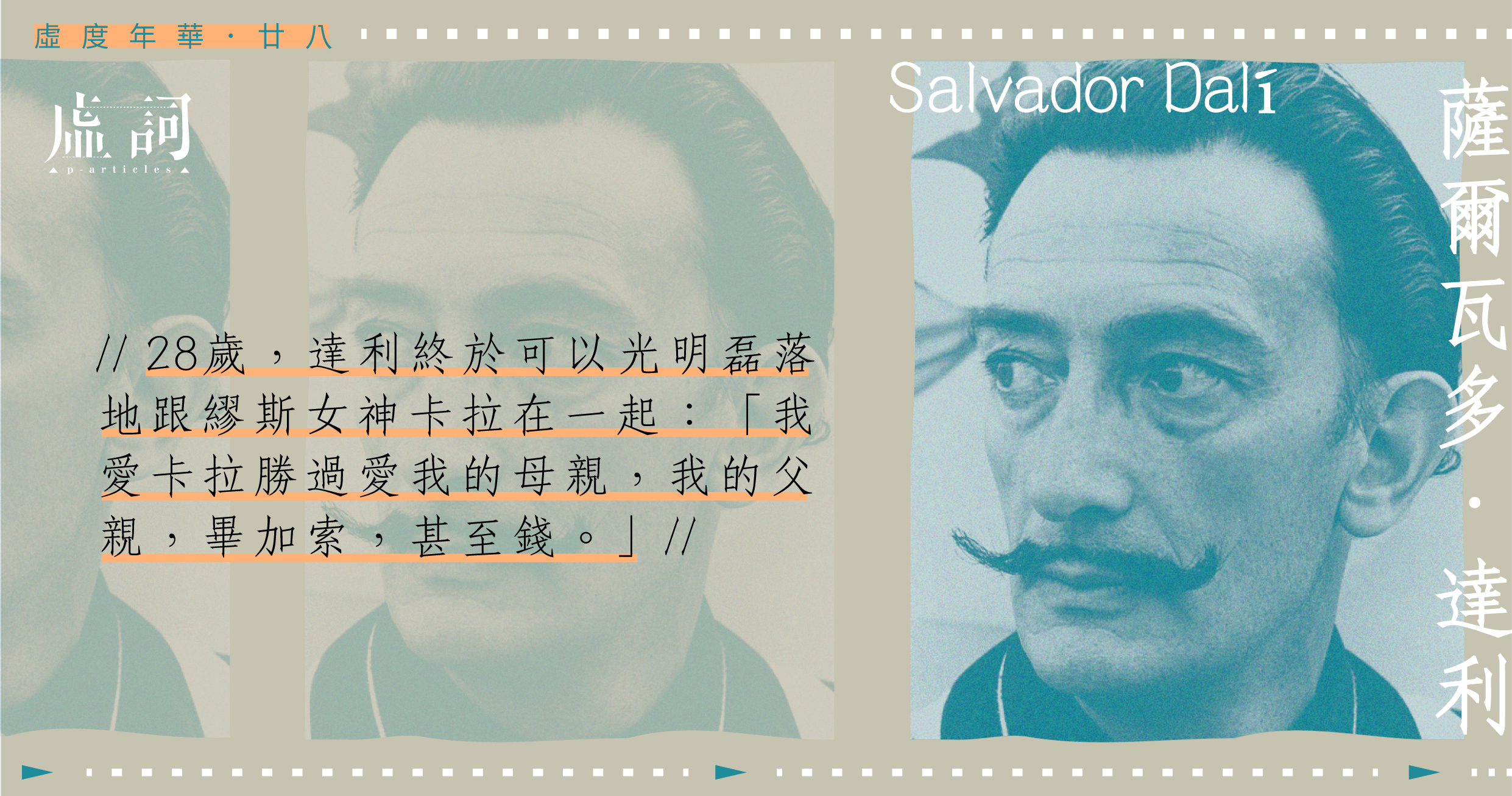【虛度年華.廿八】達利︰我愛畢加索,更愛卡拉
廿八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8-11-15
1932年,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28歲。
軟趴的時鐘、乾枯的枝椏、平靜的海港、垂死的怪物……即使你叫不出畫作的名字,《記憶的永恆》(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依然是超現實主義畫派的代表作之一。1931年,達利完成了《記憶的永恆》,同年在巴黎個展上展出;一年之後,達利攜同畫作初次參加於紐約舉辦的超現實主義群展,讓他成功於美國嶄露頭角,開啟歐洲以外的藝術市場。
「一剎那光輝唔代表永恆」,如果《記憶的永恆》代表著達利的光輝,那麼身為繆思女神的卡拉,就是達利的永恆。達利與卡拉(Gala)在1929年的夏天邂逅,彼此一見鍾情,但卡拉彼時卻是法國超現實主義詩人保羅.艾呂雅(Paul Éluard)的妻子——本名為艾琳娜迪亞科諾娃(Helena Diakonova)的俄羅斯女子,「卡拉」原是艾呂雅為她改的名字。
達利與卡拉愛得火熱,曾經何時,畢加索是達利最常想起的人,但認識了卡拉之後,卡拉卻變得比任何人都重要。「我愛卡拉勝過愛我的母親,我的父親,畢加索,甚至錢。」哥哥於達利出生前九個月死於腸胃炎,薩爾瓦多——哥哥的名字——藉著達利的出生借屍還魂,以致他自出生以來便背負著父母對哥哥的思念與期許,哥哥的影子愈大,達利渴望變得與眾不同的想法就愈強。在父親嚴厲的教條之下,母親的愛與鼓勵,漸漸變成達利心靈棲居之處,但卡拉的出現,卻勝過了母親的愛,成為達利餘生的追求與慰藉。1932年,卡拉與艾呂雅離婚,正式與達利開展新生活,成為他的經理人、模特兒,甚至是妻子——兩年後,二人舉辦了民事婚禮,確立了夫妻的名份。

(達利與卡拉)
早在《記憶的永恆》成為光輝之前,達利已經因著卡拉而創作不斷。《大自慰者》(The Great Masturbator, 1929)是達利為卡拉而畫的首幅作品,畫面中的巨大岩石狀物體代表達利本人,右側是女人為男人口交的畫面,此女人不作他人選,非卡拉莫屬。據說達利曾宣稱在遇見卡拉之前自己還是處男,是卡拉轉化了他、釋放了他,甚至啟發了他創作以性來抒述內心情緒的作品,當中包括《性慾的幽靈》(Spectre of Sex Appeal, 1934)及《蜜蜂的飛行》(Dream Caused by the Flight of a Bee, 1944)等。
雖然《蜜蜂的飛行》仍殘留超現實主義的影子,但隨著二次大戰進入尾聲,達利的畫風亦突然轉向,趨向古典風格發展,畫作中不乏受宗教、原子物理及量子力學影響的影子。而正是在這時期,卡拉從畫作背後的繆斯,一躍而成畫布上的模特兒,達利以更細膩精緻的筆觸,將卡拉的外貌與造型呈現於畫作上。其中之一便是著名的《力加港聖母》(Madonna of Port Lligat, 1949),聖母正在畫面中央慈祥地祈禱著,而這聖母恰好就是卡拉的化身,在別人眼中瘋狂躁動、野性難馴的達利,在卡拉這聖母之前,卻乖乖地安靜下來,達利在卡拉身上,找到了比母親更可依靠的情感連繫。
28歲,達利終於可以光明磊落地跟卡拉在一起,至1982年卡拉過身,頓失繆斯女神的達利才開始減產、收斂光芒。往後幾年,達利甚至多次被懷疑自殺,至1989年因心臟病離世,才免卻被蒙上自殺的污名。
1932年,薩爾瓦多.達利(Salvador Dalí),28歲,距離他前往倫敦拜訪佛洛伊德還有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