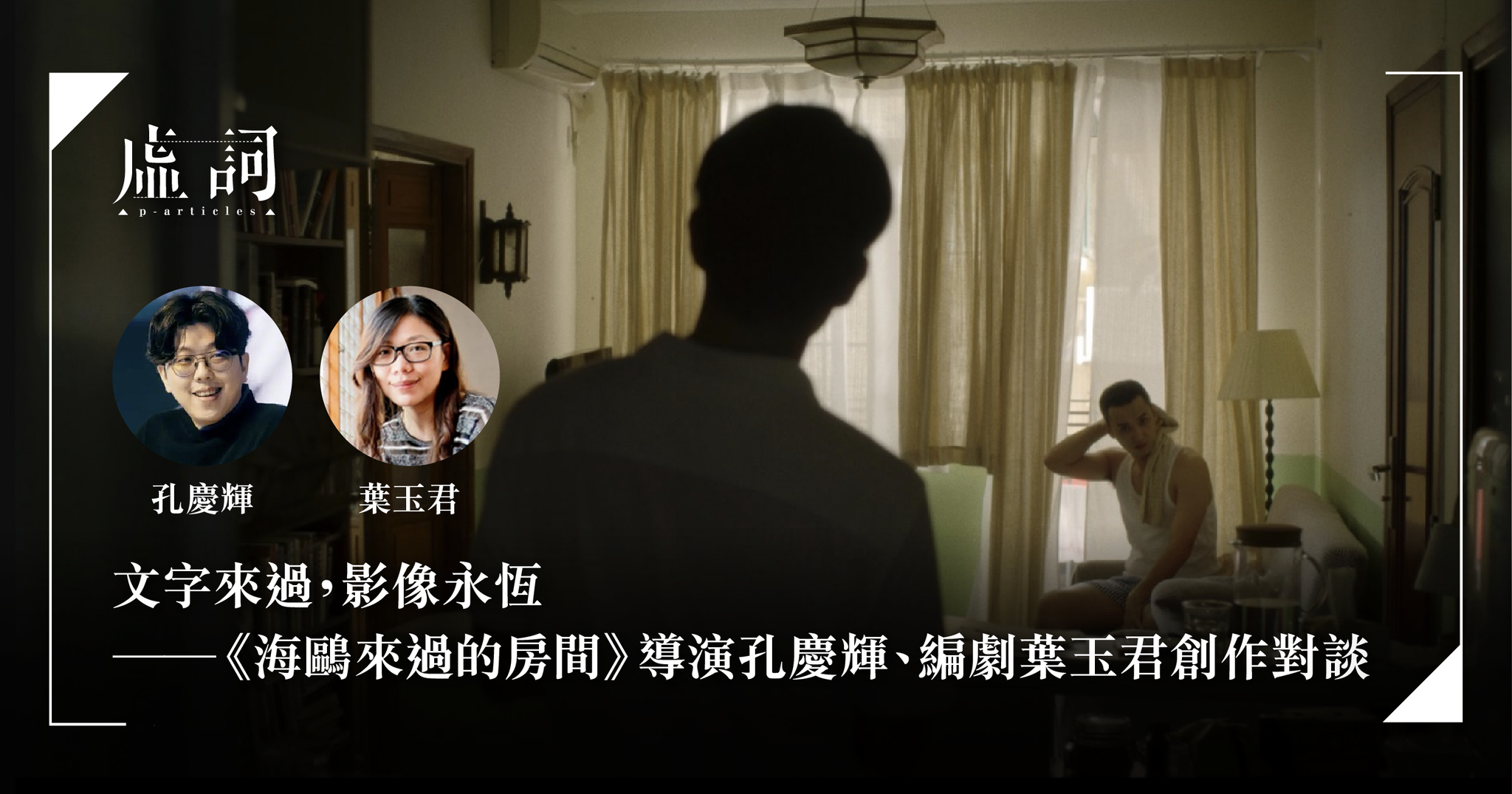文字來過,影像永恆 ────《海鷗來過的房間》導演孔慶輝、編劇葉玉君創作對談
澳門電影《海鷗來過的房間》像股小旋風掠過台灣、香港,再駐停在它的家──澳門,隨著它取得的傲人佳績:金馬獎三項提名入圍(最佳新導演、最佳音效、最佳攝影)、香港國際電影節「火鳥大奬」新秀電影競賽(華語)最佳導演,也在小城掀起有關電影與創作、文字與影像的思考和討論。
導演孔慶輝說,其實他拍《海鷗來過的房間》是想為自己心裡的問題「搵答案」,的確,藝術工作者的創作不一定是為了向讀者或觀眾提供現成答案,更多時候,是創作人藉著作品提出問題,和讀者或觀眾一起去「搵答案」。那麼,催生出《海鷗》的問題究竟是什麼?要回答這個問題,大概要去回溯創作之初的源起,回到影像背後的那些文字,在層層疊疊的構想、字字句句的探索之間,尋找創作人的提問和回答、思考和靈感……
都說《海鷗》是一齣「沒有劇本」拍成的電影,但其實早在2014年,孔慶輝就和長期合作的編劇葉玉君及一班朋友開始醞釀《海鷗》的故事雛型,「自己很想探討創作者和角色之間的關係究竟是什麼?」舞台劇演員出身的孔慶輝一直覺得,作為演員,拿到劇本和角色之後,就立刻要進入一個陌生人的生命裡,「在這過程中,你需要知道自己是什麼,行路的姿態、講野的節奏、對人的態度……當你要進入另一個角色的人生之前,你必定要非常了解自己,而這一點對我來說是非常難的。」所以,當後來決定要拍一齣長片的時候,他就決定就從此入手:「人應該怎樣了解自己?(在電影裡出現的)劇場演員、小說作家,我是想藉這兩個角色來探討這個(主題),這大概就是我的初心吧。」
電影創作的構思初期,導演和編劇大約每隔一、兩周就開一次會,大家互拋一些有趣的意念或主題出來,看有沒有可能發展成一個故事,「當談到人如何面對真實的自己這個主題,」編劇葉玉君回憶,「大家都覺得很有趣,於是就基於這個意念繼續發想下去────在劇場裡,如果角色和劇作家可以溝通的話,他們會說些什麼呢?如果有一天,有個角色走出來,要和劇作家傾偈的話,他又會說些什麼?比如,問你點解要整死我?我明明唔想咁,你點解要我咁樣?」
兩人都記得,《海鷗》的最初版本是一個瘋狂的黑色喜劇設定:故事發生在澳門崗頂戲院的後台,有一班戲劇裡的角色跑了出來,在現實世界裡生活,然後他們突然意識到「咦?原來我們係角色來架?」────「當角色發現自己是角色的時候,他們的反思會是什麼呢?」憶起往事,編劇和導演都笑言,「當時我們都覺得,哇!呢個故事勁呀!」於是拿這故事去參加在澳門舉辦的「粵港澳電影創作投資交流會」,雖然最後沒有成功闖關,但也收獲了不錯的評價和口碑。
幾個月後,孔慶輝又跑來找葉玉君繼續傾,葉玉君就提出不如寫一些自己擅長的東西,「澳門編劇的風格大多比較沉鬱,我也是。」於是兩人就開始發展其他不同風格的故事版本,後來碰上澳門文化局推出「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有150萬製作資金補助,於是他們決定一試,整理出較完整的劇本和分場大綱,而故事也變成了一齣「公路電影」,「主角變成了一個中學老師,他同時也是一個作家,一次和學生去畢業旅行的中途,他們的旅遊巴遭遇劫匪,但老師發現那劫匪原來是自己書中的角色。」孔慶輝回頭爬梳故事修改的脈絡,一方面因為自己本身就很喜歡「公路片」,另一方面比起當初的群戲,兩個角色的設定更簡單易處理,「但故事的核心沒有變,仍是希望探討作者和角色之間的關係。」
在這期間,孔慶輝和葉玉君寫了七、八個不同的故事版本,「我們一直在考慮該用哪個故事背景,比如角色是中學老師,後來我們想一想,說不如改成地產(經紀)吧,我們一直都在討論,看看在(澳門)這個社會,哪種角色設定最適合?中間有變過的可能都是這些,但想講的(主題)一直沒變過。」劇本經常反覆修改,編劇也被導演不斷「Ban橋」,但葉玉君覺得這過程也很有趣,「會知道什麼是我們不要的,因為當故事大綱寫出來後,落到分場的時候會發現,咦?唔係咁樣喎,然後我們就會知道,這不是我們要的,然後再繼續搵。當然這過程也是很困難的,因為未必知道究竟什麼才是自己要的。」
導演孔慶輝深有同感,「我覺得整個編劇過程有點像是在進行哲學討論,所以其實是沒有答案的,就變成很多時候大家都在磨這個concept究竟是什麼?究竟我們想拋給觀眾的問題是什麼?」
漫長的創作醞釀期始終也有盡頭,「電影長片製作支援計劃」的交貨死線在即,終於拖唔可拖,電影必須開拍之際,導演才發覺大鑊,「還沒有(完整的)劇本喎,人物還沒有台詞喎!我們只有一個故事框架,大概知道人物角色的走向,但怎麼拍呢?當時心裡好驚。」《海鷗》故事雖已有雛型,但仍有相當部分細節尚未確定,導演也不滿足於傳統的「表演式」創作方式,「有時我覺得,自己寫這個人物(角色)出來,好多時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去講某個議題,人物變成了工具──借角色之口去講編導想講的東西,我覺得咁樣唔得喎。」
就在初期仍糾結於「要不要開拍」的猶豫之際,孔慶輝就想:「咁不如試下再玩大啲」──「電影裡那些人物,怎樣才會有最真實的狀態呢?不如擺啲真的人物落去啦!」於是孔慶輝採用了「類紀錄片」的方式,影片中的劇場導演、演員、地產經紀、菲律賓租客、小朋友等角色,「很多都是真的人(物)來的,他們講的話(對白),都是在拍攝當下我大概告訴他們要拍什麼之後,他們自由發揮的。」孔慶輝說自己經歷了一個很大的轉折,就是最後決定用這種方式來「玩」。
出乎意料的是,這些本色演出的演員們,有時突如其來的神來之筆,甚至突破了導演和編劇的想像力,「返轉頭想,有些東西我們作為編劇未必想得出來,因為有時我們會『以目的為本』,為了劇情轉折而去營造某些場面,但想不到這些(素人演員的即興表演)出來的效果反而非常之好。」
到影片正式開拍時,劇本也大約只寫了20多場,但編劇和導演預計全片應有40多場戲,「有些只有大概的想法,具體會發生什麼還未想清楚」,所以拍攝期間孔慶輝會不時打電話向葉玉君「求救」,「就算個(故事)框(架)也在不斷調整,我會和她說今天拍了些什麼,有些新的情況出現咗,我們要怎樣改後面的情節線,怎樣行落去。」葉玉君形容這次創作對自己是一次「自信心訓練」,「整個過程有趣的地方就是,可能你掉幾頁紙(劇本)給他,他可能從中找到一個元素、一句說話、一個idea,就拿去拍了幾場戲出來,我們合作的方式就是這樣,我不斷地拋嘢給他,看看fit唔fit他心裡想要的。」
「其實戲裡一直在探討什麼是『活生生』(的人物),這樣(以素人參演的即興發揮方式)也正好看到了人物的『活生生』,」葉玉君說,「當戲裡的角色走出來的時候,如何和創作者互動?這也是最開始的命題────當你跳出這個框框的時候,這東西怎樣才算是『活』的?而不是死板地一味按照劇本、台詞。其實一個人的人生也是這樣的:當你意識到有個框的時候,你怎樣out of 這個框?怎樣去找到屬於自己的這種『活生生』呢?」
最後我問導演:你帶《海鷗》去過台灣、香港、新加坡等不同地區的華語觀眾群,現在回到澳門,覺得觀眾反應有何不一樣?「正如剛才說的,這套戲其實也是在探討一些哲學議題:人如何看自己?何謂自我和真實?這些其實也是很普世的。」孔慶輝回答,「我印象最深的是,電影在澳門公映了一個多月,大家都很直接feel到那種澳門人的感覺,比如澳門人的處事方法,他們的生活節奏、感到壓抑的方式……這是我比較開心的,好多時有人問什麼是『澳門電影』,我覺得,澳門電影就是你很忠實地拍出澳門人的生活、他們面對的問題,那就是澳門電影了。」

(左起:對談主持李爾、編劇葉玉君、導演孔慶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