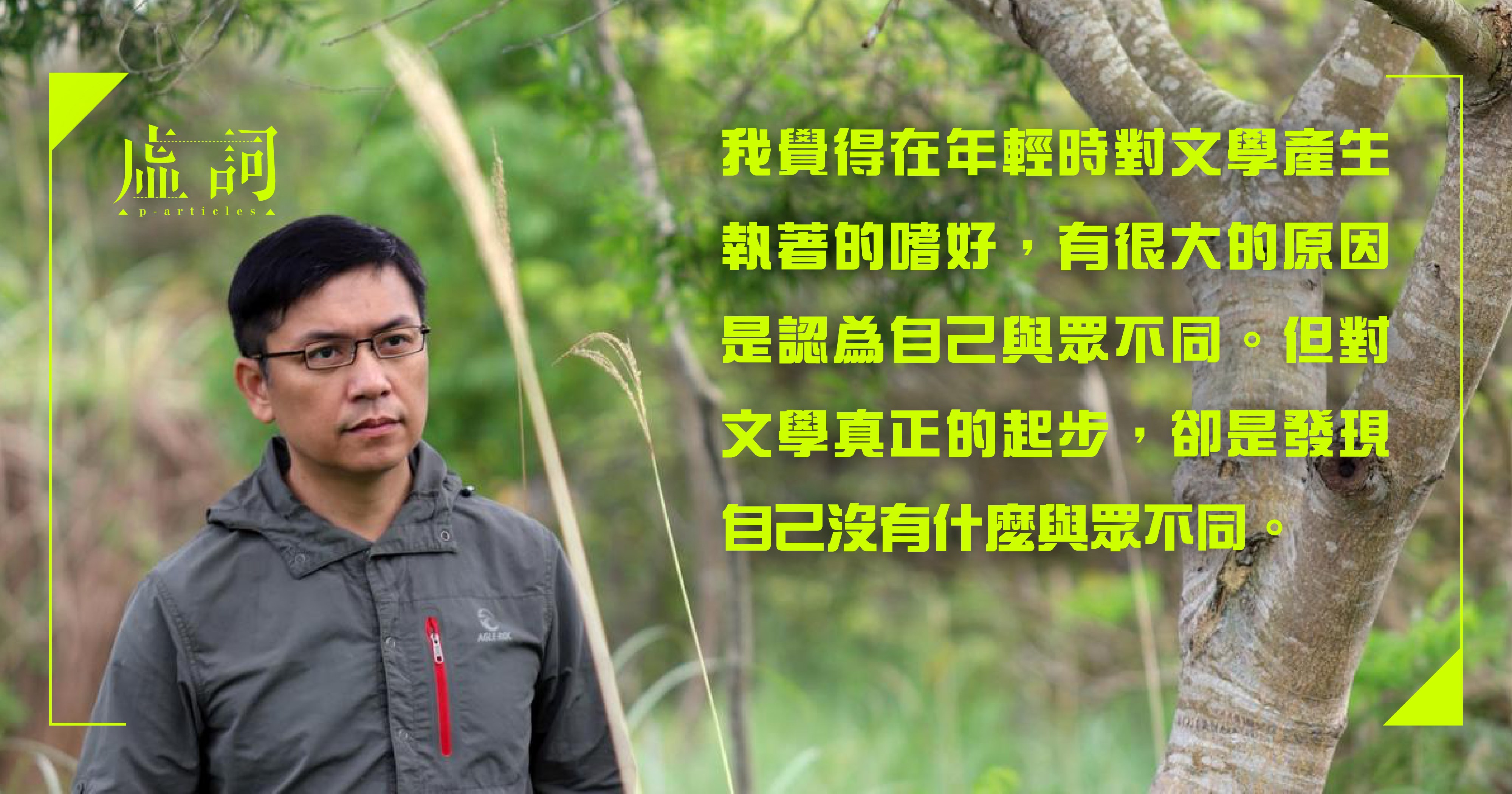《也斯的香港故事》序——一個難說的香港故事
書序 | by 樊善標 | 2023-04-26
樊善標在王家琪的新書《也斯的香港故事:文學史論述研究》序言提到,作者選定了也斯反覆談論的幾個重要課題,縷述也斯關注各課題的緣起、經過,以及課題之間的連繫,從中透視他的香港文學史觀點,困難卻也是此書的吸引力所在。 (閱讀更多)
「雙生展2021-體。回」 與你同城共生的少年
報導 | by 東 | 2021-05-27
這一代被命運再度選中的青少年,踏上我城近半世紀以來從未有人經歷的漫長路途。「雙生展2021-體。回」的三名參展創作人,皆於2000年後出生,參展作品均是他們這一、兩年來,對社會、個人和生活的體悟和回顧,並將日常生活的經歷及啟發反思,轉化成作品呈現。 (閱讀更多)
塑造香港視覺文化的大師 訪香港平面設計第一人Henry Steiner
正所謂,在香港做設計慘過食屎,社交媒體上不時會看到從事設計行業的人訴苦,甚至有「香港做設計慘過食屎協會」。設計在香港不算是討喜的職業,人工低工時長,又或者遇上難以理解的客戶的話,更是叫人難受,而被稱「香港設計之父」的Henry Steiner(石漢瑞)又是如何看待這個行業? (閱讀更多)
「一時」 x 「周末文學」:文學自救,需要每個人的堅持
問及策劃初衷,方太初略為沈吟,隨即道出一個核心問題:「香港從不缺乏好的藝術作品,到港島走一圈,展覽花一整天也看不完。偏偏在這個每天生產大量創作的地方,仍有很多人覺得香港沒有文化藝術。而即使是藝術愛好者,涉獵的範疇亦不廣,如一個『文青』能數出十個香港作家的名字,卻未必能數出十個香港設計師的名字。」故近年方太初做任何事,都希望帶入兩大目的:「讓人看見香港的創作有幾正,以及讓不同藝術範疇跨界合作。」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