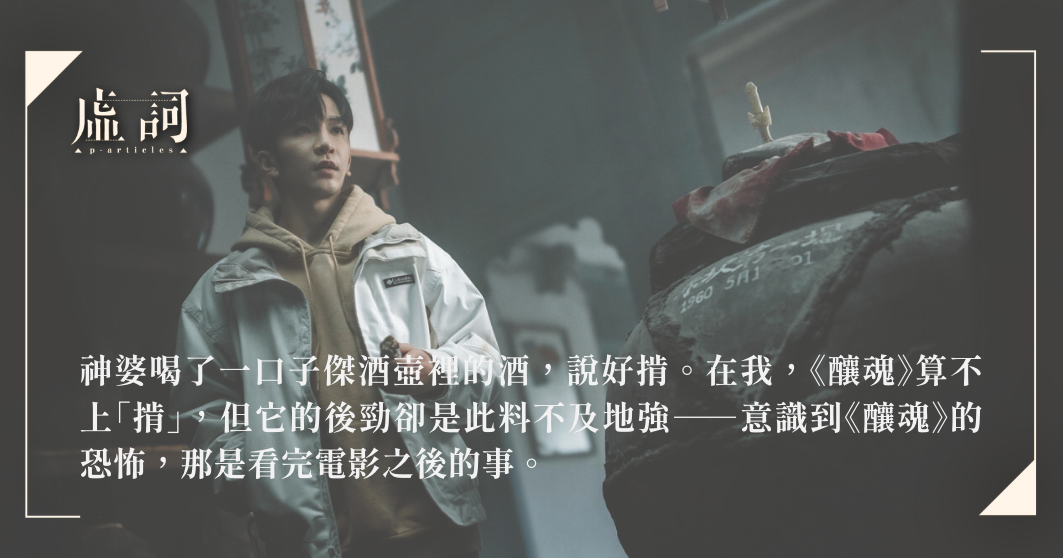新晉導演岑嘉彥執導的懸疑驚悚片《釀魂》由盧瀚霆主演,雙雙分析劇中的四位死者,重新組織事實的真相。他假定人物所說的都是實情,所有鬼也是真有其鬼,那麼在阿武之外、在鐵槌和開山刀之外,還有更厲的鬼、更血的暴力,它不但能橫行在失序、恐怖的夜,還可以安然曝露於陽光的規矩底下。 (閱讀更多)
《從前的我們》:每個移民故事,都有一個留下的人
由韓裔加拿大籍導演宋席琳(Celine Song)首次編導的《從前的我們》(Past Lives),黃柏熹認為它不是聚焦移民和美國夢的糾纏,也不是透過多重宇宙訴說移民對自身的肯定,而是透過一個兒時玩伴的目光,透過一段沒有發生的感情,透過身體和凝視,來訴說身份和回憶的曖昧,訴說離開離不開。導演透過電影說有些跨越要以一生作為代價,所謂「一生」終究是在時間的荒野裡,遇見一個人。 (閱讀更多)
藝術與史實差距三萬里?談《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
日前由追光動畫製作的電影《長安三萬里》在國內上映後大賣,亦同時惹來爭議,作為一部「動畫歷史片」,又以「還原大唐氣象」作為賣點,卻被指斥電影內容與史實不符。曾繼賢談論此次《長安三萬里》的史實爭議,分析電影中的「失實」和藝術手法,也看看以往的「失實」電影,比對而論。當我們在創作過程中要從藝術與史實之間取捨時,兩者是否必然為「魚與熊掌」的難題?我們應以怎樣的尺度去判斷? (閱讀更多)
《全個世界都有電話》的二向箔抵抗
電影《全個世界都有電話》令人聯想起〈小心地滑〉和《奇異女俠玩救宇宙》的英文譯名,但雙雙認為這部電影與兩者無關,但這另外兩個文本之間確實有共通之處——它們都是故事發生的2022年的,也就是主權移交25周年。而雙雙借用科幻作品《三體3》中的「二向箔」形容電影中的智能手機,它的平面延展在某程度上化約了距離、消融了距離造成的邊界,產生一種訊息/瞬息全宇宙的便捷,但界線的移動與消融卻又在那程度下造成了些新的困擾。 (閱讀更多)
落花時節又逢君:《長安三萬里》裡沒讀出的詩
看過《長安三萬里》後,廖偉棠想起美國詩人默溫「超譯」《早發白帝城》的〈大江〉,從而說起片中如群星閃耀般輪流登場的詩人,以及他們所附帶的潛文本。細味過後,他認為杜甫可能才是《長安三萬里》的主角,而不是電影的敘事者高適,但二人沒能在片中完全呈現的情誼是一番更驚心動魄的「落花時節又逢君」。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