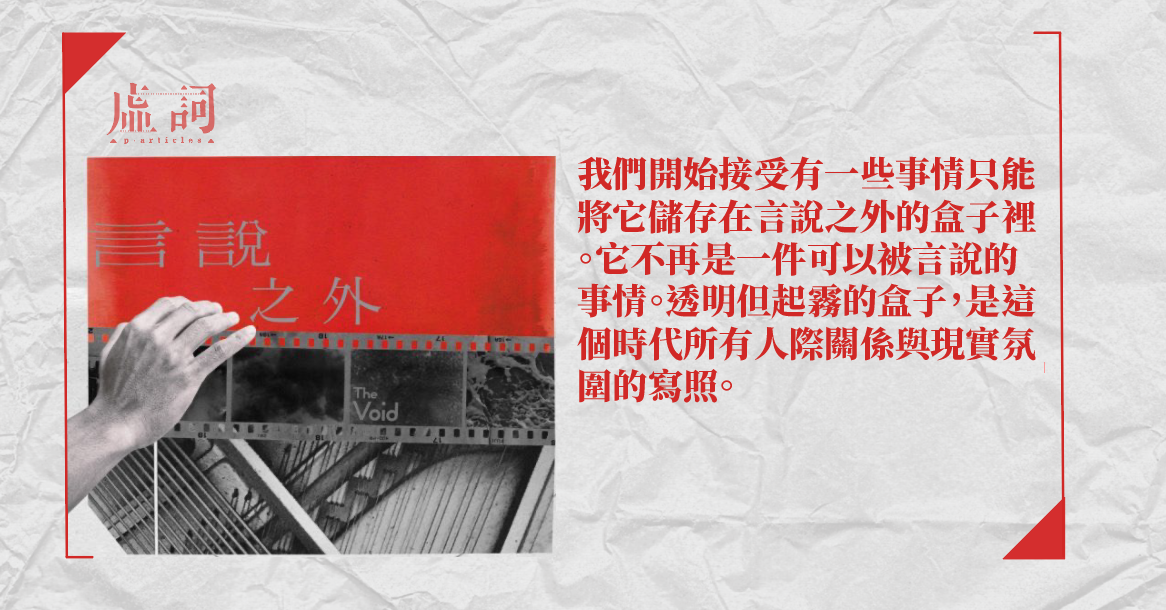疫情緩和,回到香港話劇團「復業」的黑盒劇場《言說之外》,聆聽男女主角(黃譜誠與郭靜雯)的獨白絮語,觀看那些壓抑、無從宣泄的肢體語言,一場集體文本實驗,將現實日常裡不能言說,無法對當事人宣之於口的心底話,連同自身,都放在一個劇場空間/玻璃盒子裡。這個宛如囚籠的房間,難免有點像疫情下整個城市的隔離生活。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原則》】:學做一個「人」,先別失去對人的信心
求學不是求分數,教育理念更應著重的,是如何教導學生做一個「人」。在種種冰冷的制度背後,是要透過罰則來換取學生的絕對服從,抑或在制度裡加入人性化的處理,足以帶來兩種截然不同的走向。 (閱讀更多)
【香港話劇團《原則》】:真理在胸筆在手
近日劇院重開,香港話劇團的《原則》載譽重演,雖為舊戲新演,不過,回望過去一年飽歷滄桑的香港社會,語境大有不同,劇中這一場由「撤回」新校規所引起的校園鬥爭,繼而激起教師請辭,學生罷課,再牽動家長、社會輿論及整個教育制度,一切都是那麼似曾相識、歷歷在目。校園是社會的縮影,但劇場亦是現實的橋樑,或者觀眾可以稍為抽離自身,嘗試理解另外一方的想法。如劇中所言,可以討厭,但不要仇視,可以批評,但不要批鬥。時勢再險惡,都不要離棄民主與自由的基礎。 (閱讀更多)
回歸與搖滾:觀前進進《聽搖滾的北京猿人2021》
有劇評人認為此戲是傘運之後最圓融的社運題材作品,李向昇覺得圓融之處,正在於此戲能很好的安放不同的聲音,不隨意批判,引人深思,尤其遇上這別有意義的時期,更添隱喻意味。 (閱讀更多)
再聚——Project Roundabout「不日上演」
信的標題為「給劇場點一盞永明燈」。為劇場點燈,顧名思義,是指劇院重開,觀眾得以進入劇院欣賞演出,有燈,有觀眾,劇場又重新運作;不過標題不止於此,它清楚點明「不日上演」這計劃是要為劇場點一盞「永明燈」,就是「有燈,繼後就有人」的意思。整個計劃,短期目的固然是要幫助業界度過疫情難關,長遠而言更要為香港劇場留住優秀的人才,讓演員不用因為生活困難而被迫轉行。主辦單位希望透過讀戲演出,為年青演員創造實戰機會,讓香港的舞台劇界能夠持續發展。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