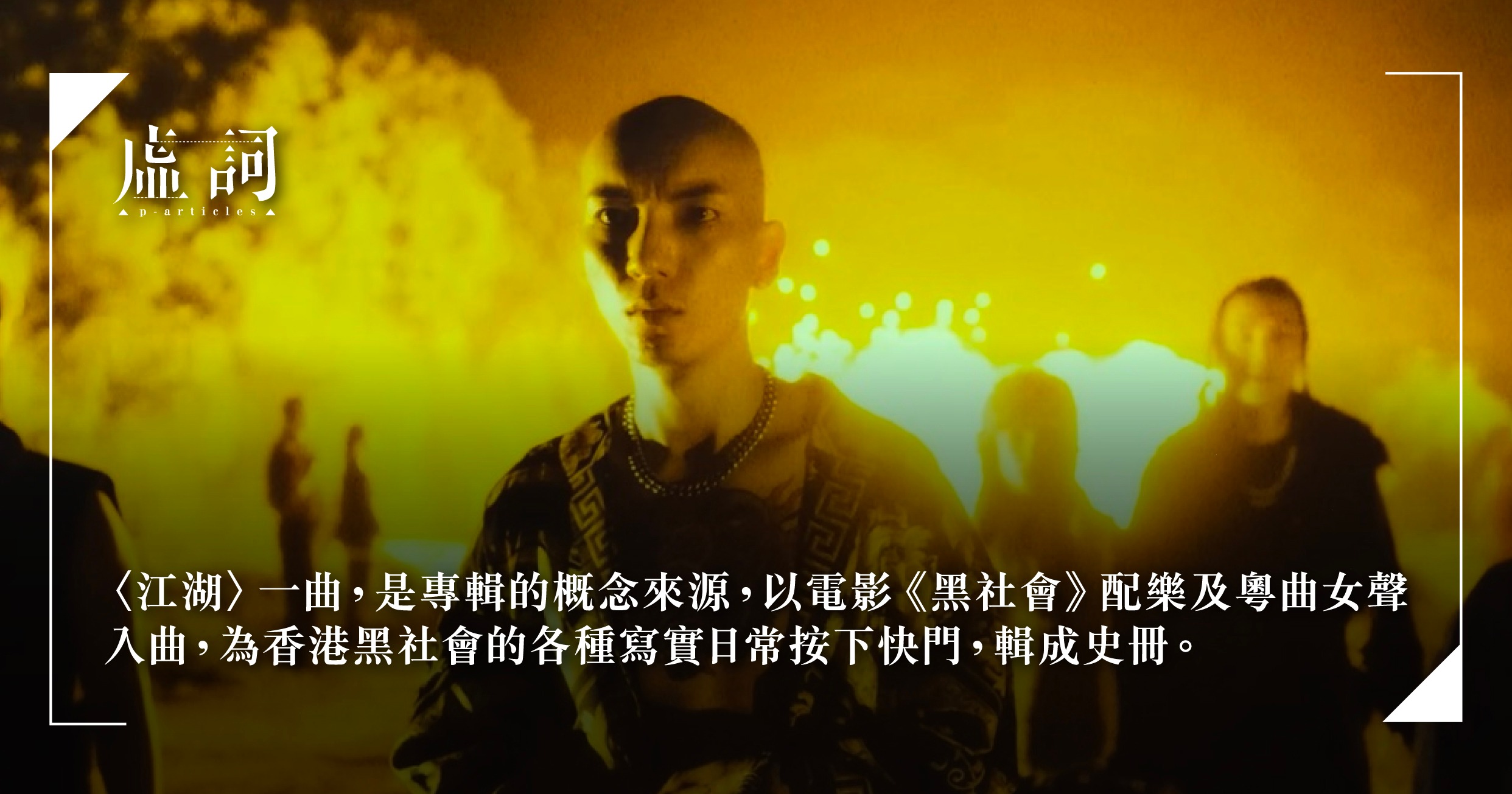《東京女子圖鑑》中的都市全貌——現代女性的生活與夢剪貼簿
劇評 | by Darius | 2022-12-25
Disney+的原創台劇《台北女子圖鑑》遭到台灣網民的大量負評,大部分留言都拿台北版的和原作《東京女子圖鑑》比較。原版雖沒網民所言拍得那麼出色,某些橋段例如角色對著鏡頭說出內心獨白的橋段在如今看來更顯突兀,卻依舊難掩劇本的出色之處。 (閱讀更多)
評《蒙面騎士》:拿起槍是為了放下槍的革命
書評 | by Louis @ Gunslinger 不曾遠去的硝煙 | 2022-12-23
哪怕冷戰以降的群眾運動大多以失敗告終,但是受壓迫者的境況和這些男男女女因不公而生的怒火終究是不會消散的,他們的怒火必將會展現出來,永不消滅,《蒙面騎士》一書正是訴說這個故事,戴錦華先生對薩帕塔運動精神的推崇,對女性主義的渴望和高呼「受夠了就是受夠了」的筆觸,更是教人動容。 (閱讀更多)
金在德的《棕色》、反本質主義與當代跨文化舞蹈
劇評 | by 尹水蓮 | 2022-12-19
城市當代舞蹈團即將上演《棕色》一劇,尹水蓮教授形容,劇中的舞者,宛若大樹分杈出來的樹枝。他們動作一致,一同傾斜身軀,一同背着手、小踢腿。他們膝蓋微曲,保持彈跳,讓身體上下擺動。背景音樂由金在德本人創作,以弦樂器與打擊樂器組成一闕混合曲,造出敲木般的聲音,慢慢把氣氛推上高潮,然而這種重複的節拍和旋律,卻不斷地阻撓音樂演得過於戲劇化。作品有部份元素來自傳統音樂和舞蹈,像韓國的巫俗舞salpuri的步法以及小鼓舞chaesangsogochum中的反覆彈跳,而聲音則近似牙箏ajaeng(七弦低音樂器)和韓國傳統鼓buk。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