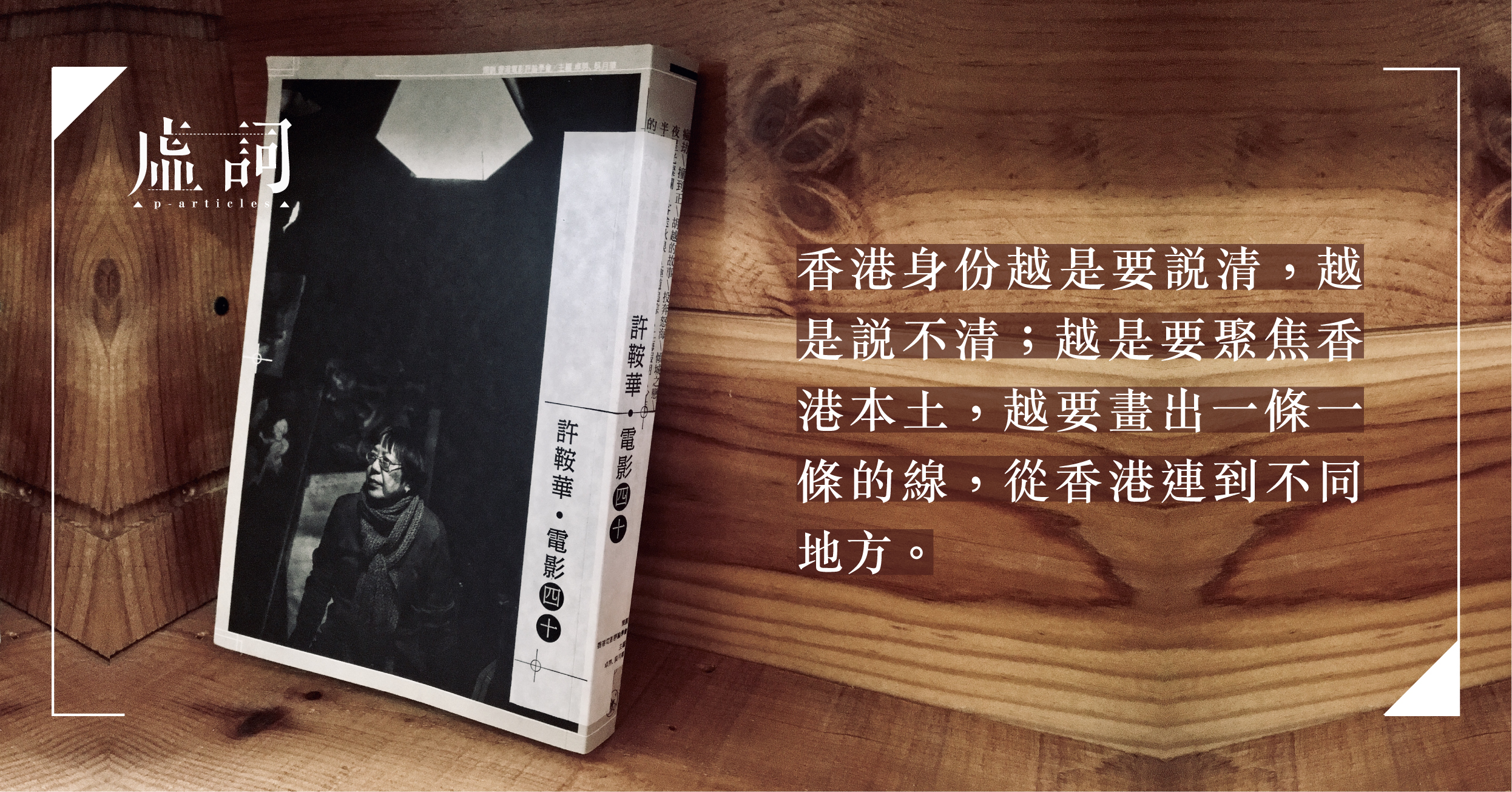「人生客路永沒平」:許鞍華的旅程電影與香港意識
影評 | by 李展鵬 | 2019-01-22
「香港故事總是變成關於其他地方的故事,彷彿香港文化本身並非一個主體。」[1]亞巴斯(Ackbar Abbas)曾經這樣說。
可不是嗎?在港片裏,香港故事常常是一段段的旅程。尤其在港片鼎盛期,整個年代的香港導演都在處理相似的議題:關錦鵬的《人在紐約》(1990)中,來自中港台的三個女人漂泊紐約,各有心事;嚴浩的《似水流年》(1984)中,一個煩倦的香港女人回鄉重訪兒時好友,心情複雜;王家衛的《阿飛正傳》(1990)中,「無腳嘅雀仔」旭仔拋下香港的一切遠走菲律賓尋親,客死異鄉。
有趣的是,女導演又彷彿比男導演更執着於旅程:張婉婷的「移民三步曲」[《非法移民》(1985)、《秋天的童話》(1987)及《八両金》(1989)]以愛情故事包裝移民題材,羅卓瑤拍下調子悲冷的《愛在別鄉的季節》(1990)、《秋月》(1992)及《浮生》(1996)等移民電影。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移民潮下,數十萬香港人移居海外,再加上香港本身就是個移民城市,這使得不同導演紛紛從流動題材訴說香港故事,探索香港身份。
從七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許鞍華也拍了好幾部旅程電影,包括「越南三部曲」《獅子山下:來客》(1978)、《胡越的故事》(1981)及《投奔怒海》(1982),以及《客途秋恨》(1990)、《極道追踪》(1991)及《上海假期》(1991)等。這些旅程電影的題材風格跨度在同期港片中是最廣的:許鞍華既拍香港人,也關注另一族群——越南人;她有時風格寫實,有時注入類型片元素;更甚者,她把自己的家庭流動歷史搬上銀幕,拍成半自傳式的作品。這些電影不但反映了一個世代的流離,而且更書寫出這個城市的某種難以名狀的特性──「香港性」(Hong-Kong-ness)。
《獅子山下:來客》以寫實筆觸關懷越南難民,為許鞍華日後的旅程電影奠下基調。
越南難民悲歌:《胡越的故事》
許鞍華的旅程電影一開始並非聚焦香港人。踏入電影圈之前,她為香港電台電視部拍了部《獅子山下》的單元劇《來客》,講述三個越南難民在香港的遭遇。越南是八、九十年代港片的一個特別的符號,徐克的《英雄本色III夕陽之歌》(1989)及吳宇森的《喋血街頭》(1990)等都借越南講香港心事,而許鞍華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觸碰這題材。越南的命運與香港關係微妙:首先,越南在1975年越戰結束後被越共統治,而香港則於1997年回歸中國;再者,更切身的問題是1975年開始有越南難民湧入香港,港英政府更在1979年宣佈香港是國際第一收容港,在接下來的二十年曾收容超過二十萬越南難民,引起極大關注。
《來客》以寫實筆觸關懷越南難民,為許鞍華日後的旅程電影奠下基調,也就是一種身不由己的流離。劇中人從越南逃到高棉,從高棉逃到澳門,再從澳門偷渡香港,受盡煎熬,只願最終可到美國。劇集於1978年播出,當時還沒有九七問題,但越南人的流離仍觸動了許鞍華。當《獅子山下》被認為寫活了香港人的生活百態,《來客》把越南難民也納入香港故事中。
到了《胡越的故事》,她嘗試把難民題材結合黑幫類型,起用周潤發與鍾楚紅飾演難民胡越及沈青。他們在香港學日文,辦假護照,企圖扮日本人逃到美國,但計劃生變,後來流落菲律賓唐人街,跟當地黑幫打交道。
電影充滿了流離的視覺元素,序幕是胡越乘難民船在香港靠岸(為日後的「投奔怒海」的意象埋下伏線),又有假護照的大特寫〔這是當年港片重要的香港意象,多年後《春光乍洩》(1997)同樣有護照大特寫],結尾則是胡越再次漂流海上。黑幫類型為這個難民故事添上暴力與危機,強化了難民朝不保夕的生活。片中的馬尼拉唐人街一如地獄:侏儒的奇異表演、猖獗的人口販賣、殺人如麻的黑幫。
雖是越南難民故事,但電影卻有意指涉華人/香港人。胡越是越南華人,他曾被問:「你的名字又是『胡』又是『越』,你不是中國人?」這種混雜身份正是香港人的寫照。胡越跟一個混黑幫的香港人結為好友。一心想去美國的胡越問他為何不離開,他說:「走去邊?由一條唐人街去另一條唐人街?」當他見到一群大陸偷渡客,又說:「我們都是命中註定,一世逃亡。」電影把越南難民、大陸人、香港人的命運牽引起來。最後,沈青身亡,胡越前路茫茫。電影尾聲呼應序幕,胡越又回到海上漂流,他的獨白這樣虛構着沈青的故事:「個女仔深信定可去到美國,我哋要靠呢個夢,完成旅程。」一代又一代華人都抱着美國夢,至今如是。
《胡越的故事》雖是越南難民故事,卻有意指涉華人/香港人。
黑幫肆虐東京:《極道追踪》
《極道追踪》同樣以黑幫元素講海外華人故事。留學日本的香港學生Ben(劉德華飾)及大陸學生鐵蘭(鍾楚紅飾)捲入黑幫紛爭被追殺,電影靈感來自中國女學生在東京一火車站離奇墮軌身亡的真人真事。[2]電影跟《胡越的故事》有不少相似之處:一頭一尾都是主角(這次是香港人Ben)在海上漂流的鏡頭;一如馬尼拉,東京同樣危機四伏,黑幫肆虐;《胡越的故事》有購買假護照的情節,《極道追踪》中鐵蘭的護照則被人惡意收起,沒有護照──即是無法流動──是他們永恆的惡夢。現實生活中,當時香港人也曾爭取居英權,也尋求外國護照。
片中三個主要角色,鐵蘭最後慘死,Ben撿回一命逃回香港,另一大陸學生則繼續尋找他的前女友──那個已經被黑幫操縱拍AV的大陸女子。貫穿全片的,是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帶出鄉愁情緒。跟《胡越的故事》一樣,電影的訊息是:城市總是地獄,漂流總是悲劇。
這兩部電影借用黑幫元素,虛構中有寫實。黑幫世界是隱喻:漂泊他鄉就恍如置身黑幫江湖,身不由己,危機處處。同時,黑幫類型有其局限,特別在性別書寫方面。在《胡越的故事》中,胡越身手過人,雖然屢屢陷於險境,但亦有反抗之力,反觀沈青就成了難民加女人的雙重弱勢,只等候被救援;《極道追踪》如出一轍,Ben面對小混混面無懼色,但鐵蘭卻有多重困窘,她要當陪酒小姐、被男人欺負,最後更慘死。兩片複製了主流黑幫片的局限,把男性定義為強者、女性歸類為弱者。[3]而且,黑幫元素亦削弱了電影的寫實性:例如Ben看來家境不錯,跟鐵蘭是兩個世界的人,但這種階級差異少有着墨;至於電影充斥追殺場面,亦令戲劇細節及人物性格未得以好好發揮。
香港的缺席與存在:《投奔怒海》及《上海假期》
許鞍華的旅程電影題材甚廣,《投奔怒海》及《上海假期》就跟以上幾部截然不同。這兩部電影一沉重一輕快,一部講越南的政治局勢,一部講上海的親情故事。在成績方面,前者成了港片經典,後者則少有人討論。不過,兩片卻有共同點:它們都似乎跟香港沒有關係(《投奔怒海》關於一個日本記者去越南採訪,《上海假期》關於一個在美國長大的小孩去上海跟爺爺相處),然而,香港卻以缺席的姿態存在。
《投奔怒海》當年贏盡票房、口碑、獎項,後來入選「百部不可不看的香港電影」及「最佳華語電影一百部」。這當然是香港電影,但那是不是個香港故事?主角芥川汐見是個親越南的日本左派記者,越南政府要作政治宣傳,邀請芥川參觀他們的「新經濟區」,但他很快發現當局只是粉飾太平,人民在越共統治下其實過得很苦,大家只想逃離越南。在亂世中,誰都要投奔怒海。
電影以有力的影像拍出越南慘況,同時亦隱約跟香港有所聯繫。片中夫人一角是中日混血兒,十四歲就做人情婦,跟過法國人、美國人、日本人。她開一間酒吧,主要做美國人生意。她的華人血統,以及她在不同人種與政治勢力的夾縫中生存,對照着香港的複雜處境。另外,電影在1982年上映,適逢中英兩國就香港問題展開談判。片中對越共的描繪,被認為切中當時香港人的情緒。影評人焦雄屏指出,電影用了香港人的視角去呈現北越,透露出對共產統治的恐懼及批評。[4]「投奔怒海」的意象,也彷彿預言了香港後來的移民潮。一個日本人去越南的旅程,令香港人有微妙的情感投射。
在《上海假期》,香港同樣是缺席地存在。片中,上海老人顧大德(午馬飾)收到移民美國多時的兒子的消息,說要把他孫子顧明(黃坤玄飾)送到上海給他暫時照顧。這個在美國長大、滿口英文的小孩跟爺爺相處不來,又嫌中國落後,處處不滿。他遭遇的文化衝擊,對香港觀眾來說一點也不陌生。裏面的中美文化差異,大部份可以置換成中港差異。
一天,顧明離家出走,在上海郊區遇溺被救,才被中國的人情打動。電影的大團圓結局是:顧明終於「懂事」,明白爺爺的苦心,也彷彿接受了中國。電影探討親情、文化差異、中國發展,而國族認同是其中的重要主題。顧明被罵:「假洋人!」「你是中國人,憑甚麼用美國標準批評我們!」片末,爺爺亦循循善誘:「你幸運,比別人有更多選擇,但有些東西是不可逃避的,那就是你的膚色。」而顧明亦終於乖乖的不作反駁,默認這道理。另一點題的細節是顧明被郊區村民救起之後,晚上跟他們一起寫書法,他寫出「顧明」二字,導演用了大特寫呈現這兩個中文字。那一瞬間,顧明似乎跟他的根源接通了。
這就是電影的最可議之處:顧明的確有點無禮任性及嬌生慣養,但他的懺悔竟要透過某種「認祖歸宗」來達成,教養問題一下子變成國族認同問題。彷彿,只要這小孩不丟棄中國人的身份,他的任性無禮就立刻可以解決。但這小孩要學的,明明應該是禮貌與尊重。而且,他在美國土生土長,認同美國文化也很合理。
吳念真的劇本有人情趣味,但用國族召喚去處理文化衝突,便過於簡化及天真。最明顯的例子是顧明在學校被教導「熱愛黨、熱愛祖國、為人民服務」,老師講述一個小孩為了救火而葬身火海,教他們要勇於犧牲。但顧明聽不入耳,他說:「學校為甚麼不教在火災中如何求生如何救火,只教他們犧牲?」這想法,自然被校方視為不敬。這牽涉的,是教育制度的差異。而制度面對的問題,並非單靠「認祖歸宗」可以解決。
在九十年代初,中國內地在改革開放下已有急劇變化。然而,當香港人身處內地,仍要面對種種文化差異的衝擊,到今天仍然如是。所以,《上海假期》雖然沒有香港,但電影的旅程仍潛藏香港視角。只是,那些衝擊是否那麼輕易可以單靠認同中國身份就能化解?

《投奔怒海》用了香港人的視角去呈現北越,透露出對共產統治的恐懼及批評。
個人的也是政治的:《客途秋恨》
《客途秋恨》是許鞍華的半自傳電影。這部電影表面上是一個香港女子尋訪家族歷史的時空之旅,但又同時牽涉香港歷史,甚至是中國近代史,視野甚廣。電影當年在香港票房一般,也沒贏過甚麼獎項(只在台灣金馬獎得過最佳劇本),但是,它不只對許鞍華來說是一部意義重大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回答了「香港是甚麼」這關鍵問題的電影。
故事講述張曼玉飾演的曉恩自小跟陸小芬飾演的母親關係惡劣,她在英國讀完碩士後回香港參加妹妹的婚禮,繼續跟母親衝突不斷。身為日本人的母親想回鄉一趟,曉恩陪她遠赴日本,終於瞭解母親的過去。電影使用多重回溯的方式訴說曉恩的家族史:她父親是軍人,二戰尾聲在滿洲國邂逅日本人葵子,生下曉恩;戰後,父親在香港工作,葵子帶着曉恩寄居在澳門的老爺奶奶家,兩老後來想「為祖國效力」,於六十年代遷回內地,而曉恩兩母女則在此前搬到香港跟父親共住。
曉恩一家看來是個普通的香港家庭,但家族史卻牽涉複雜的政治、身份、地域。早有學者指出,《客途秋恨》的個人經歷背後都是香港的文化政治。[5]曉恩父親是國民黨人,母親是日本人,祖父母心懷大陸,妹妹婚後移民加拿大;曉恩在內地出生,童年在澳門度過,在香港長大成人,後來在英國讀書。一家三代人,經歷二戰、文革、走難潮、香港經濟起飛、澳門殖民時代,還有從七十年代就有的移民海外潮。許鞍華也許只是要回溯個人成長,但她的家族史卻反映了香港發展、中國近代史,甚至是世界歷史。這些微觀與宏觀的歷史,盡在於電影畫出的那張地圖:香港、澳門、內地、日本、英國、加拿大。要尋找香港文化身份,就必須一一找出香港跟這些地方的關係。[6]
沒有了《胡越的故事》及《極道追踪》的黑幫元素,這部電影思考本土、探索身份更為深刻,許鞍華的女性筆觸也得以發揮。片中,父親常是缺席的,曉恩兒時他在外工作,曉恩成年後他又去世了,兩個女人成了焦點。然而,這個有關母女矛盾的故事,絕對沒有像肥皂劇般消費女性恩怨。她們的故事,恰恰代表兩代女人的流動經驗:葵子屬於戰亂時代,當時流動是相對痛苦的;曉恩屬於現代化的香港,有機會留學英國,她妹妹則移民加拿大,她們的流動是相對愉悅的。
片首,曉恩申請英國BBC的工作被拒,但白人同學卻有面試機會。她的英國生活輕鬆愉快,但又冷不防遇上疑似種族歧視事件。片末,她在香港投入新聞工作,在這城市找到一份認同。而夾在中間的全片重點,是她跟母親回鄉的一段戲。曉恩對母親的身世後知後覺,她中學時才知道母親原來是日本人;到了日本,當母親一筆一筆寫下「平野葵子」四字(這個細節跟《上海假期》如出一轍),已經廿多歲的她才知道母親的真姓名。[7]如此重要的家族史,曉恩懵懂不知,就正如在英國無憂無慮的她不會去思考香港。
她小時候,葵子因為語言不通而終日沉默寡言、脾氣古怪,煮的日本菜又被老爺奶奶嫌生冷,家庭並不和睦,這母親在她眼中一直是個怪人。後來在香港,葵子大概因為生活圈子窄,常常在家打麻雀,亦令她反感。在日本,曉恩終於看到一個「正常」母親:她有哥哥、父母、朋友、舊情人,她會跳舞,會開心笑,會講流利的日文。與此同時,曉恩自己卻因為語言不通遇到種種尷尬與誤會,她身陷母親當年在港澳的困窘。當兩人在日本傳統浴室中一起洗澡,肉帛相見,也意味着母女的和解。
在最陌生的環境找到根
為甚麼一個香港人的身份尋索之旅,要走到最陌生的日本鄉村?如果許鞍華是要尋根,那些根(眾多的根)竟在最陌生的國度、最疏離的環境尋獲:在日本,她懂了母親,清楚了父母當年的異國戀,搞懂了她小時候的家庭矛盾。另外,在澳門,她度過了快樂中有張力的童年;片末,她回內地,瞭解祖父母對家國的執着。當然,還有她可能會再回去的英國,以及她妹妹的新家加拿大。無論是日本、澳門、內地或英國,都是她的家族史不可或缺的部份。《客途秋恨》故事主線是母親回鄉,但主題卻並非鄉愁,反而是要超越鄉愁;電影一再強調家的複雜、單一根源的不可能。許鞍華談到這部電影時說:「『鄉愁』只是一種傳統觀念,很多時候是一種逃避現實的negative feeling,不是positive feeling。」[8]
電影非常大膽的論點是:所有的「異域」都可能是自身歷史的一部份。定義香港,不可單單只看香港,而要追溯這個有複雜歷史與移民背景的城市,如何跟異地、異國、異文化產生關係。走過這趟旅程,曉恩回到香港投入新聞工作,報道反貪污的社會運動,那是七十年代──風起雲湧的麥理浩時代。她這樣說:「我第一次仔細地看香港人的面孔,聽他們的聲音。」彷彿,沒有之前的旅程,這香港身份就無法確立。
然而有趣的是,電影並非以香港作結。片末,曉恩回廣州探祖父母,她把在香港的一身時尚換上了白衫藍褲,並得知祖父母在文革中的苦況。祖父一直希望她傳承中華文化,找出《宋詞選》送她,卻被紅衛兵抓到,被盤問半天。他說:「不要對中國失望。」最後,南音〈客途秋恨〉徐徐響起,全片結束。許鞍華不只一部電影以回內地尋根作結:《男人四十》(2002)結尾,林耀國(張學友飾)跟文靖(梅艷芳飾)面對婚姻危機,他抱着她說:「去完長江回來再講(離婚的事)吧,我們讀了那麼多詩詞,應該要去一次的。如果再不去,到時三峽一灌水,很多東西就會消失了。」這在暗示,他們的共同文化認同有可能會挽救婚姻。許鞍華對香港的尋索,有時總帶一份中國情結。
然而,儘管有中國情結,電影指出香港歷史文化必然是複雜多元的,葵子這人物就是活在夾縫的人。她在女兒面前自傲於日本老家的家勢,卻在日本朋友面前誇耀香港就像東京;她跟哥哥重逢時說:「我一個人在外國生活,很苦。」隨後又對女兒說:「日本的東西太生冷,還是廣東菜好吃,我好想飲湯呢。」在中日夾縫中,她最後還是回到香港,跟七十年代許許多多的移民一樣,視香港為家,做個香港人──雖然在她身上,仍有抹不走的日本痕跡。她是夾縫特質(in-between-ness)的上佳例子,不屬於這,也不屬於那;這正是香港身份的微妙處,一種獨特的「香港性」。[9]
所有旅程都是香港故事
許鞍華電影的一段段旅程,骨子裏都是香港故事。學者洛楓提到,作為一個貿易港、移民城市、國際都會、旅遊城市,流動本來就是香港的文化特性,這孕育了許多離散文學及電影。[10]而旅程既是身體的流動,也關係到身份的曖昧多變,正如《客途秋恨》中兩母女的身份都是混雜模糊。
許鞍華從為勢所逼的離散(diaspora,如越南難民)講到當今舉世皆然的流動性(mobility,像曉恩兩姊妹去英國去加拿大),展現了香港難以定義的、無以名狀的文化身份。我們不必問葵子最後更認同香港還是日本,不必問曉恩會不會有天重返英國,不必問胡越這越南華人為何承載香港人情感,不必問投奔怒海的到底是越南人還是香港人,就正如我們不必追究,《阿飛正傳》中旭仔在菲律賓尋母不遂,為何不回香港,而《春光乍洩》中黎耀輝的回家之旅為何到台北為止,而何寶榮又為何從不眷戀香港。流動的香港身份,就藏身在旅程中、在異國土地上、在不同族群中。
後殖民理論大師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用樓梯比喻後殖民文化。[11]樓梯是很曖昧的過渡性空間,人們不會在此停留,永遠處於行進狀態;樓梯代表了身體的流動、無家的認同及文化的曖昧,那正是某種後殖民狀態,一種因為模糊曖昧而潛藏無限可能性的文化空間,可以抗拒保守單一的認同,如民族主義或原教旨主義。香港的旅程電影與曖昧身份,就為這種後殖民樓梯空間作出了很好的詮釋。
也許有人說,這種強調流動與曖昧的香港身份已經不合時宜,尤其最近幾年,「本土論」甚囂塵上,香港人要立足本土,建構清晰的身份。但是與此同時,今天關於香港身份的討論仍然莫衷一是:有人認同中國內地,有人眷戀殖民時代,而「城邦論」雖主張香港成為城邦,但又強調香港要繼承「華夏文化」,擁抱中華傳統。[12]另一邊廂,曾經消失多年的移民話題再度成為熱話,香港人再次考慮四散海外。城邦、華夏、戀殖、認同中國、移民海外,這些分歧正正說明:香港身份越是要說清,越是說不清;越是要聚焦香港本土,越要畫出一條一條的線,從香港連到不同地方。
這種曖昧模糊看似是某種缺失,但是,所謂牢固的認同其實才是虛妄的,混雜而變動的認同才是常態。亞巴斯有力地指出,香港文化身份的混雜不清並非一種病理,這種開放性是文化創新變革的契機所在。[13]在今天的全球化下,旅程與長途交通是現代社會的關鍵特性,不斷的流動驅動着社會變化。[14]過去二十多年,人文社會學科對此多有反思。以往,人類學的研究重點是文化與一個固定地方的關係,但文化其實是由流動的人所創造,也是不同文化混合交疊的結果。流動,是文化的關鍵部份。[15]
許鞍華的旅程電影訴說了香港心事,探索了香港身份,同時,這種香港特性連繫着一種全球文化。香港故事,正是某種有普世意義的故事。「到最後才明人生客路永沒平。」《客途秋恨》尾聲,梅艷芳的歌聲唱起這首遺珠之作〈秋天復秋天〉。人身為客,在大地走一回,路途從不平坦,路線並不單一,結局也很多元,所有尋找身份與建構文化之路亦如是。
[1]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5. 這句話原文是“[…]stories
about Hong Kong always turned into stories about somewhere else, as if Hong
Kong culture were not a subject.”
[2] 這種具備離奇的戲劇元素的新聞,似乎特別容易令人聯想到海外華人的悲劇。除了《極道追踪》,陳耀成導演的《錯愛》(1994)同樣以華人女性在紐約的地下鐵被推下路軌慘死的真人真事作起點創作。
[3] 《胡越的故事》及《極道追踪》的女主角是鍾楚紅,她在兩部電影中的形象及演出跟她不少電影頗有不同,她素淨清麗,演技自然流露,不用賣弄性感。但另一方面,兩片的黑幫陽剛味卻沒有給她發揮空間。當年,她息影前夕透露希望再拍許鞍華作品,《極道追踪》令她如願以償,可惜效果仍不理想。
[4]
焦雄屏:〈前言:九七震盪:宿命、懷舊、寓言〉,《香港電影風貌1975-1986》,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頁191-193。
[5]
Lisa Odham Stokes and Michael Hoover, City
on Fire: Hong Kong Cinema, New York and London: Verso, 1999, p.145.
[6] 同註1。
[7] 曉恩對自己家族史的後知後覺,令我想到電影《胭脂扣》(1988)的細節:永定及楚娟四處追尋十二少下落,有一天,二人走進他們工作處附近的一間古董店,終於從舊報紙找到當年如花及十二少的殉情新聞。永定住在西環,但對當地的妓院史似乎一無所知;本土歷史明明就在身邊,古董店明明近在咫尺,但是,一向沒有歷史意識的香港人卻很少去發現。
[8] 鄺保威編:《許鞍華說許鞍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0,頁45。
[9] Audrey Yue 曾在其分析《客途秋恨》的專書中探討片中的親密關係及離散如何交集,但本文因篇幅所限沒法就此展開討論。見Audrey Yue, Ann Hui's Song of Exil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10]
洛楓:《盛世邊緣:香港電影的性別、特技與九七政治》,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159。
[11]
Homi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12] 陳雲:《香港城邦論II:光復本土》,香港:天窗出版社,2014。
[13] 同註1。
[14]
Scott Lash and John Urry, Economics of
Signs and Space, London: Sage, 1994.
[15]
James Clifford, 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1-24.
* 本文節錄自《許鞍華 電影四十》,蒙三聯書店(香港)及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