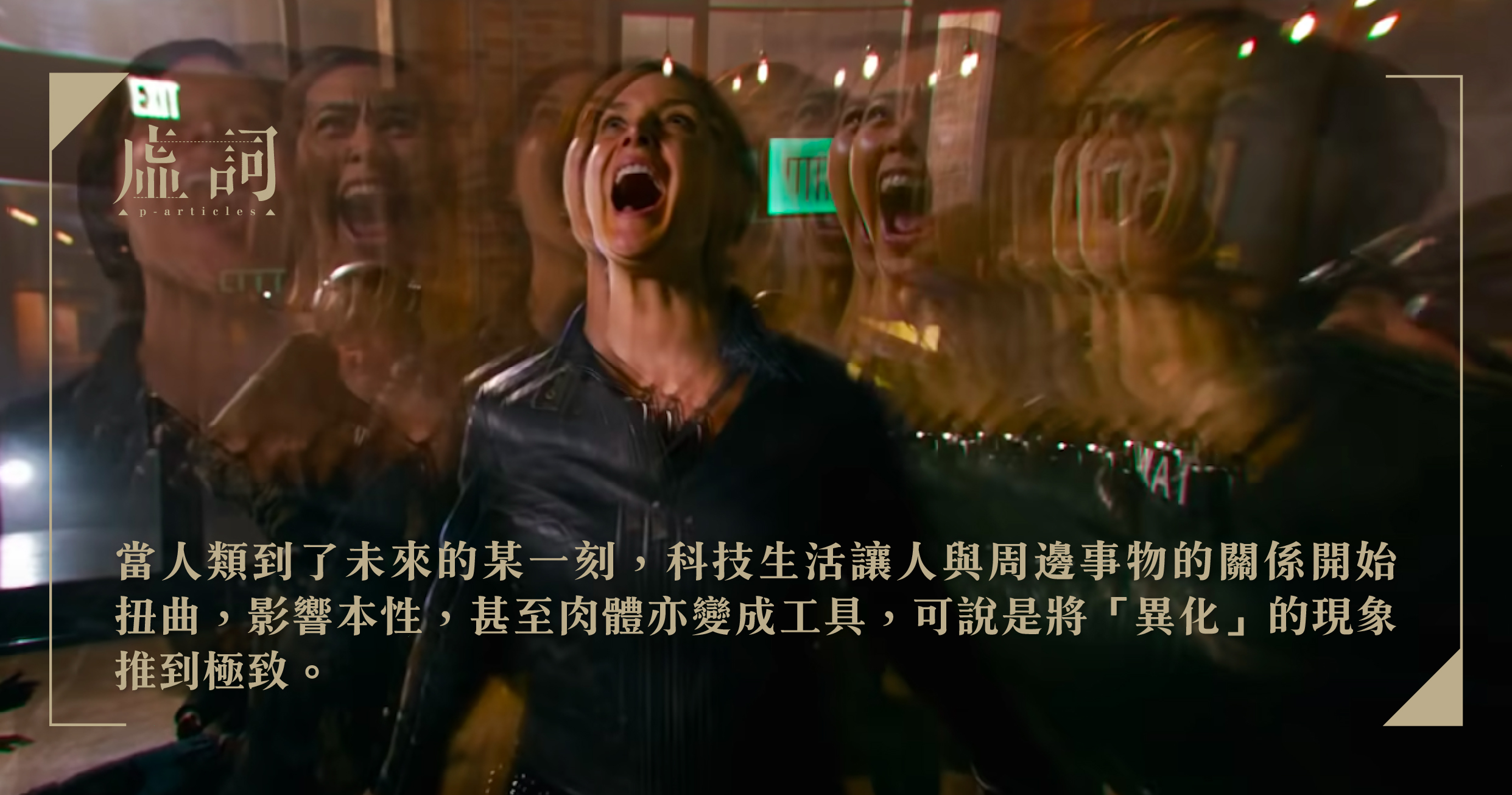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警告:極致異化
二十年前華卓斯基兄弟(現在應該叫姊妹)的《廿二世紀殺人網絡》(MATRIX)哄動全球,帶出一股荷里活功夫熱與及人與科技、虛擬世界的討論。作為一套後現代風格的電影,無疑它對於電影創作及社會都有很大的影響。當年電影提出對未來世界的憂慮,今天看來,非但沒有消失,而且還一一實現。藉著《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第四集上映,本文藉機回顧前三部電影之餘,並帶出一個甚少人提及的電影主題:異化(Alienation)。讓觀眾在進場看第四部前,能再多一層的思考。
《廿二世紀殺人網絡》,除了電影版所說的三集外,還有一連串的動畫故事。縱合所有故事,人們可以從中起碼知道一個故事背景:人類高度發展下,製造出永久使用不用休息的人工智能電腦,但機械的高度發展使人類愈感威脅,於是人類發動攻擊,欲重新操控電腦的核心「母體」(MATRIX),最後卻失敗了,成為「母體」的一部分。整個故事的大綱,本身便是人類被「異化」的圖像。因為電腦,「母體」是人類製造出來的產物,是生產出來服務人類的,但最後卻變成受電腦控制、奴役。
異化理論(Alienation),在原先的意義上又可指為疏離,在不同的語境運用中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意義。現時最常引用的是黑格爾及馬克思的說法:人與本性產生的自我疏離是由自我做成的。人經由物化的過程創造了自我的本性。在黑格爾的學說中,物化是精神的過程,而馬克思則認為是勞力。馬克思他觀察資本主義工業生產過程時,指出工人對於生產方式漸漸失去控制,甚至失去對生活及自我的控制。工人從來都不是自主、自我實現的人類存在,他只能以資產階級給予他們定型的模式而存在。從電影具體來說,當人類到了未來的某一刻,科技生活讓人與周邊事物的關係開始扭曲,影響本性,甚至肉體亦變成工具,可說是將「異化」的現象推到極致。
物化與無意識的異化
在《廿二世紀殺人網絡》的世界中,人類的意識生活在「母體」製造出來的幻象之中,肉體則被「存放」於一個個液體容器內,由插頭與電腦連接。可以說,人們在「母體」中雖然有著各式各樣的生活與工作,實際上他們最大的功用只是作為母體主機的電池,提供電腦運作的能源。動畫版本敍述起源時,有一幕顯示一個嬰兒身體被電腦裝上插孔,再插上插頭,存放於液體容器中密封。然後一個遠鏡畫面顯示一個「母體」正連繫著數以萬計的容器,當中又有數百計的「母體」。這個畫面具體地呈現出人類被「物化」(objectification)。人類不再是人類,而只是一塊電池。當人類的價值被物化時,便出現了馬克思指的「物化(objectification)乃是異化的實踐。」(1) 而共通之處是,「母體」中的人類,仍是「在一個異己的實體支配下來從事生產活動。」,而且,他們是沒有意識的。
或許這裡再詳細說明什麼是無意識異化。再以馬克思所說的宗教為例,為什麼宗教信徒就是無意識的異化?馬克思所說:「人們若全神貫注於某個體系時,便只能以一個異己、幻想式存在,來將他的本質加以客體化。」(2) 莫斐斯一生中都相信神使的預言:人類當中會有一個救世者。於是他找到了里奧。在里奧的能力不斷醒覺後,他更相信神使的預言是真理,甚至令錫安中大半人都相信這個語預言。在電影《決戰未來》時,拉克指揮官對莫斐斯說:「不是所有人都相信你這一套。」但是當里奧在錫安步出升降機時,無數錫安平民都向他求助。這一幕就如一個個信徒在朝聖一樣。救世者的存在及神使預言就是錫安人類的宗教。可是,「母體設計師」卻道出一個可怕的「真相」,救世者的存在卻是母體中定期出現的一個錯誤。而里奧已是第六次的錯誤(第六代救世者)。救世者回歸萬物之源正是為防這個錯誤失控。那就是說,母體是人類的產物,而救世者是母體的產物,但人類卻去相信,膜拜這一個產物。就如莫斐斯一樣,去將自己的生命意義投放在里奧身上,甚至為他犧牲生命。他不再是人,而是客體化為一個「殉道工具」。他的行動不自覺被神使及里奧影響,甚至控制,「在一個異己的實體支配下,來從事他的生產活動」。而莫斐斯的生產,就是向錫安的其他人宣揚里奧是解救錫安的救世者(傳教)。這樣看來,莫斐斯推廣的自由,與及所謂的「選擇」,實際上都是是受神使及里奧影響的「沒選擇」。在「母體」中的人們,他們在意識上是被電腦蒙蔽(而電腦本是人類的產物),讓自己以為自己在正常生活,有自由、有選擇、有工作。實際上他的肉身卻被物化為一塊電池。身體的能量被提供成為電腦運作的能源,直至死的一刻。這樣看來,在錫安的人與母體中的人其實並沒有太大分別,只一是一個被宗教控制,一個被電腦控制。
越工作越貧乏
在「母體」中,「母體」利用程式鋪設的世界告訴人們,他們是在1999年,但現實世界卻是2699年(而這個真相連錫安的人也不知道,他們流傳的資訊亦有誤)。人類在不斷地「母體中」生產,實際上是不斷消耗自己(供電),而「母體」則不斷獲得能量運作下去。「工人愈努力工作,他所創造的與他自己對立的對象世界就變得愈有力量,他的內心生活就變得愈貧乏,他屬於自己的就愈少。」(3) 唯一不同的是,人類愈努力工作不會得到愈少,而是從一開始,他們就一無所有,所以根本不存在多與少的問題。
錫安是人類能真正生活的地方,是人類反抗「母體」的天堂。而莫斐斯他們就是不斷從「母體」中尋找有反抗意識的人,將之解放出來。同樣道理,如果所有的人,都像首集背叛莫斐斯的發電機先生,只想沉醉於虛擬中,或是全神貫注地為「母體」生產,那樣反抗的力量就會愈來愈弱,而「對立的對象世界就變得愈有力量」。然而,有趣的是,「母體」是完全地操控著人類的,但是卻又有人類在反抗它。為什麼人類能反抗它呢?如「母體」的設計師所說,錫安的存在,其實也是「母體」所允許。讓錫安存在,目的是為了從另一個角度觀察人類,讓母體製造的世界更真實,亦因為母體的能量來自人類,故此人類必須被保存而又要防止他們坐大。故此,雖然錫安已被「母體」毀了5次,但仍要安排少量人類重建錫安,形成不斷的循環。可以說,人類與母體是一個相互依賴的關係:在母體中的人類需要母體才能生存,就如人類即使被異化,也需要工作才能生存(要從工作賺取金錢、食物等);「母體」亦要人類才能繼續運作下去,就像生產系統、資本體制要人類的參與才能進行一樣。但因為要維持這個體系的運作,故此在錫安的人(像現實中的無產階級)必須受控,而且要在少數。
於是可以看到,社會中有些少數派(可能是共產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就如錫安中的人類一樣,試圖反抗資本主義及生產系統所帶來的埋沒人性本質的影響,但更多的人,就加入了「母體」,成為當中的一份子,被勞役,服務自己的敵人。
人在工作中是會迷失的。
不論在母體還是在錫安,都是著重秩序規管。在首集中,里奧被上司白先生訓話:「你挑戰權威……認為自己出眾,規距不適用於你……本公司是世上最頂尖的軟件公司,僱員都知道是公司的其中一份子,僱員有問題,公司都有問題,你要作出抉擇,可選今天開始準時上班,或另謀高就……」這一段話有趣的地方在於,它反映了人們身處的地方,不論是電影中的母體,還是我們的世界,都有一個共通點:世界就像一間公司,我們都是公司的一份子(僱員),人們有問題,世界亦會有問題,於是公司這個權力系統便要規範人們,使人們順服。否則便要不順服者離開(在母體,莫斐斯等駭客就是不順從的人,要被消滅),用傅柯的說法,每個人都是被一個權力系統控制了。重點是,這種控制導致了人們因為不想被邊緣化,又或是為了生活,就要作出順從權力的舉動而工作。里奧那樣未被莫斐斯解放前,在白天,他是某間一電腦公司的電腦程式員,但觀眾知道他是具有反叛行為,他不想過著刻板,講求秩序的生活,可是為了不被辭退,他亦選擇了順從,在被訓話完後,他說「明白了」。里奧是有自由傾向,不愛受束縛,愛思考。所以講求秩序,機械式的工作無疑是與里奧本性相反的。他完全演釋了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說的:「勞動對工人來說是外在的東西,也就是說,不屬於他的本質;因此,他在自己的勞動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發揮自己的體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體受折磨、精神遭摧殘。因此,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勞動中則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勞動時覺得舒暢,而在勞動時就覺得不舒暢。因此,他的勞動不是自願的勞動,而是被迫的強制勞動。」
這種強制勞動,正是里奧白天工作不快的原因。在公司當一個權力的一部分,被控制著不是他自己。他自己是渴望自由的,當莫斐斯問他相不相信命運時,他答否是因為「不喜歡命運不由他控制」。所以里奧在晚上是一名電腦黑客,史密斯說他破壞了所有電腦法律,正是一種渴望打破權力的表現。
有一點值得懷疑是,當他醒覺成為救世者後,這個身份究竟又有沒有否定自己的成分,相信里奧自己亦搞不清楚,救世主這身份究竟是工作還是他自己的本性。如前所說,如果他的本性是反抗權力,那麼,救世者這個身份可能亦是另一個工作。因為救世者是母體運行時一個錯誤而產生。那這個身份是母體這個權力所賦予。他在母體中有著強大的能力,但仍是受到控制,這種控制來自母體的祭師及建築師。祭師是系統其中一個程式,但里奧等人卻受他的指引行動,所以祭師其實只是另一個控制系統;而救世者回歸萬物之源見建築師,正是另一個控制系統,以防救世者失去控制。那麼,他這個救世者的命運其實亦不由他控制,豈不是與他的本性相反了?那麼,救世者豈不是一種強制勞動?更可怕的是,因為全人類的安危在里奧身上,他沒有選擇權不去做,而且慢慢接受了,順從了這個工作,所以他有事便會依賴祭師的指引。他是壓抑的。尼布甲尼撒號在錫安補給期間,給了里奧一個休息時間。當電梯中所有人出去了,只餘下里奧與崔妮蒂時,他們二人立即擁吻纏綿一番。另外還有一幕是,當所有人在聖地跳舞時,唯獨他們二人離群,在房中「翻雨覆雲」,這兩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里奧其實是極希望放下救世者的身份的,正如他在出電梯後,一眾市民圍著他時,他叫崔妮蒂不要走,說「我需要你」,但崔妮蒂卻說「不要緊,他們更需要你」。於是,里奧留下了安撫眾人(繼續工作但繼續犧牲)。即使在與崔妮蒂一起時,他亦放不下他的工作,因為在他的腦海中,不斷閃過一些與母體有關的畫面,崔妮蒂被殺的畫面。不論在「母體」中﹑在錫安,他都在工作中不斷否定自己。所以,里奧無論在母體內外,都是被異化了的工具。
到目前為止,在電影中都反映出他在母體的行動和在船上的行動。很少關於他工作以外的片段(如和崔妮蒂做愛的那段,但都反映了他的異化特徵),那麼里奧的本質是什麼呢?如果說「工人只有在勞動之外才感到自在」,但電影中里奧何時何地都像在工作,那是不是他的生活不會自在?又好像不是。再閱讀電影時,可以發現了里奧在兩種情況下是比較「型」的:一次是他剛開始學功夫時,他爆了一句粗口,然後沉醉在當中十小時。然後在跟莫斐斯對打時是面露笑容,很開心。賽若膚說,只有通過打鬥才能分辨救世者的身份,那是否打鬥就是里奧本質的流露?另一種情況是在他飛行時,飛行是他獨有的能力,他是喜歡飛的。在第一集片尾飛過,在第二集,林克說他「又在耍超人的那一招」,他的樣子是無可奈何的。我們可以推想,里奧應該是不只一次地飛來飛去,而且是好型地扮超人飛來飛去(當然,有什麼十萬火急時,里奧是不會這樣,例如莫斐斯和崔妮蒂被雙生子追殺)。我們不妨假設,在非急救狀況打鬥與飛行時,就是里奧的閒暇時間。或許我們可以作一個推測:功夫是一種力量,一種工具,幫助里奧反抗權力,保護他想要保護的,故此里奧在打鬥的過程是快樂的,是很「型」的(他最常做的一個手勢叫人去打他)。而飛行是另一種可以幫助他在危急時趕得切救人的能力。這兩種能力都能讓他流露自我的。這種自我本質是什麼呢?馬克思在他的手稿中,提到了人的本質的解釋,是取自費爾巴哈哲學中表述人和整個人類時所用的術語:「真正人的生活……以愛為前提,這些都是人類的自我感覺,或關於個人屬於人群這種能動意識」。那麼我們可以嘗試結合母體設計師對里奧的觀察得到結論,他說前五代的救世者都有一種悲天憫人的特質,而里奧則將這種特質轉化,發揮出另一種不同的特質-愛情。里奧的本質是愛的話,那麼正好與馬克思和費爾巴哈的人的本質是以愛為前題建立關係的論調吻合。人們便會明白,為何里奧知道崔妮蒂快死時,他的飛行速度是史無前例地快的(林克說從未見過這麼快的東西),亦明白為何救世者的能力覺醒,是要崔妮蒂吻了他,里奧才會復活,才會成為救世者。因為要喚起救世者的本質,便需要愛吧。
(1) 雖然馬氏這裡說的物化,是人們若全神貫注於某個體系時,便只能以一個異己、幻想式存在,並且受一個異己的實體支配下來從事生產活動。在這裡,他用了宗教作例子說明,而與Matrix中相同之處是,同樣有一個超越人類的權力形成一個實體,控制人類,同樣地Matrix 中對於救世主的定位,亦像一個宗教。Karl Marx, Early Writing,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T.B. Bottomore,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P.36
(2) 同上。
(3) Karl Marx, Early Writing, P.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