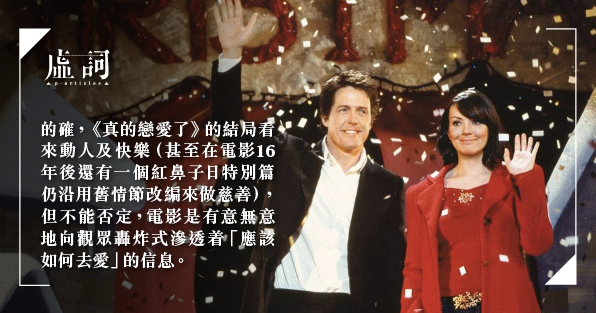真的戀愛了還是被逼戀愛了?愛情電影給予觀眾的糖衣藥
愛情主題的影視作品,不論事後影評是好是壞,總會有一定的吸引力。近來話題度較高的《12日》又是另一例,與前作《12夜》一樣的利用片段式的述事,濃縮了講述一個實際以年計的關係過程,這種表述方式在有限的片長中的確能做到較為簡潔有力的效果,但因為主角的關係像章節跳躍,亦可能令觀眾難以適應。不過本文並不是談《First Love》及《12日》。說到片段式述事的愛情經典作品,最令筆者印象深刻的電影莫過於二十年前的《真的戀愛了》(Love Actually),一套輕鬆小品但又令觀眾印象深刻的多線愛情故事,去年聖誕節前見《好集慣》提及這電影踏入二十周年,在全球各地仍然銷量大賣,是每年聖誕節必備的節目(註1)。對這個讚譽,筆者的確不能同意更多,但同時,本文想從另一個角度談談這套電影的經典之處——它揭示了人們所身處的環境,並不是能單純地自主選擇的行為模式,人們的愛究竟是一種自願還是被逼?其實可以有很大的討論空間。的確,《真的戀愛了》的結局看來動人及快樂(甚至在電影16年後還有一個紅鼻子日特別篇仍沿用舊情節改編來做慈善),但不能否定,電影是有意無意地向觀眾轟炸式滲透着「應該如何去愛」的信息。
首先,電影中的主角們對愛都有一種共同看法,就是聖誕節要去跟最愛的人度過,而且要在聖誕節中說「真話」。這看似是理所當然的事,問題在於是誰人規定如此。傅柯曾指出性、愛與權力的關係時,指出「人們不是有自由去做,而是被一個權力(Power)所牽引去做」(註2),在電影中,甚至在現實中可以想想,為什麼原本為了紀念耶穌基督降生的聖誕節會變成世人示愛的日子(變相成了另一個情人節?)在電影開首給了我們答案。比利(BILLY)這位過氣搖滾歌手,以一首《Love Is All Around》重新包裝成《Christmas Is All Around》,正是將愛(Love)等同了聖誕節(Christmas)。他在宣傳這首作品時,是透過一個又一個傳媒(電台、電視)去宣揚「聖誕節要去愛」這個信息。正如這就解釋了為什麼主角們都要在聖誕節去追求愛,因為都受到了一股「權力」(Power)——傳媒所影響,傳媒往往營造了一種氣氛、潮流去讓人追求。類似的事情在現在其實仍經常發生,除了上文說的《12日》,近來還有一個關於《First Love》的故事,有報導指台灣有對情侶女方因看了《First Love》後決心要去找回前度而與現任男友分手,筆者不知這類的例子是不是孤例,但以上例子也的確反映愛情這類主題的影視作品(甚至加上特定某些節日播放)向來對大眾行為的影響是鉅大的,此外,現實中人們已習慣一到了西方節日除了消費,就是充斥一類聲音:要買禮物給伴侶、要出「Pool」、要找人陪。電視、電影、互聯網也會跟隨潮流發佈一大堆愛情作品或重溫(寫文這天剛剛見「試當真」就發了一條「泰妹」做主角的MV《Christmas Gift》,又是以愛情為主題的音樂作品),廣告也不斷提及與你心愛的人過節之類。
若不理會傳媒是否可以脫離權力的控制呢?
不幸地,媒體只是權力系統的一部分。另一個是社會教育。故事中,Sam(《移動迷宮》湯瑪士‧桑斯特飾,小時候真的可愛又很英俊)與Daniel(地上最強老爸里安.尼遜飾)正是普羅大眾的寫照:Sam從小便被父親教導要如何去愛。事實上,在家被老爸教育如何去愛的過程,與學校性教育堂教導學生要如何處理性基本一樣,在傳統的思維中,性與愛本身都是一樣——需要別人教的。或許我們會替Sam有一個較開放的繼父而高興,會教他如何去追求愛人,但社會上更多人則是被教導小孩子應該讀書不應談戀愛,於是出現了一些到現在已十分過時但仍然有一代人會奉為圭杲的規條,如中學生不應談戀愛的經典說法。不論是那一種情況,其實亦反映人們被這個權力大系統控制,貫輸觀念。正如傅柯所言,對性我們不是單純的說對與錯(Yes or No),而是究竟是誰人說才重要(註3)。因為說話者所說的不一定是事實,只是論述和傳釋,當中是懷有目的。Daniel這個父親教導兒子什麼是愛,要如何去愛時,他只是不斷地貫輸他自己那一套愛情見解,是他的個人看法,但不一定正確,畢竟世上每個人的「愛情路」都不同。毫無疑問,他的動機是希望與Sam這個兒子建立一個良好關係。在教導Sam如何求愛的過程中,二人溝通多了(而且Sam專注愛情,Daniel就不怕他去吸毒)。這個才是他的目的,也像傅柯理論中提及性不是亂說,而是有目的性地說(註4)。由此看來,性不是亂說,愛也不是「亂教」,同樣具有目的性。一個的目的是生育及建立家庭,另一個目的則是讓青少年有精神寄托,兩者同樣地有穩定社會的作用。
眾所周知,即使女性主義不斷發展,現代社會仍是一個父權為核心的系統。這個權力系統的源頭是什麼?從婚禮那一段,可以知道這個源頭來自人們「天上的父親」(「上帝就是愛」的觀念),故此,人們要結合的時候理應要回到「父親」的面前作見證。再看婚禮後半部Mark(《The Walking Dead》男主角安德魯.林肯飾)所造的驚喜,這個驚喜有趣在神父(Father)是有份參與的(看二人「give me five」的擊掌便知了),寓意了愛是由「父親」所教導的。在這幕中令人最不自覺地進入陷阱的是這個驚喜《All You Need Is Love》這首歌,洗腦地告訴人們,你們需要愛,單是「All you need is love」及「love is all you need」這兩句便出現了至少十五次,「Love」這個字亦出現了三十八次。這一幕戲完全表現出一個行動是:一個父親(神父)正在一個「父權空間」(教堂)用音樂將愛這訊息「轟炸」進人們的腦子中。可說是另一種的「強逼教育」:由父親教導孩子們你們需要愛。
父權空間是什麼?就是一個父親角色的人物(其實可以身體結構上是女性,但思維是男性思維,例如慈禧太后便是一例)擁有絕對的權力,絕對控制的環境。教堂是一個父權空間的濃縮。在教堂中,天父(Father)是最大的,他是世界的源頭,每一個信徒來到祂面前是要俯伏跪拜的。祂的話語、戒命、律法(Law)每個人都得遵守,這就是父權法則(The Law of The Father)的形成。由於天父是至高無尚(高到看不見),於是神父,即是天父的地上代言人,成了父權空間中最高者。聖經的律法,事實上已變成了今天的道德標準(這得力於西方世界在中世紀以來多年政教合一的情況,就算到了啟蒙運動以後,宗教思維仍深入人們骨髓)。於是父權空間得以擴大,即我們身處的世界,也就是一個父權空間(社會)。
婚禮這一幕還有另一個含意,所有的愛情到了終點便是結婚。結婚是要在教堂,是要在這個父權空間中進行的,這反映了人們的愛情實則受父權所監控。在這裡我們也看到,愛與性的同一個目的,就是建立家庭,生兒育女,因為聖經也說「你們要生養眾多而且遍滿全地」,這是父權中其中一個規矩。這也就進一步說明了,愛與性同樣是被權力系統建構出來。
教育、宗教、傳媒形成了一個更龐大權力系統。而三者合力對愛及性作出了一個「合理」定義:每個人都需要愛與被愛;聖誕節是一個要跟愛人說真話(示愛)的日子;二人交往的終點是要結婚;組織家庭必需要有小孩,因為性的功能是生育,故性行為必須要有愛情作基礎,一夜情、縱慾是罪惡,「非陰道性行為」是不當的。沒有人能夠離開這個系統去追求愛。不是嗎?電影中的那對三級片替身演員John (馬田.費曼飾,之後不再當床戲替身,先跟福爾摩斯查案,之後又做了哈比人,近幾年還當了「CIA」去瓦崗達幫忙)及Judy(祖安娜.佩吉飾),他們的相識是從拍色情電影開始,故此即使二人只是替身演員,但他們的關係仍可說是從「性」開始,不過他們為了建立一個「正常」關係,亦要重新透過認識-了解(工作時傾計,由社會上的話題變成個人話題)-約會(在聖誕節)這個過程以發展愛情。John約會Judy是要勇氣的,從他的表情而及他害怕被拒絕,人們便知道他十分緊張。這種緊張的成因不難理解。因為如上所說,權力系統告訴人們,人人都需要愛,求愛是必須。也就是權力生產了性出來後,使人覺得性是人的慾望(註5),而性本身是要有愛作為基礎,於是愛亦變成了必需品,在這種思維下他自然害怕失敗。而且,當他失敗了的話,他二人的性行為便不能「名正言順」的繼續下去。這個「名正言順」當中包括了經濟因素、家庭及道德觀念在內。二人工作關係只能符合社會經濟因素:色情電影抒發了一眾「飢餓人士」無法發洩的慾望,有助穩定社會及促進經濟;但是在沒有愛情基礎的情況下,John的內心會有一種罪惡。只有結婚組織家庭才能化解這種思想。故此為什麼最後在機場時二人跟碰到劇組同事Tony說訂婚了要去渡蜜月時,John會說了一句:「這回終於可以名正言順了。」這一種「名正言順」的觀念正是權力系統給予人們的:當權力建構了性出來後,又要不斷打壓它,使人在特定的環境中才可以說(註6)。這個特定的環境就是在二人訂了婚之後,可以光明正大的去建立家庭,去幹那一回事。當人們都遵循這一個法則:求愛、結婚、組織家庭、生育、教育下一代。一代一代的人都去遵守時,社會便持續穩定,權力便得以永續。
事實上,這個「名正言順」的觀念,只不過是John受到了權力影響下,將自己問題化(problematize)了。令人困擾的是人們總是被一些好像是事實(truth)的概念所影響,人們病態地(ill)信服的道德概念(關於性及愛的疑惑、我們覺得不名正言順不行)都是被建構出來的(註7),只要那個人深受權力系統影響(像John一樣),「名正言順」的觀念根深蒂固。那麼他就會不斷去反思,覺得有問題、有罪疚。為了擺脫罪惡,他仍會返回或順從權力所設定愛的方法。
既然人們是深受「權力」影響,那麼我們求愛未必是出於我們的本意。反而只是因為權力系統、從小的教導、社會上意識形態所影響,以致人們都要去跟從這一種法則。遇到阻力時亦要努力去衝破它。所以《真的戀愛了》幾個愛情故事都是叫人們打破階級的阻隔勇敢去愛,故事只是以大團圓作為結局,但極有可能在往後的日子人人都是分手收場(雖然續篇中仍然見到他們都是有情人繼而有情人,但續篇就沒有了John and Judy,他們只是訂婚,可能未必結得到婚)。這種鋪排使人在為故事感動的同時,無形中鼓勵他們,以免人們因有阻礙而放棄愛。電影最後一幕,所展示的無數個框架,同時告訴人們自身是怎樣受到一個權力系統的框框限制。既然愛只是權力系統所建構出來時,那當我們去跟從其他人(或是順從權力教導)去追求愛情時,我們未必是「真的戀愛了」,而是「被逼戀愛了」!
雖然本文透過傅柯的理論,寫了一大堆陰謀論的分析,但《真的戀愛了》仍是筆者最喜歡的一套愛情+節日電影,無他,因為輕鬆、有趣吧(當年的曉治‧格蘭的確很有魅力很吸引觀眾)。當然,說到權力恐怖如斯是否就不用去愛呢?老土一點說,其實要愛一個人,又何需要等到節日裝作浪漫才去示愛,才刻意找伴?每一年的聖誕、新年、情人節、坊間的媒體資訊、家中的長輩都會不斷關心大家的愛情生活,外加生日、各式各樣的紀念日,好像特定的例行公事要做一些儀式感強的東西,在這種氣氛下,大家不妨俯心自問:今天你是真的戀愛了,還是被逼戀愛了呢?
註:
1. 好集慣:〈《Love Actually》20周年演員重聚 聖誕再看一遍〉,https://www.facebook.com/betterme.magazine/posts/pfbid0Urj3ZG7BqRQfW2ov67VnmxpRbQJvEc75NiaDxws4p6EbNJurUgyWkmjZdRZjTV9Yl,檢視日期:2022年12月17日。
2.“in short, with this genealogy the idea was to investigate how individuals were led to desire, a hermeneutics of which their sexual behavior was doubtless the occasion”Michel Foucault, The Use of Pleasure. Volume 2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0, p5.
3. “The central issue, then ,is not to determine whether one says yes or no to sex, whether one formulates prohibitions or permissions, whether one asserts its importance or denies its effects, or whether one refines the words one uses to designates it; but to account for the fact that it is spoken about, to discover who does the speaker, the positions and viewpoints from which they speak, the institutions which prompt people to speak about it and which store and distribute the things that are said.” 同上注,p5-6.
4.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Vintage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1990, p3.
5. “by creating the imaginary element that is sex, the deployment of sexuality established one of its most essential internal operating principles: the desire for sex- the desire to have it , to have access to ot, to discover it, to discover it, to liberate it, to articulate it in discourse, to formulate it in truth. it constituted sex itself as something desirable”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156.
6. 同上注。
7. “What are the games of truth by which man proposes to think his own nature when he perceives himself to be mad; when he considers himself to be ill; when he conceives of himself as a living, speaking, laboring being; when he judges and punishes himself as a criminal? What was the game of truth by which human beings came to see themselves as desiring individuals?” Michel Foucault, The Use of Pleasure. Volume 2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p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