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為陳詞濫調定錯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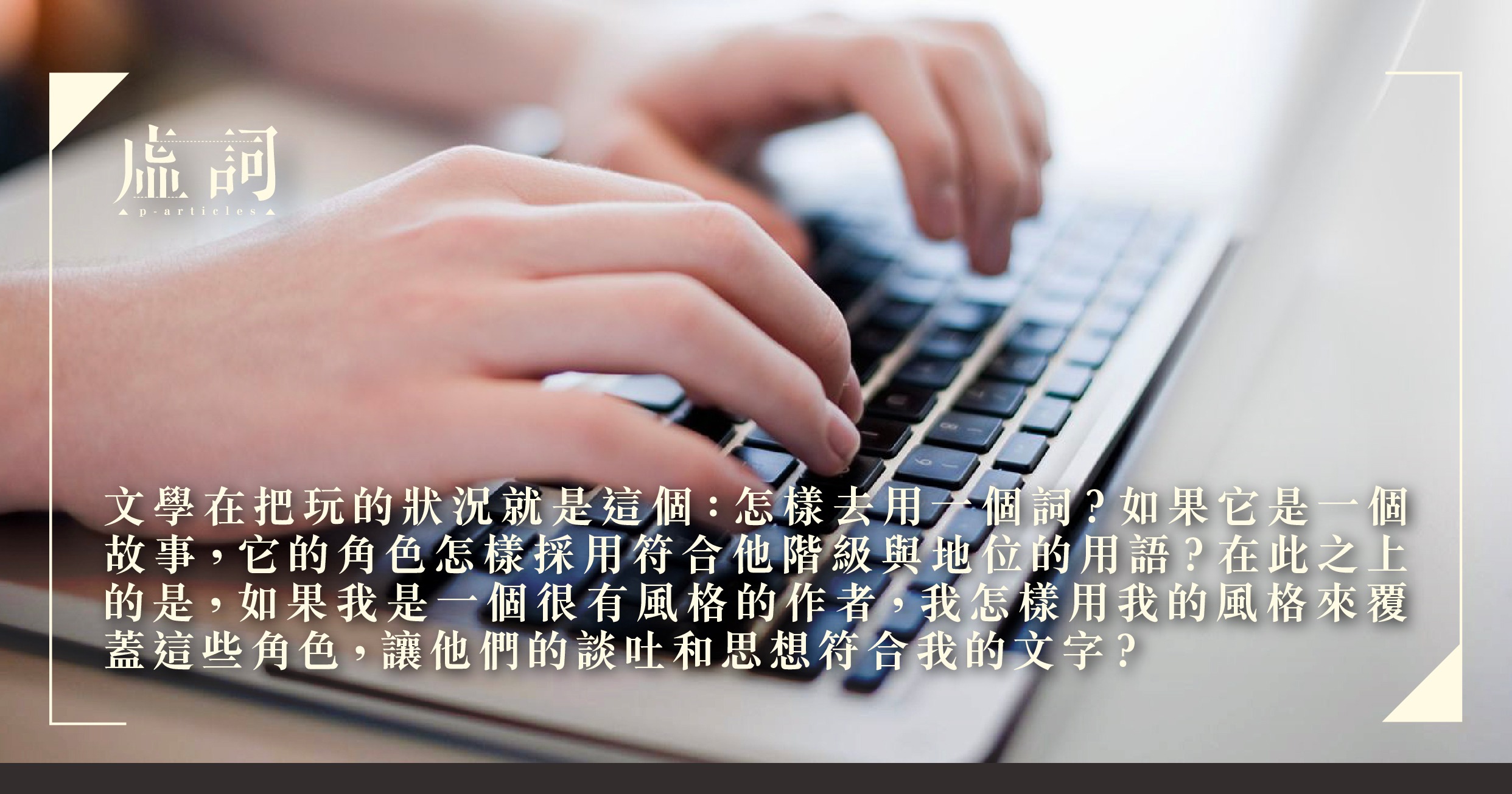
274497804_281821540761239_2926319241766292181_n.jpg
每個人都有討厭某些用詞的權利,比如我討厭還記得、娓娓道來,打造等等;有人會討厭視頻、音頻、網紅等等。每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討厭詞庫」,因為這代表我們對語言是敏感的,可以在無聊的日常中找出使人不適的因循守舊。
這個詞庫代表你的社群、出身背景和美學取態與其他人不同。我們說自己討厭某個用詞,通常不是因為這個詞本身,而是指向那個詞的使用者。換言之,語言只是個藉口,是個前哨戰,單純講自己討厭哪個字和分析它的源起都是假動作,這個詞庫真正的意義是:去攻擊這個詞庫的用戶。讓他們吃屎,叫他們弱智,滾回他媽的懷抱吧。比如當有人說他討厭視頻這個詞,是因為它來自中國,這確實無可厚非。
不過這種攻擊很容易會誤中友軍,很是危險。比如說,當他討厭「視頻」,又沒有去罵身邊鋪天蓋地的「打造」時,一定會被更專注於語言的人反將一軍。然後當然是熟悉的扣帽子,貼標籤,反諷譏笑,網絡嘴炮組合拳。這種時候最用力攻擊他的通常不是敵方,而是前一秒的友方,因為他不夠純粹,對教義不夠熟悉,是個被污染的人了。結果下場就跟九成的網絡罵戰一樣,不了了之。
好似有一條專業的鏈條在那裡,必須找出最精準的用法,並且否定其他人的用詞,顯得自己最懂運用語言。否定這個動作很值得玩味,因為語言本身就是否定性的。比如隨便舉個例——香蕉好了——香蕉這個詞就否定了其他不是香蕉的東西,用排除法剩下這種東西,就命名為香蕉了。所有的語言都是這樣,否定其他東西,擠出一個空間給自己。視頻是這樣,達人是這樣,網紅也是這樣。原理一樣,效果不同。
當然,這種方法必然是鬆動的,這也是為甚麼我們會說語言是變動的。從錄像到錄影到影片到視頻,從厲害到犀利到勁到屌到牛b,從紅到hit到潮到火(以上不按順序),總有更多新詞建立起來,因為新是一種無法擺脫的宗教,而人到某個年紀就會不再接受新事物。於是很不幸的,這些用詞必然帶來用戶的互相否定,比如說太老或太年輕、太中國或太其他地方、太造作或太淺薄。講來講去,都是人與人的互看不順眼。一句到尾就是不溝通了。
而文學在把玩的狀況就是這個:怎樣去用一個詞?如果它是一個故事,它的角色怎樣採用符合他階級與地位的用語?在此之上的是,如果我是一個很有風格的作者,我怎樣用我的風格來覆蓋這些角色,讓他們的談吐和思想符合我的文字?怎樣讓風格進入我的人物,讓語言進入我的讀者?這些問句加入起來的意思是:當你一個文字工作者,本來就知道一些字是某些人在使用時,你怎麼就不直接罵他們呢?你只不過是認為他們與你不同,有時更瞧不起他們不夠你有文化。語言只是個華美的藉口,語言是一襲華美的袍子,在你眼中人人都是虱子。
法國文學家布朗修就著陳詞濫調寫了一篇文章,剛好就叫做〈文學如何可能〉,因為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就是文學的根本了。他劃分了兩種人:A,完全反對陳詞濫調,把陳詞濫調的使用者叫做弱智的人;B,支持慣例,支持既有風格的人。
關於完全反對陳詞濫調的人:「一些人反抗語言,因為他們從語言中發覺一種不完美的表達手段,因為他們希望語言是可理解性的一種徹底的完美化。如此的野心導致了甚麼?一種語言的發明:一種沒有陳詞濫調的語言,一種沒有表面之含糊的語言,其實就是一種不再提供任何共同尺度且徹底擺脫了理解的語言。」
關於支持慣例的人:「另一些人反抗語言,因為語言被視為一種過於徹底或太過完美的表達手段,因此不是一種文學的語言。並且,因為他們的無情要求,因為他們對一種不可通達的純潔性的關注,他們最終抓捕種種的慣例、規則、體裁,直至完全地放逐了文學。」
這篇文章的核心在於,無論是反對老土或是支持守舊也好,過了火就沒有朋友。厭煩只是一個表徵,我最厭煩的三個詞——還記得、打造、想問問——現在通街都是,但我知道它們的用戶也只不過是用起來方便。美學判斷不應該引致人身攻擊。當你跑去罵一些人用詞弱智時,其實也無補於事,因為「如果作家知道,他越是反抗陳詞濫調,他就越是受束於陳詞濫調,或者,如果他得知,他只是在他憎惡的幫助下寫作,那麼,他就有機會更清楚地看到其力量的範圍和權威的手段了。」
去攻擊某些用詞,絕大部分都是攻擊一個團體;攻擊這個團體的目的,是因為自己恥於為伍。但最常見的狀況是,每個人語言的界線都或多或少有點重疊,但又有些優越感,比別人更懂。陳詞濫調這場仗最令人煩躁的一點是:每個人都以為自己發明了這場仗——難道只有我覺得這個、沒有人發現了那個——不是,所有人都覺得了,只是我們在思考要怎麼使用這些詞語,或是直接棄用,而不是隨地撒尿。沒有辦法接受老套事物的人,是最最老套的;總是覺得別人是錯的人,總是錯的。
關於陳詞濫調,前陣子有個天才的網民發現了只要用幾個詞語,就能回覆所有對話:真假、確實、亂講、冷靜、有料、救命、笑死。這些全部都是陳詞濫調,但它們確實能回覆所有的話,而且還很好笑,那麼,我們就應該直接跑去討厭它們老套嗎?因為它們不雅,發明者又是個沒有權威的網民(極大可能是個異性戀男性),就直接棄用嗎?
布朗修在文章最後提到,一個作者最應該做的事是不屈服於陳詞濫調,但與此同時,他要「能夠製造它們」,「接受規則,但不把這些規則當成一條指引路線」,因為「只有陳詞濫調能夠把思想從反思的畸變中拯救出來」。
語言是否定的,這是它的本質。但我們除了去跟一些陳詞濫調說不以外,更重要的是扭轉它們的用法,或創造些新的詞彙來取代它們,不是老說不要不要的,這樣看起來總像掙扎。比如說,如果「大師」這個詞不能用了,要用甚麼?大佬嗎?所以布爾加科夫的著作應該叫《大佬與瑪格麗特》?策蘭的詩叫〈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佬〉?
而我總是很喜歡陳詞濫調的新用法,比如說成語的語言遊戲,又或是直接誤用一個詞。必然有人會說這是「錯」的,但哪來甚麼「對」的?從來都只不過是群體跟群體的衝突而已,如果我們真的尊重語言也想為自己的團體出一分力,那就發明一點新東西給大家吧。笑死。
(標題為編輯所擬,文章轉載自作者facebook專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