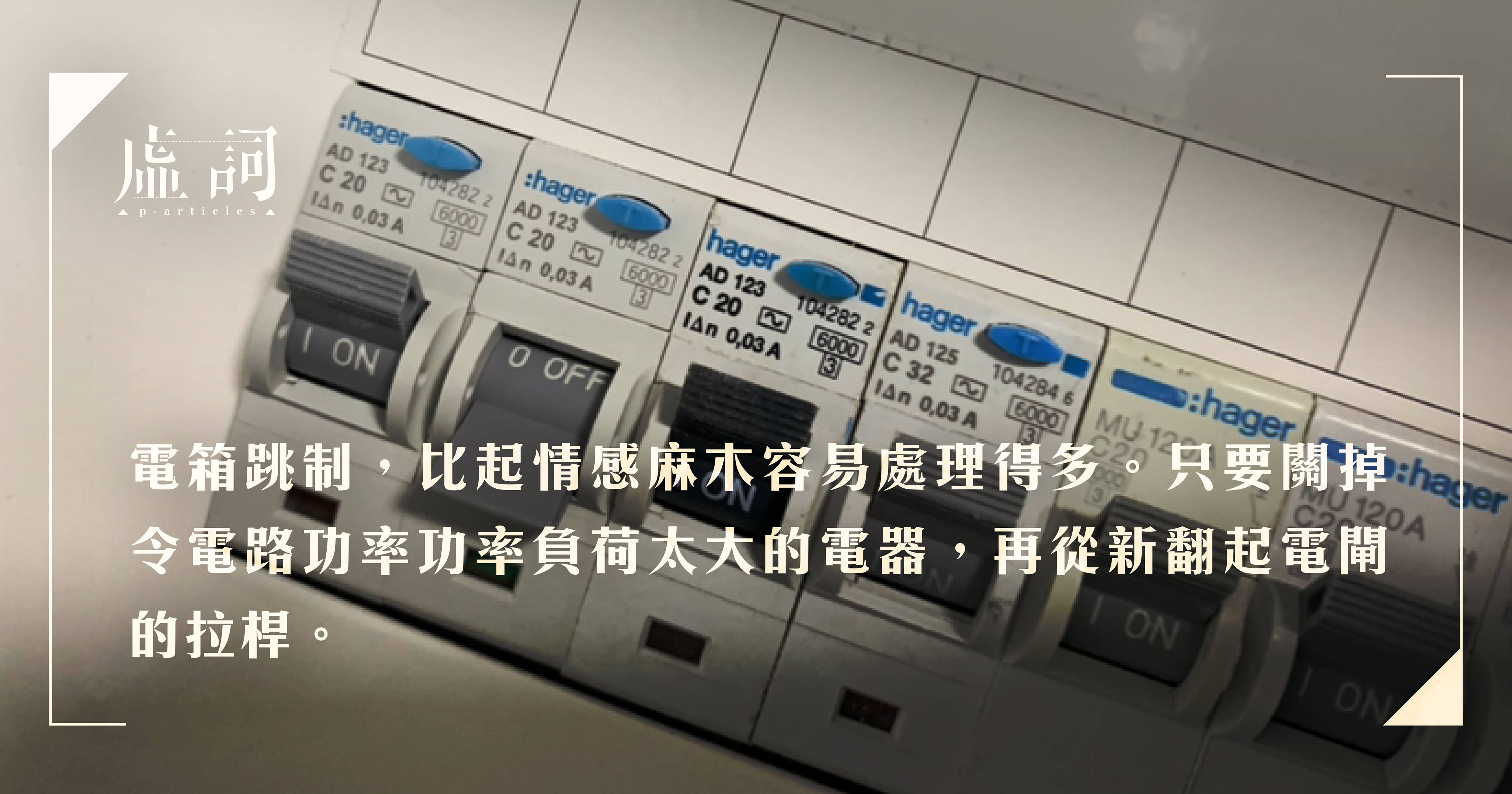電箱跳制
散文 | by 詩子 | 2021-06-27
情感麻木,就像大腦的電箱跳制。
首次體悟到這種麻木,是小學五年級。當時住家門口斑駁的水泥地,在烈日與雨水長年澆蓋中長滿裂縫與皺褶。我失慎踏在某日雨後從縫隙中冒出頭的黛青苔面上,腳趾奮力夾著的人字拖抓不住地,坐骨與尾椎同午後灼熱地面熱情地擊了一掌,聲音響亮。手上原來端著盤準備到後院喂雞的冷飯殘羹,在半空中翻滾過一圈又一圈後,鐵盤低朝上扣在我圓滾滾的小腹上。我坐在地上,雙掌撐著地,菜汁混著油滲入了衣服褲子,濕濕黏黏地貼著肚皮,冰冷的觸覺蔓生到大腿與臀部。
摔得響亮,卻不太痛,屁股上堆滿可作避震的脂肪,所以沒有傷及骨頭。這種皮肉的疼痛,總如拋向平靜湖面的小鵝卵石,起初響亮清脆的聲響在靜謐中,可以嚇得湖面上釣魚翁不住抖動身體,而後陣陣漣漪隨之泛開,一圈圈淡卻,再眨幾下眼,石塊的身影就墜入湖水中,與水汽一同蒸發不見。
只不過,一想到不知能不能褪色的衣服,想到要洗澡、洗頭、掃地,想到雞要挨餓一陣,這樣那樣在腦海中絮絮叨叨的道道思緒,不受控滾作一團,打起了死結。那瞬焚起的心煩,大約是與曖昧對象在高級餐廳吃過午飯後,發現自己原本潔白新衣的顯眼位置,濺上了一片污漬時那種煩躁,乘以十倍。
想來也是自己活該,當時穿著那雙劣質聚丙乙烯製拖鞋,鞋底早被磨蝕成一片平滑光面,我卻不願意更換。以及衣櫃中早以塞滿,因鬆緊帶疲乏而糾作一團的內褲襪子、羅紋扭成麻花炸開的圓領短袖衫。也不知是為了甚麼,無法拋棄這些緊貼著我生長的衣物,即使它們成長的速度已超越我,不再是體面的衣物,甚至會危及自身,卻始終無法坦然迎接它們的消逝。這份壞習慣也一直無法割捨,緊貼著我生長至今。
當瞬狼狽的我,腦中只閃過出門前見到的畫面——媽媽就坐在進門後,隔著五六步遠的木製沙發上,哄裡著襁褓中的小弟弟看電視。我只想逃過此後待著的沈重責任,坐在原地發愣四五秒,便決心要放聲大哭。我想,只要哭得夠大聲,即使擠不出淚來,她也會出於疼惜,為我解決一部分麻煩。即使懷抱著這種心思的小學生,實在太過工於心計,一點都不可愛。
媽媽並沒有陷入我粗製濫造的母愛陷阱。她確實抱著弟弟出門來瞥了我一眼,淡淡然地說,小弟弟已經睡著了,別哭得太大聲。在日光中泛著光圈的漆黑烏鴉,縱情向瓶中擲入石頭,卻不喝水,放任溫熱的濕潤徑自隨之溢出,於是我的淚便確實流出來了。不敢作聲吵醒弟弟,只能在原地躺下啜泣,試圖用自己化作一灘水窪的身體淹死腳下那片青綠。
躺在空曠地面哭了約莫半個小時,都沒有誰再來看過我,屁股早已不疼,淚水也再溢不出眼眶,悲傷似乎隨著淚溜走了,流得一滴不剩。我沒有任何感覺,不想哭也不想笑,只決定要站起身來收拾遍地的泥濘,再從廚房找到些快過期的麵包去喂那群可憐的雞。這是我最後一次在媽媽面前不顧廉恥地嚎啕大哭。
後來聽人說,蚊子親吻出的癢,之所以會被指甲用力按壓刻出的十字掩埋,是因為深沈的痛,總可以漫過那些薄薄鋪在表面的不適。
電箱跳制,比起情感麻木容易處理得多。只要關掉令電路功率功率負荷太大的電器,再從新翻起電閘的拉桿。
本應是件容易的事。不過高中時,我是個活脫脫的生活白癡。在獨居的家中,跳閘的夜裡,手機沒有電,又找不到手電筒或者蠟燭,只是隱約記得電閘裝在廚櫃靠天花板的某一隅。所以癱軟在床上作了一陣無用掙扎後,便放棄了抵抗現實的不留情面。
那是我第一次發覺,被囚禁在軟弱的人類軀體中,在無光的黑夜,除去睡覺,軟弱無能的我無法促成任何改變。屋裡一片漆黑寂靜,脫下眼鏡後,眺望對面樓道,別人家的燈火裡粼粼和煦的黃與冷豔的白。因為雙眼近視且散光,即使度數不深,遠遠眺去,對岸的燈光在彼此重疊又過分暈染的朦朧邊界中,撐開了一片迷離徜仿的星光閃爍。
情感麻木。無力自觀的當下,再如何按動按鈕開關,光都不會照耀。只能看著遠方縹緲閃爍的燈火,冀望從中尋一絲慰藉。
所以我並不感到訝異,當我從鐵絲網覆蓋束縛著,囚籠似的行人天橋,邁過橋底下滾滾車流與塵埃,一步步走近,推開閘機冷冰冰的旋轉桿子,在兩旁保安的熱切注視中邁入那處熟悉又陌生的校園。時對於自己全然沒有預料中的情緒波動,只感到出奇平靜,並不訝異。
第一次拜訪這間大學,是隨中學老師來聽物理講座。講座的內容早已忘光,只記得,這間學校的建築有種過分整齊乾淨編織出的迥異及混亂。不留空隙填滿的紅橘色背景,每棟樓幾乎劃一的外觀樣式,都在竭力碾壓我可以在世界中佔據的小小空間,似整個人被浸沒在一片猩紅的海中,擠壓的力量無孔不入,拉扯著我沉下去,沉下去。
對於本就有點路癡的我而言,用字母去標示那些看起來一模一樣的建築,就像生了十幾個同卵十幾胞胎的家庭,用規律的名字命名這群孩子。仔細考慮過便會明白,無論是喚作ABCD又或一二三四,都不會有助於外人辨別他們。所以當我身在其中,總是不清不楚如墮五里霧中。當時只覺得它像一座迷宮,後來才發現,它更像一座監獄。
像我進入過的唯一一座監獄——域多利監獄。兩處的磚紅色外牆與方正樓房,在迷糊記憶中相互重疊延伸,且同樣漫散著使我不安的氛圍。不過域多利監獄,顯然在時間洗刷下已經褪色。一座是舊監獄,一座是新監獄。
在大館依靠現代技術偽造出的陳舊氣息中,有一片「胡志明的天空」,飄搖在兩面紅牆夾著的狹隘走道間。站在其中仰頭望去才發覺,每日披在頭頂的天空,竟不比低矮紅磚墻要高上多少。囚牢就似從腳下土地繁衍迸發出的林木,沿著矮牆爬上天,茂盛得不留一絲空隙,長成一口深邃的井,我們站立在井底,無處可逃。那時的胡志明大概不會想到,在未來某日,這整座他鄉城市長出的繁盛森林間,處處都是那樣的天空。
而我亦是到最近才後知後覺,在懸得離地面特別近的天幕下,這整座城市,本就是一片昏亂紛雜的迷宮。從此地生長過,每一顆落地生根的心都早已走不出去。無論那些鐵絲網、閘機或囚牢存在與否,所有逃亡,都不在計畫之中,亦無法實行。我只妄圖著,可以替困在此地的每瓣心靈,拔起無法承受的負荷與傷痛,再次拉起電閘拉桿,點亮你的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