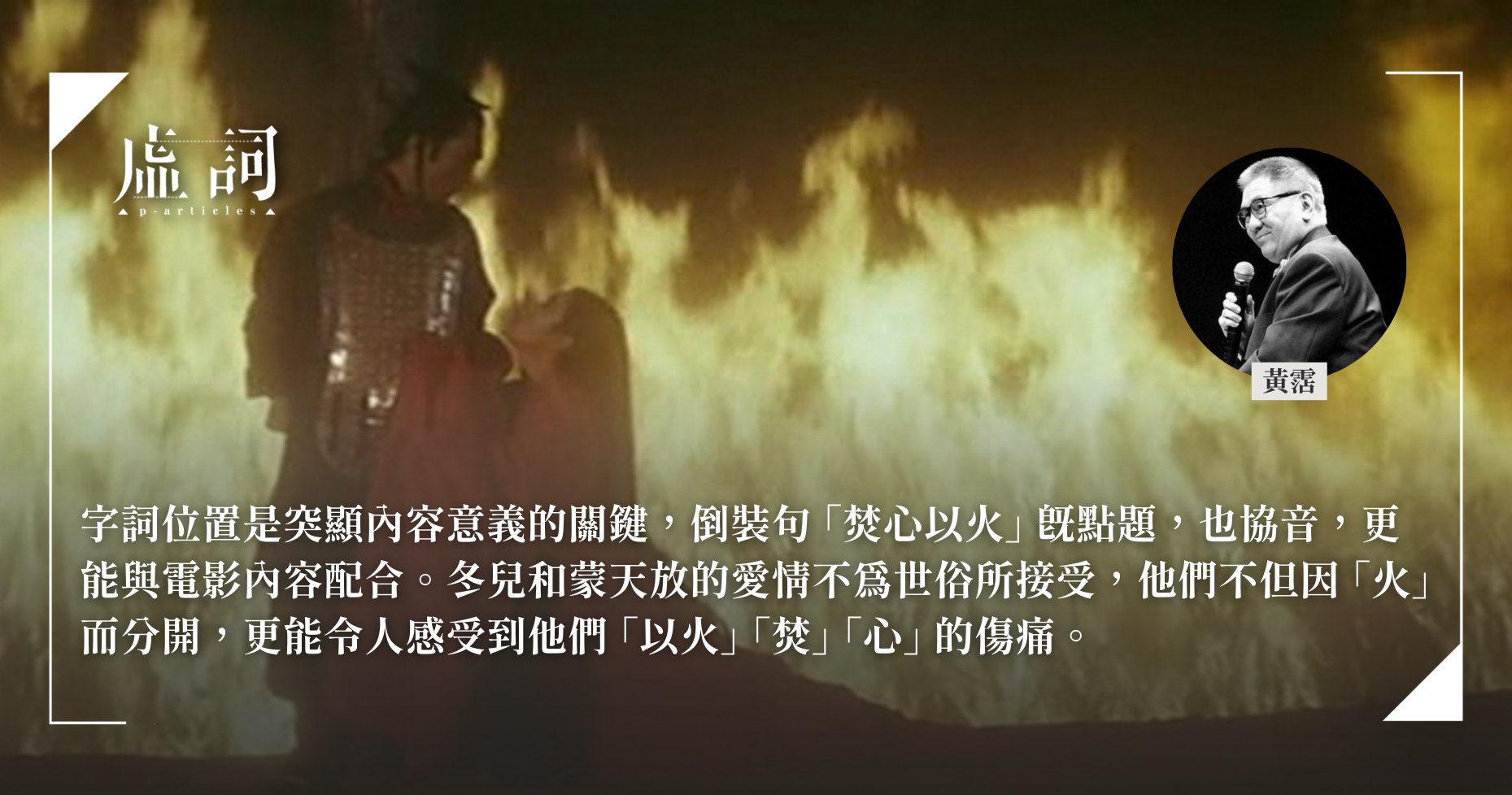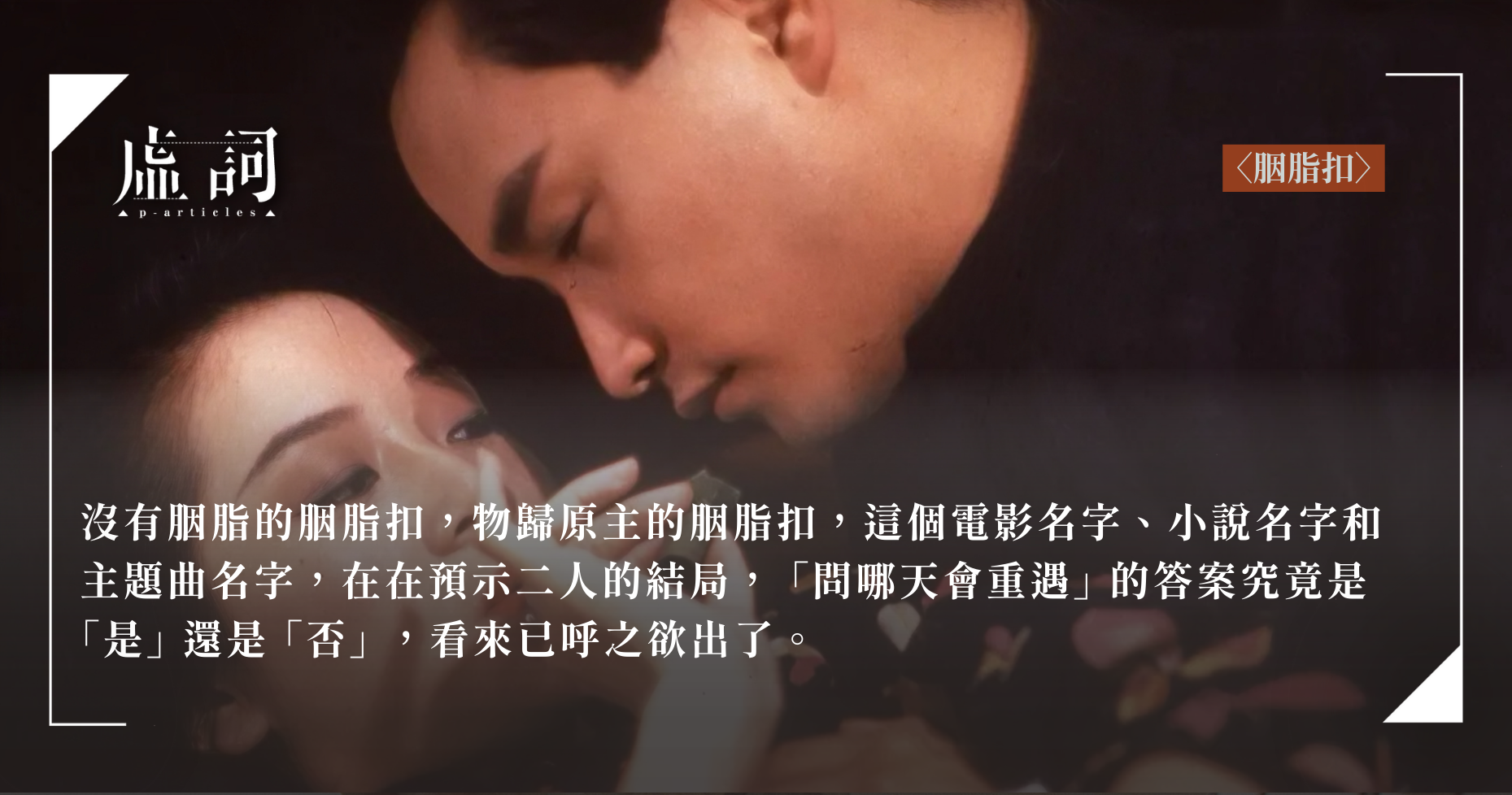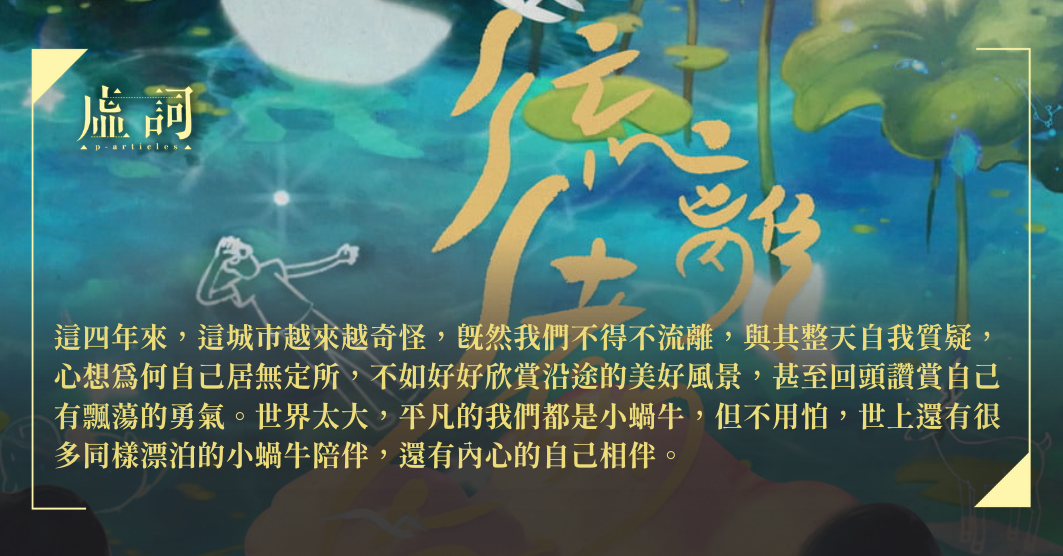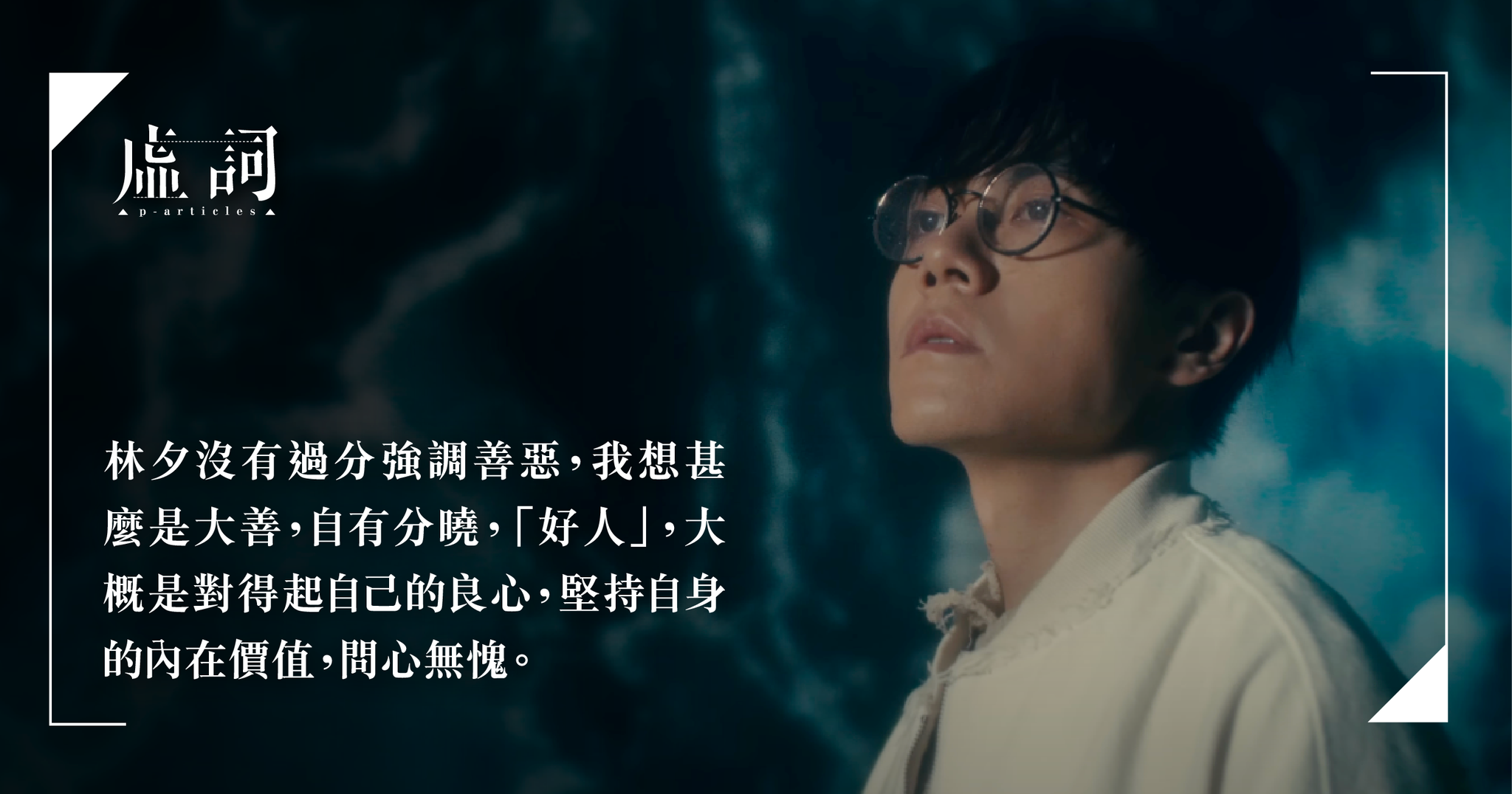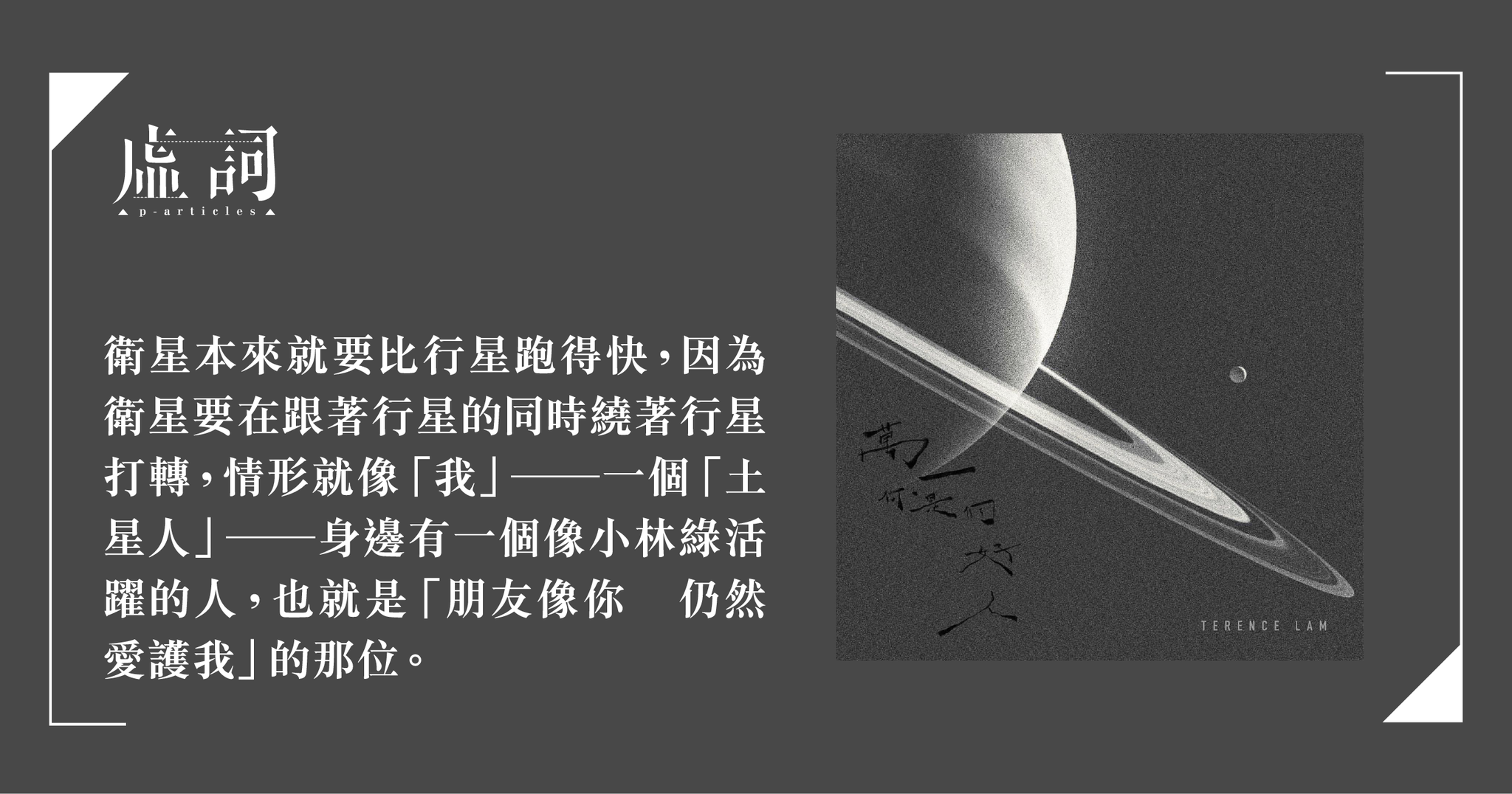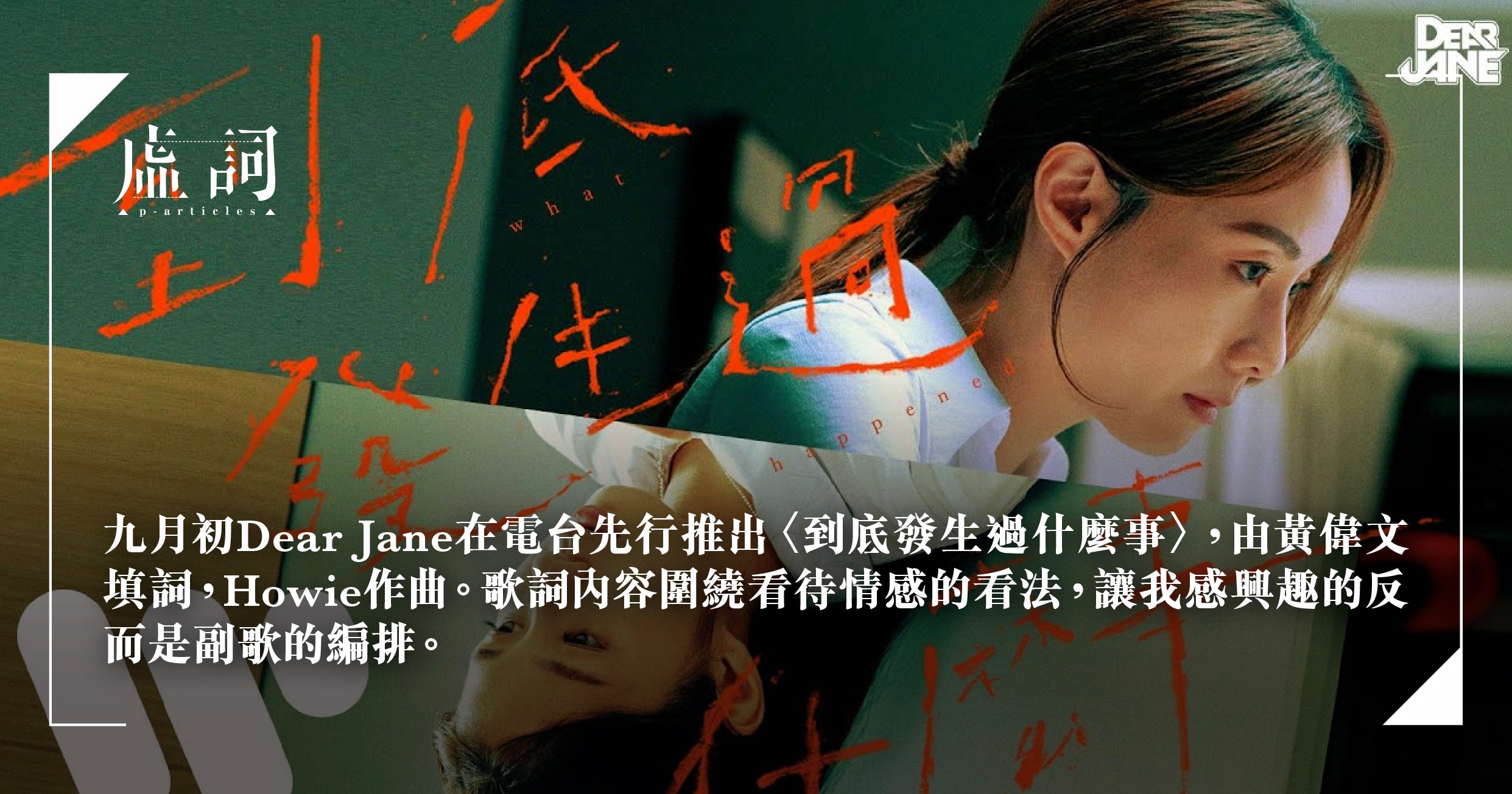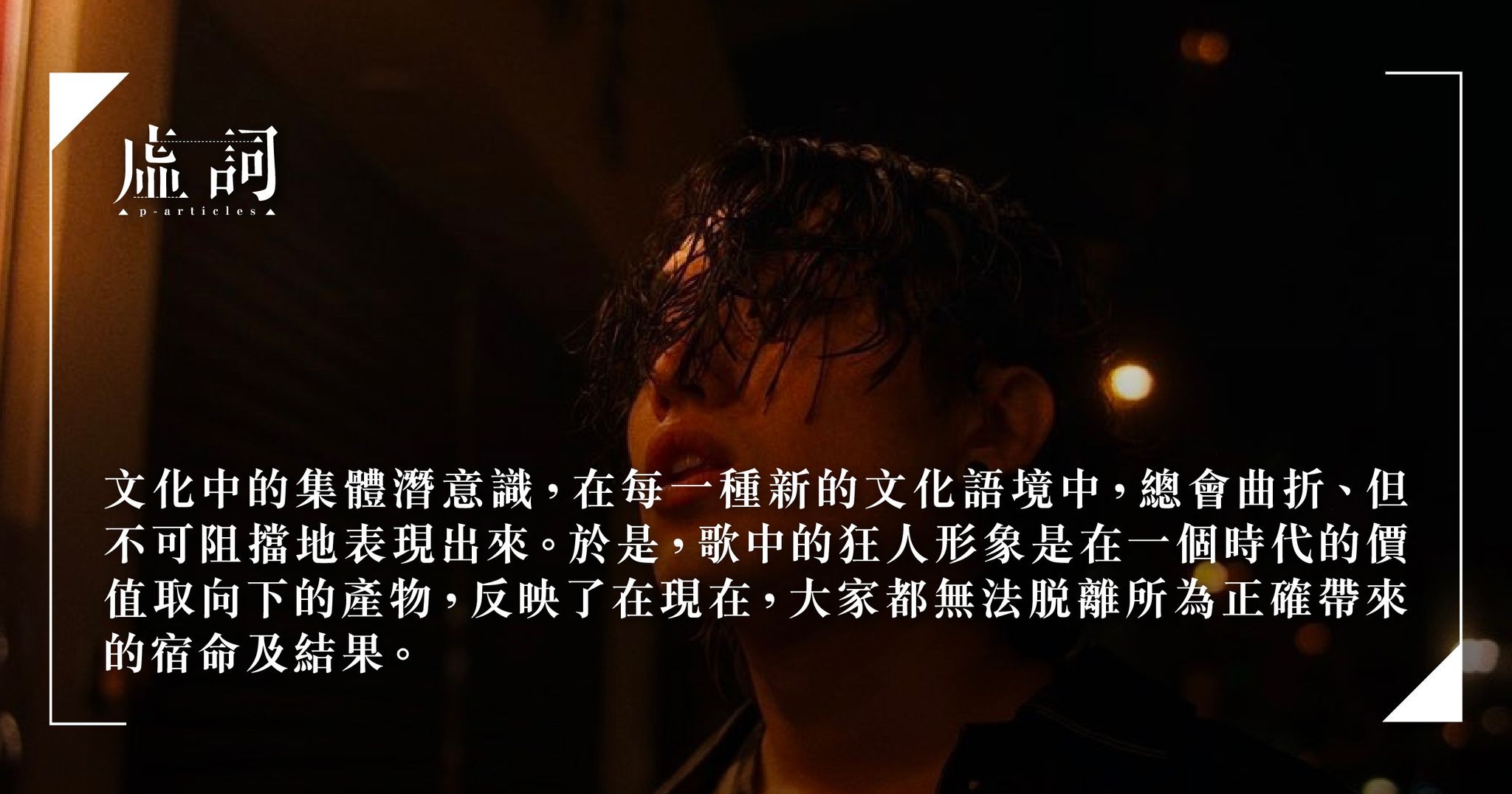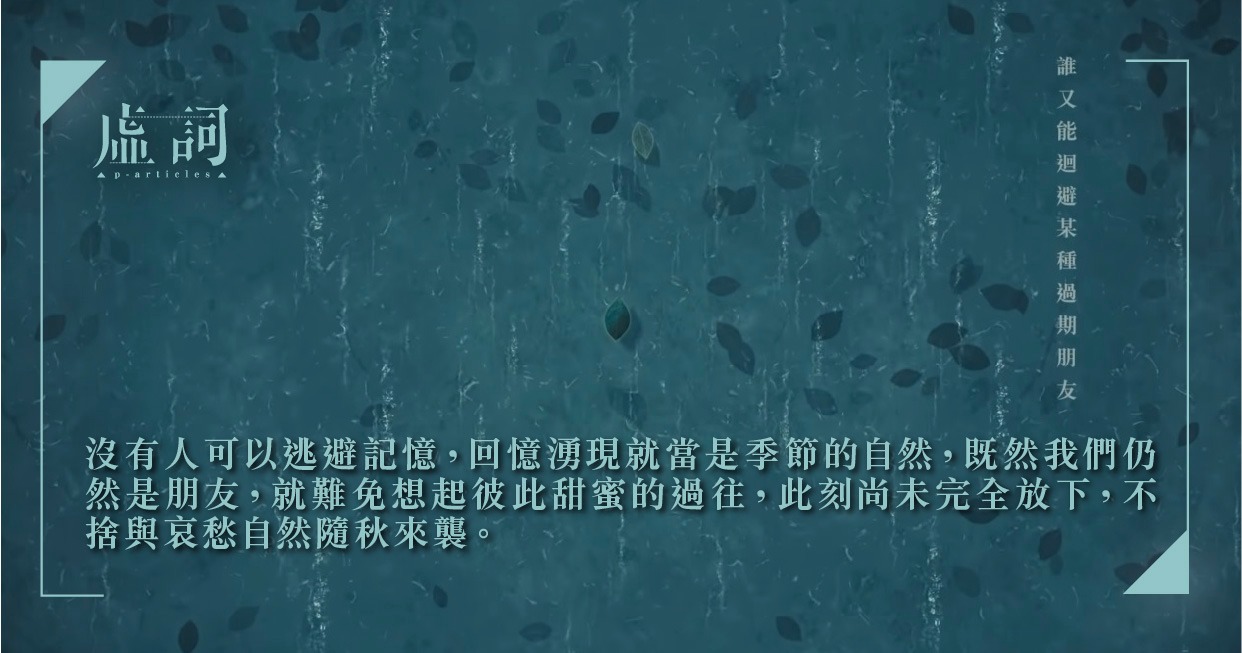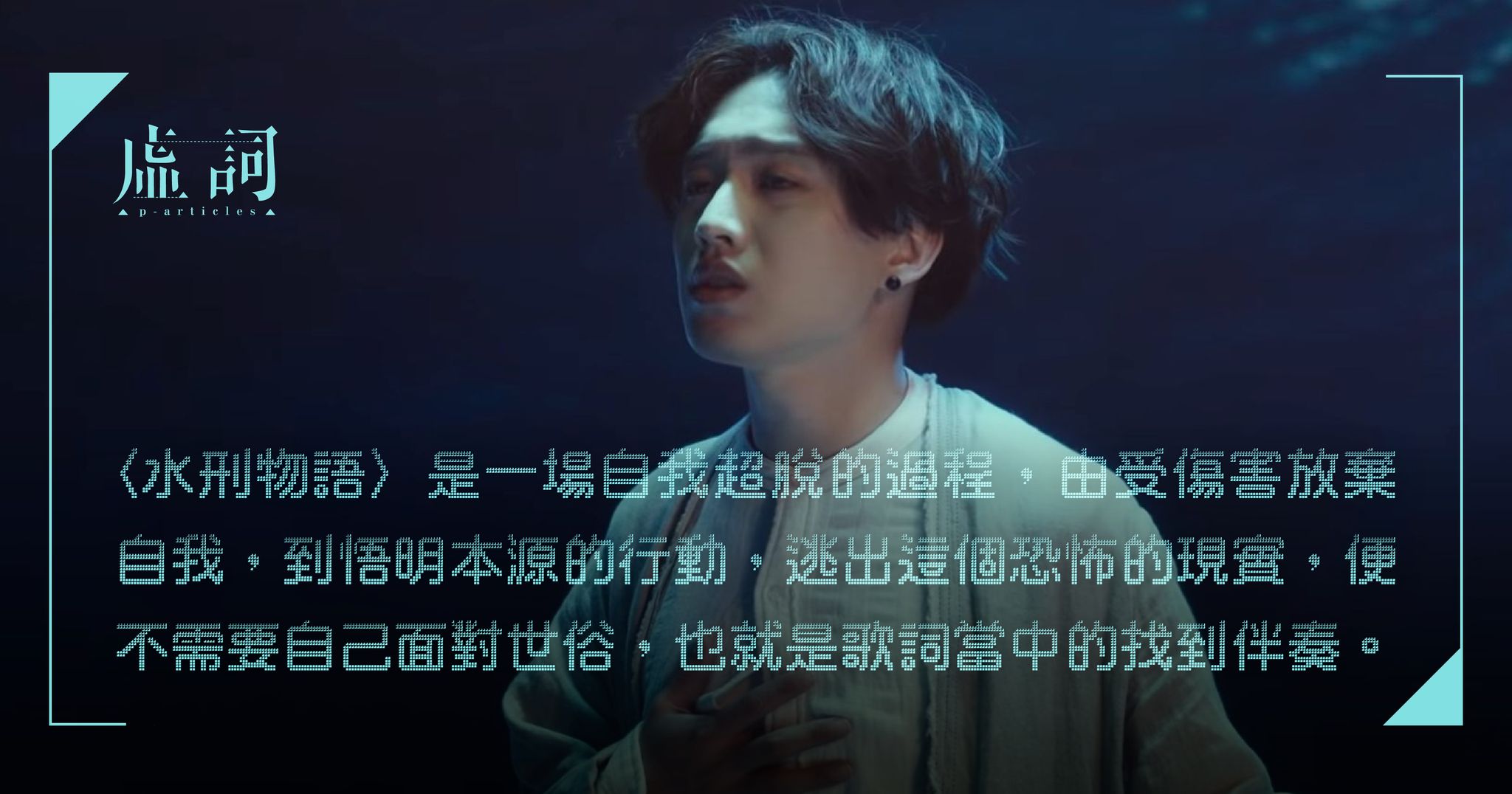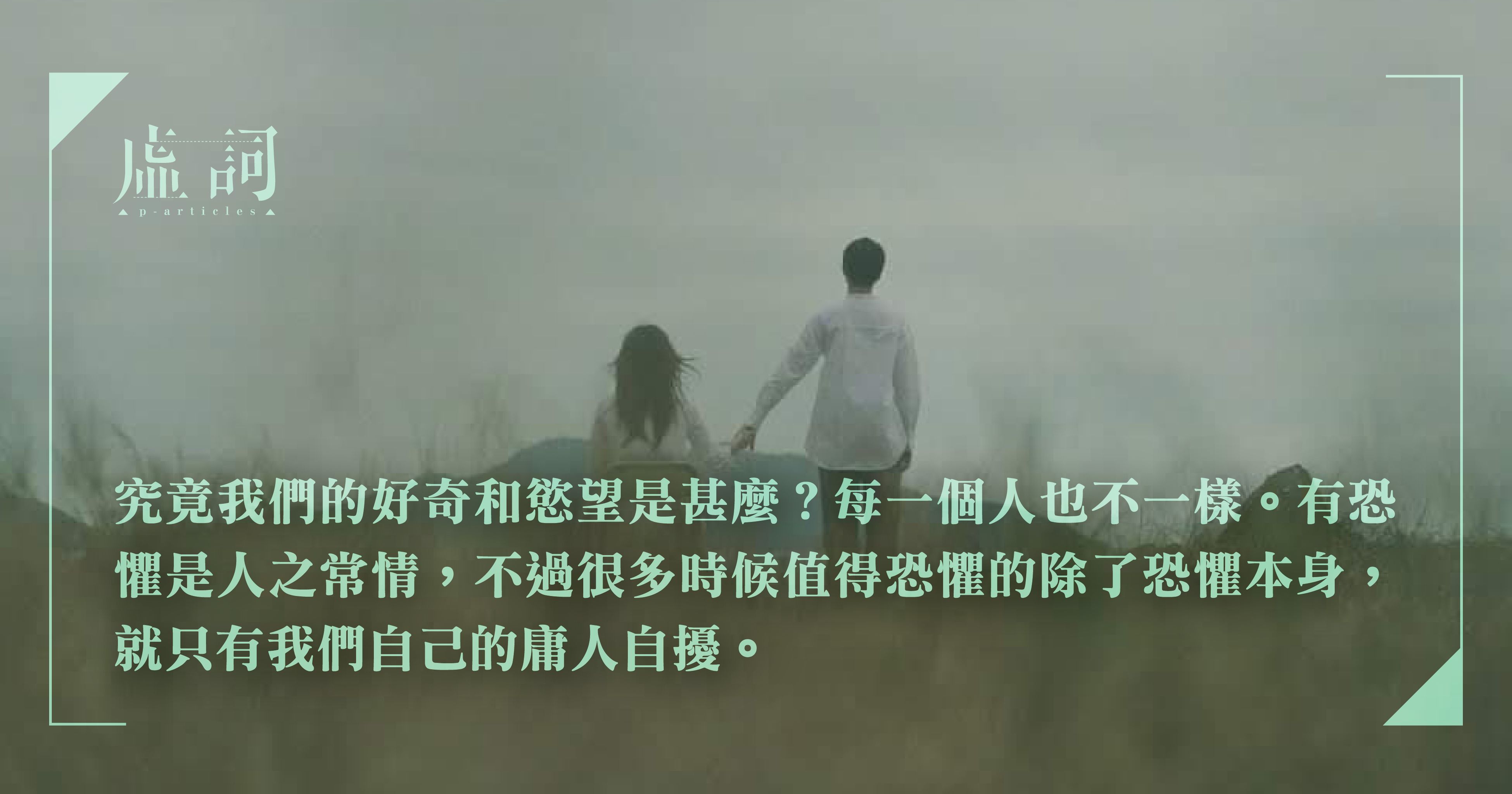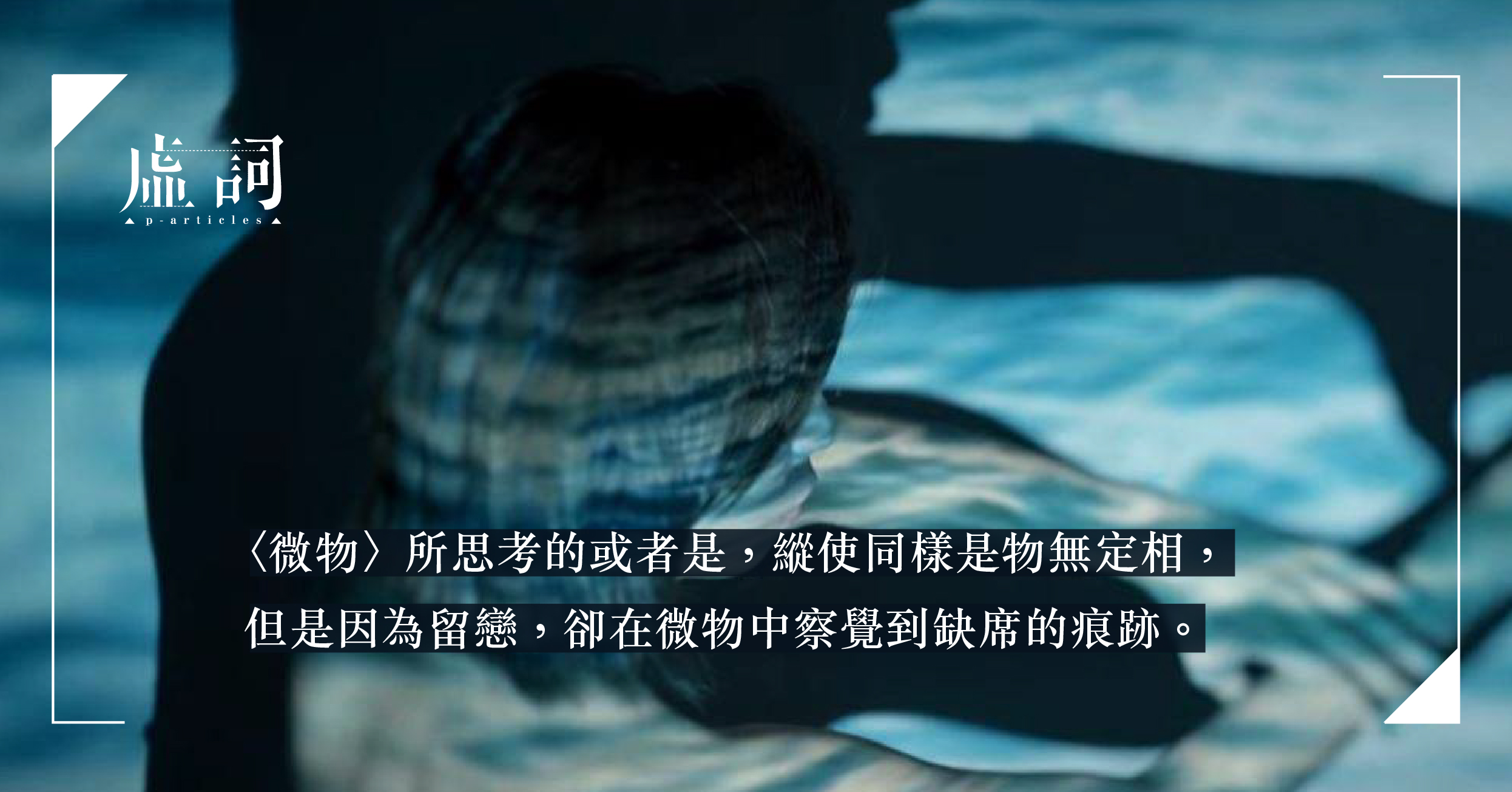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詞評"

林振強的「突破」:由與麥潔文合作之作品說起
其他 | by 羅顥熹 | 2026-01-07
羅顥熹再探香港資深填詞人林振強之作品,是次聚焦於其與歌手麥潔文的合作火花,指出麥潔文早期在娛樂唱片時期的「非情歌」嘗試,及後與林振強合作後,有著從捕捉霹靂舞熱潮的〈電光霹靂舞士〉,到本意寫盡孤獨、卻常被誤讀為靈異作品的〈夜夜痴纏〉。及至後來轉投新藝寶,林振強更以〈勁舞 Dancing Queen〉等鬼馬之作,成功助麥潔文轉型為勁舞歌后。羅顥熹認為林振強的詞作有情也有境,其收放自如的詞風超越6、70年代詞人的寫法與文字,開創出流行歌詞新模式。

【2025・回顧】來都來了不妨睇好文?虛詞年度十大文章 & 編輯部私心之選
現象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5-12-31
一年一度的虛詞排行榜又來了!今年虛詞繼續深耕文化新聞報導,讓讀者緊貼世界各地的藝文動態,同時製作各類型的流量post,務求讓更多文化內容出現在大眾視野,目前成果頗為理想。本年度榜單由影評強勢主導,榜首更是打破多年都市傳說、終於首映的《風林火山》,可見讀者對這部話題之作的好奇。意想不到的是,2025 DSE中文卷竟然在一眾好文中殺出一條血路,看來有卡夫卡加持果然不同凡響。如果這份榜單未能滿足你的閱讀慾,不妨留意文末的「編輯部私心推薦」,希望能趕在年終前可以為一眾好文拉票爭取流量!

〈佛洛依德愛上林夕〉:只求傾聽的夢境
其他 | by 余永曇 | 2025-07-23
余永曇傳來〈佛洛依德愛上林夕〉詞評,指出詞人周耀輝以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為靈感,借同為三大詞人之一「林夕」的名字隱喻夢境,以探索潛意識中的慾望與恐懼。余永曇表示〈佛〉的歌詞通過三段夢境描寫,呈現天馬行空的意象,如金螞蟻、噴泉瀑布與無分針的時鐘,隱晦表達主人公內心深層的掙扎與渴望。而副歌中道出人們需要的並非解夢者的分析,而是傾聽者的陪伴。當我們在傾訴夢境的過程中完成自我覺察,捅破潛意識和意識之間的浮冰。

〈黛玉笑了〉:捻花而笑的林黛玉
其他 | by 余永曇 | 2025-07-03
余永曇傳來〈黛玉笑了〉詞評,詞人周耀輝將《紅樓夢》中林黛玉那多愁善感、葬花哀悼的傳統形象,重新塑造為捻花微笑、豁達開竅的現代女性。〈黛〉中的黛玉從感嘆命運無常,轉而以微笑面對離合,展現「敢愛敢分」的現代愛情觀。由「葬花」的細膩哀愁,到「捻花」的瀟灑釋懷,映射出當代情感哲學。

〈笛卡兒的長生殿〉:楊玉環的生命延續與存在反思
其他 | by 余永曇 | 2025-10-23
余永曇傳來〈笛卡兒的長生殿〉的詞評,表示從歌名已看到詞人周耀輝將法國哲學家笛卡兒與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愛情故事《長生殿》相互融合的故事。〈笛〉通過楊玉環成為仙女擺脫壽命與愛情的桎梏後,才終於窺探到自我存在的價值。周耀輝亦借用笛卡兒之名,在歌詞中加入對時間與存在的反思,把西方哲學與中國的愛情故事糅合,誕生出一個從愛情的沉溺中覺醒、開始思考自我的楊玉環。

淺談《富士山下》與《在青木原的第三天》歌詞中的生死修行
其他 | by Cléo | 2025-05-21
Cléo傳來歌詞評論,認為陳奕迅主唱、林夕填的《富士山下》與吳青峰給何韻詩填詞的《在青木原的第三天》,兩首看似無關的歌曲,均在歌詞中暗藏對「生死修行」的叩問。前者,林名仿佛化身觀音陪伴傷心人在絕望中放下執念;後者則以隱晦意象勾勒出生死邊緣的徘徊,從回憶的微光中尋找活下去的理由。兩首歌雖風格迥異,卻都指向同一個核心——音樂如何成為痛苦中的一線生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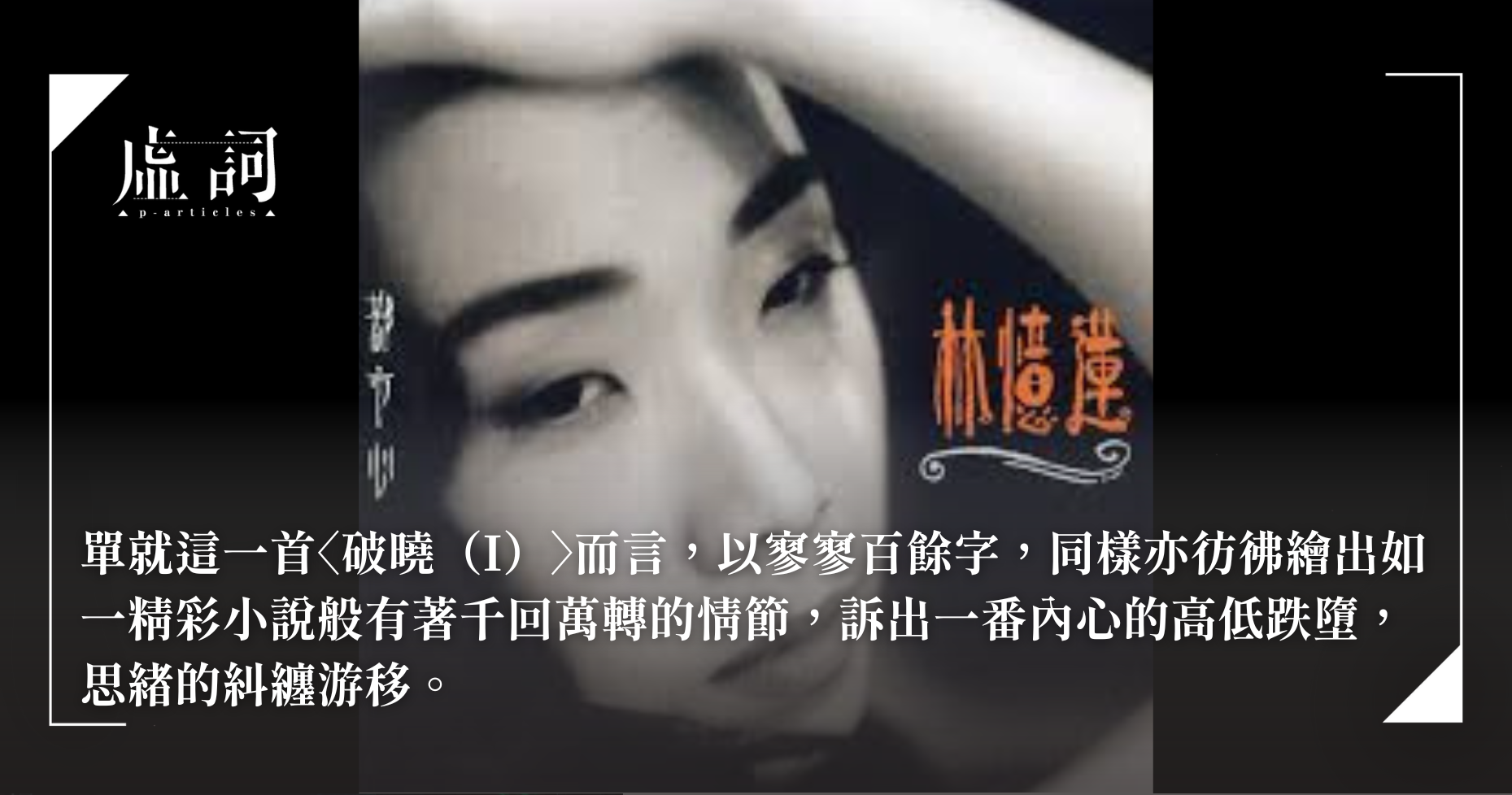
似破不破的晨曉——聽林憶蓮的〈破曉(I)〉
其他 | by 亞C | 2025-02-25
亞C認為,不少廣受歡迎的小說或是戲劇很多時最為引人入勝的便是其中的情節,尤其是某些意想不到的反轉,常為人津津樂道。但是對於流行音樂和歌詞而言,拋卻唱片公司或經理人等商業上的考量,有著音律和字數的規限,較難也較少在一首歌裡如小說散文般出現所謂的「起承轉合」,隱含著各種意想不到的高低起跌。亞C偶爾發現,林憶蓮的專輯《夢了,瘋了,倦了》中〈破曉(I)〉,以寥寥百餘字,同樣亦彷彿繪出如一精彩小說般有著千回萬轉的情節,訴出一番內心的高低跌墮,思緒的糾纏游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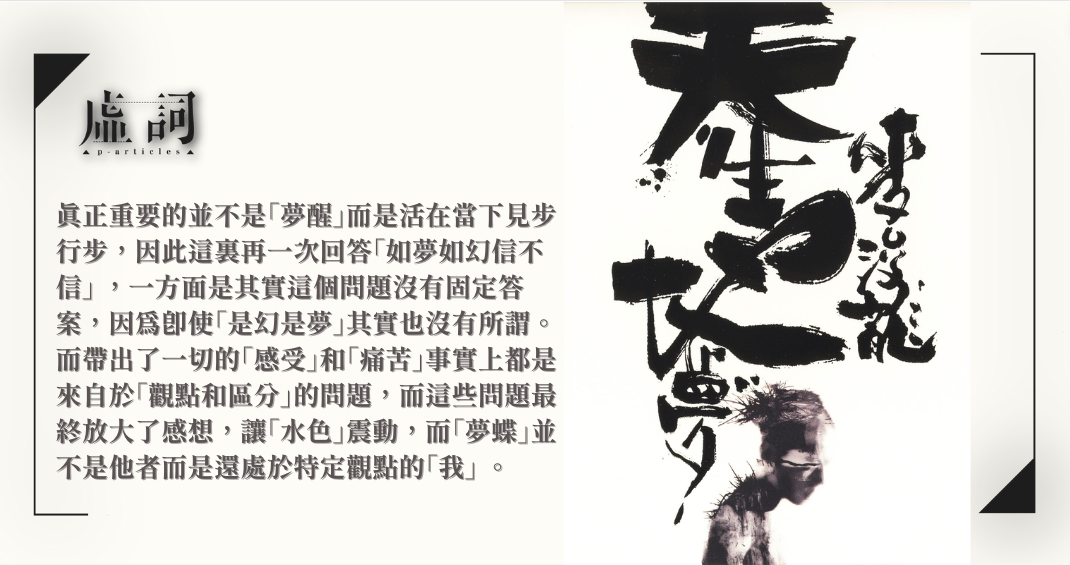
從生死疲勞到得到青空——林夕《天生地夢》詞評
其他 | by 明月 | 2024-04-02
流行歌可能是商品,但無可否認的是往往有著哲學思想以及一眾歌手、填詞人、作曲、編曲、監製心中所表達的人生意象。明月探討在麥浚龍的大碟──《天生地夢》中〈生死疲勞〉、〈顛倒夢想〉與〈弱水三千〉的三首歌詞,逐一拆解。倘若浮生若夢,那麼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呢?

不是你的命,不要亂認命——藍奕邦〈命〉詞評
其他 | by Sir. 春風燒 | 2023-12-14
兩年前藍奕邦發表了〈生〉,詞曲由藍奕邦親手包辦,寫的是人的艱難掙扎,並探討生的意義。是次林夕所填的〈命〉除了延續這個話題以外,還討論一個人被隨機誕生在某個時空,似是探討人面對存在的拋擲性,是不是只能認命?Sir. 春風燒評此曲,認為歌詞將人的覺醒和大膽都歸因於先天遺傳而不是後天的識見,但只有人類才能做到知命但不認命,教人握緊尊嚴不認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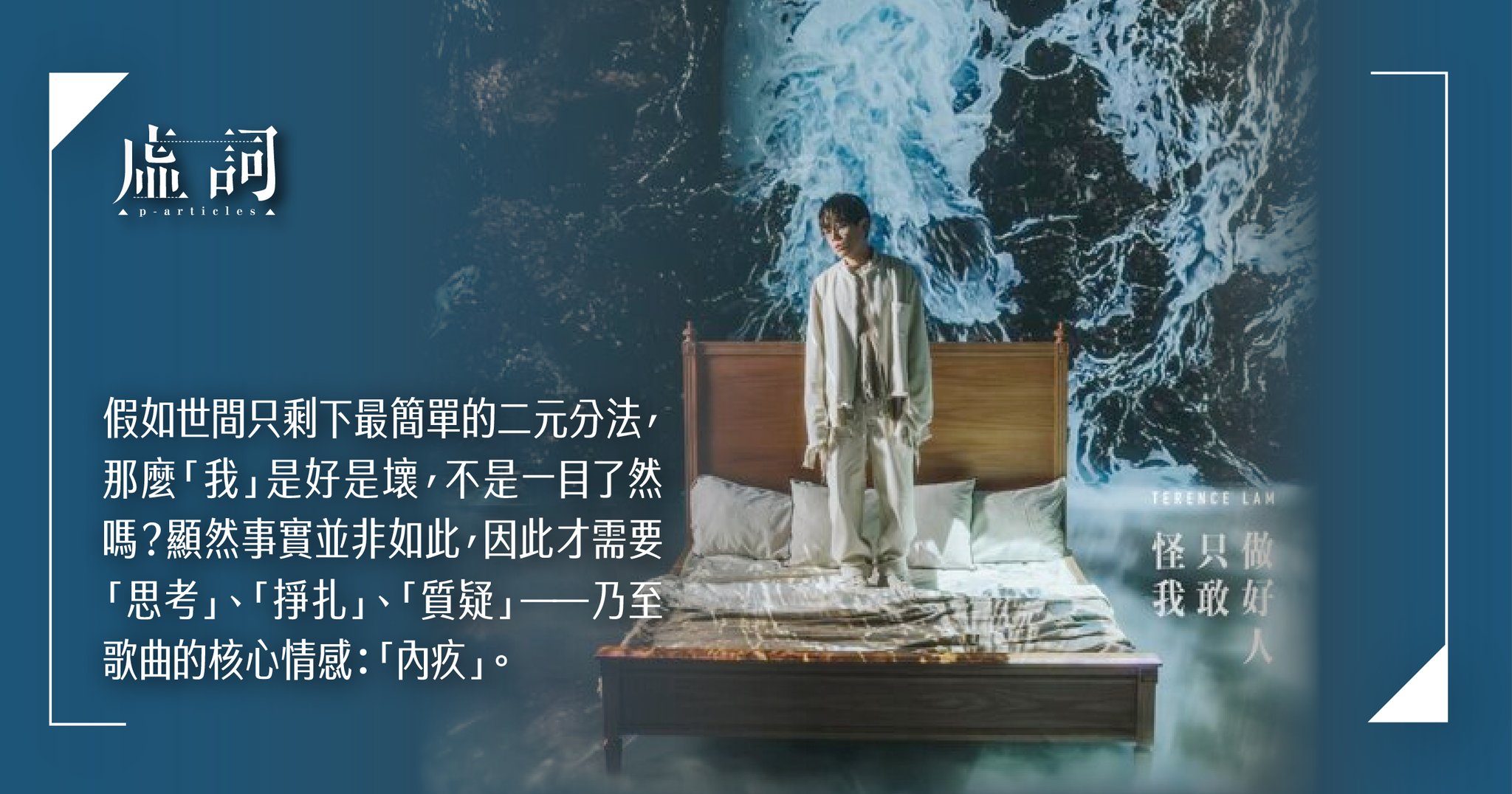
善惡何曾涇渭分明?——聽林家謙〈怪我只敢做好人〉
其他 | by 任弘毅 | 2023-10-17
再談林家謙新作〈怪我只敢做好人〉,任弘毅在一面倒支持「邪不壓正」、「不論代價堅持做好人」的詮釋下,重新反思歌名的含意,發現當中刻意的不協調性,世間的好壞不是純粹的二分法,才需要「思考」和「質疑」。他認為這首詞珍貴之處在於林夕以細微違和感提醒我們:好壞往往只是表象,而當中的詩性辯證、覺悟之高,即使非林夕本意,也是一份十分寶貴的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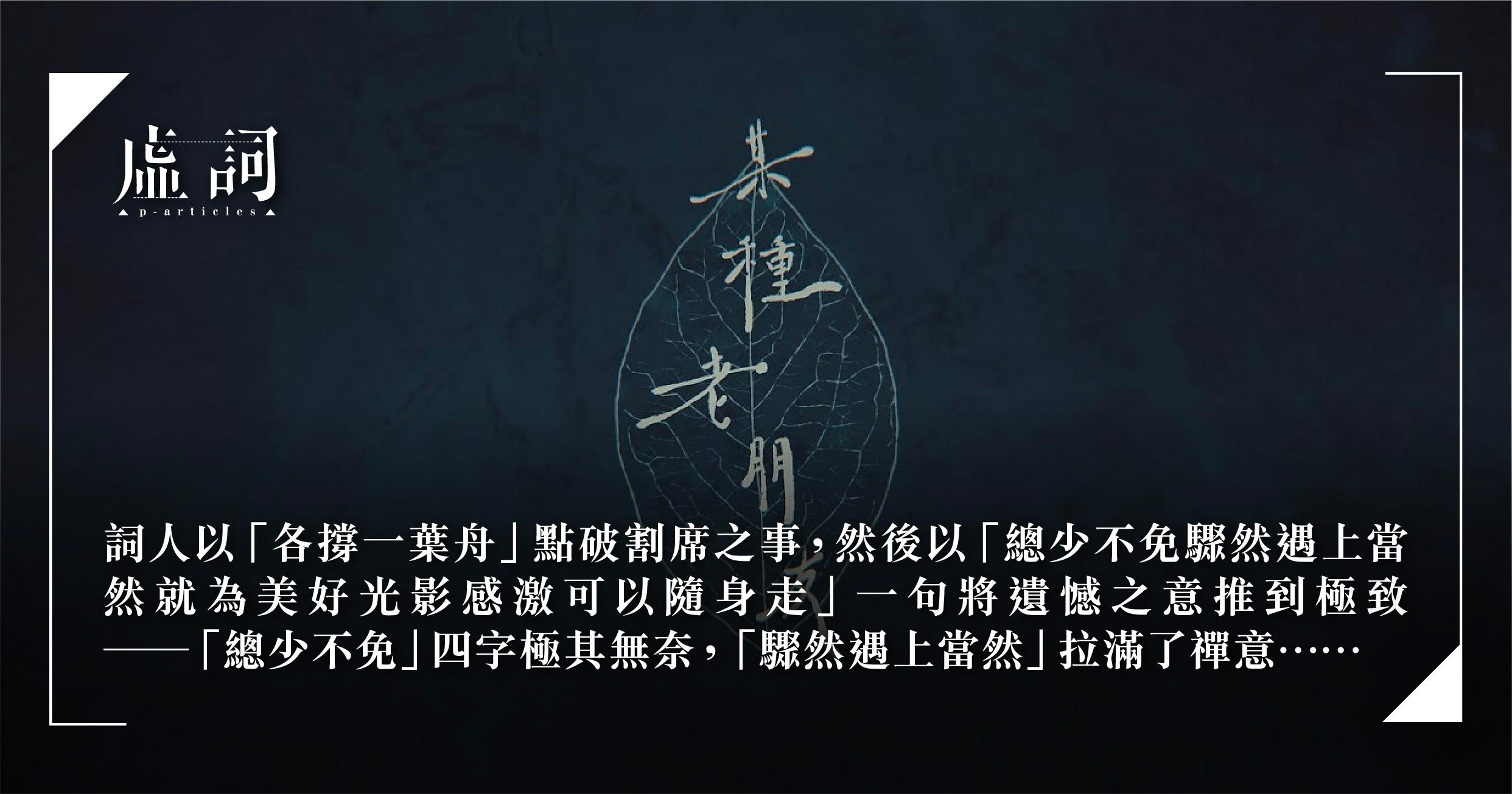
林夕的割席美學:《某種老朋友》詞評
其他 | by Sir. 春風燒 | 2023-01-10
詞人以「各撐一葉舟」點破割席之事,然後以「總少不免驟然遇上當然就為美好光影感激可以隨身走」一句將遺憾之意推到極致——「總少不免」四字極其無奈,「驟然遇上當然」拉滿了禪意,世事和人情變故不但快而且彷彿是命定的,令人感慨現實難以捉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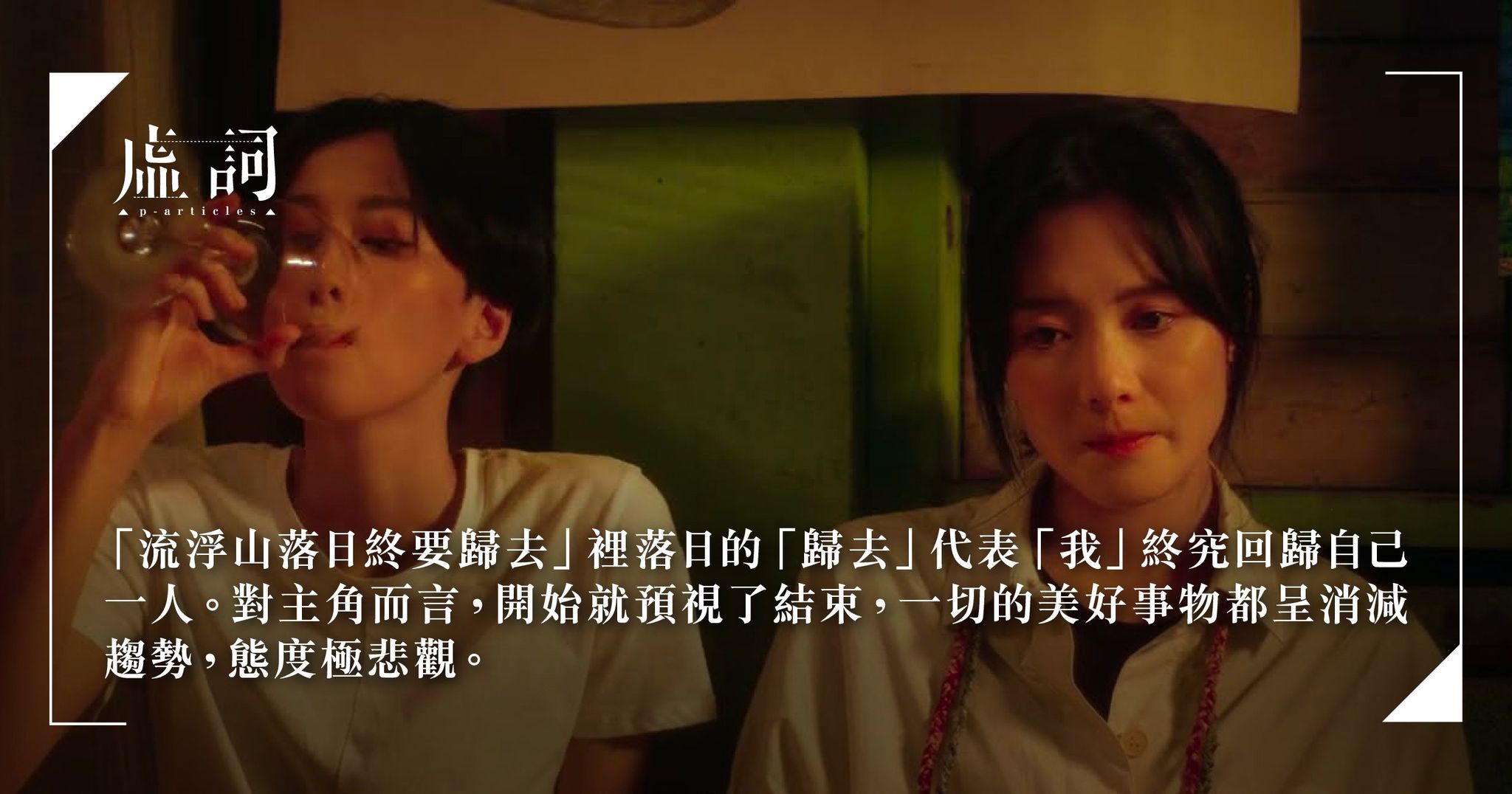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jpg》——從私密的日常看一個時代的境況
其他 | by 熊蔚婷 | 2022-06-08
唱作歌手Serrini的《我在流浮山滴眼水.jpg》,歌名看似無厘頭,但若理解全首歌詞,自會發現箇中意味,熊蔚婷認為這首歌取材日常,歌詞風格直白質樸,當中抒發的愁緒亦是老生常談——在這個充滿荊棘的時代,面對未知仍要勇於冒險,接受失去作為人生常態,而非一昧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