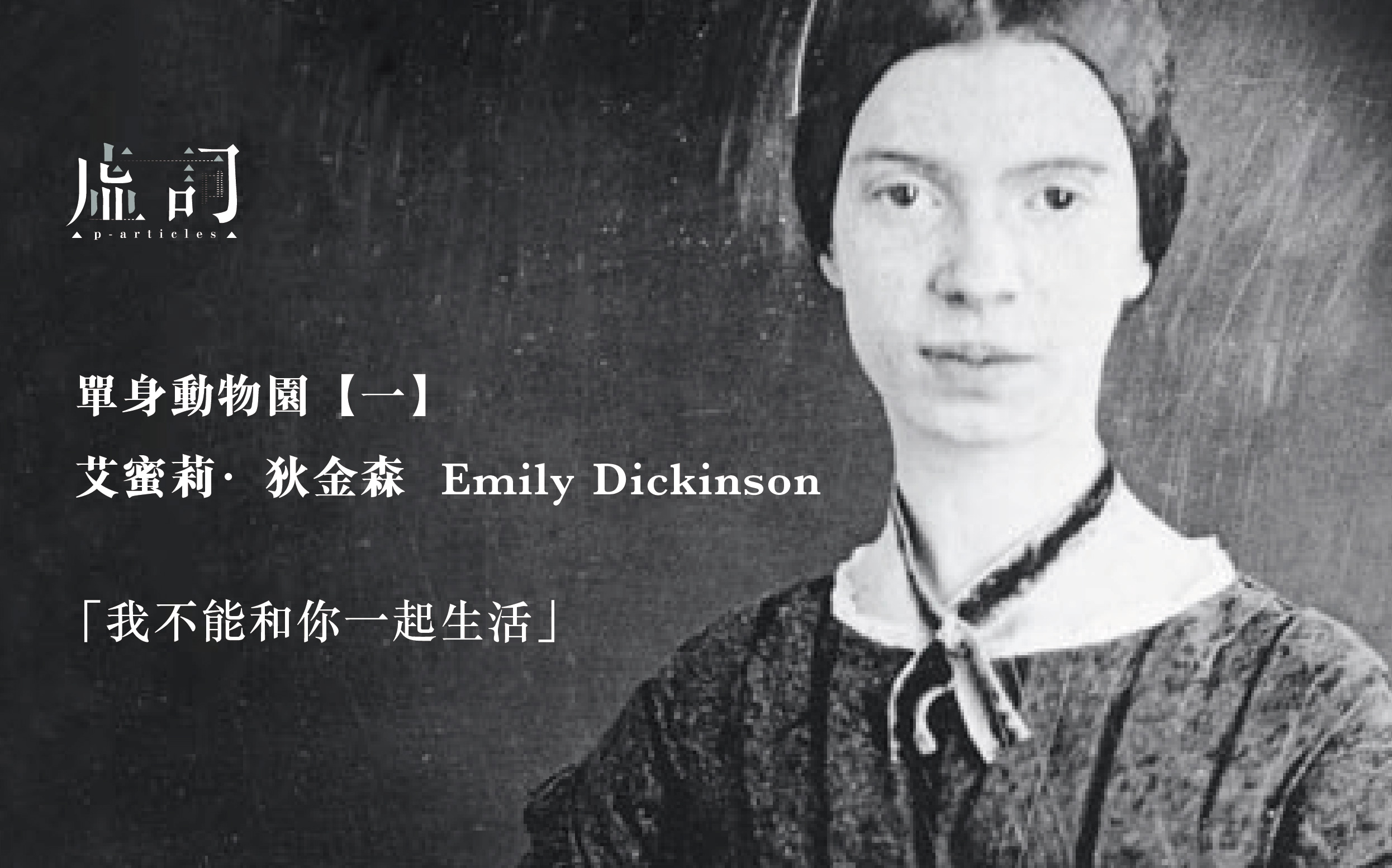SEARCH RESULTS FOR "單身"

【又到聖誕】流出!編輯部Lonely Christmas Boxset
其他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12-23
一年容易又聖誕,又係考驗一眾單身人士意志力嘅時候,尤其今年因為疫情,一個人獨自在寒流下支撐,難免更覺空虛寂寞凍。今年疫情下的聖誕,「虛詞編輯部」為讀者嚴選Lonely Christmas Boxset,實在係居家出行,單身聖誕,必備良藥。

《文學單身動物園》小輯
專題小輯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11-12
從才子卡夫卡到對拒絕婚姻的西蒙.波娃,以及經歷情傷再無法振作的安徒生、周夢蝶,《文學單身動物園》寫及古今中外、千百年間不同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的獨身故事,並引介他們的愛情觀。年代替換,但「單身」的無形壓力,或者不曾減少。獨身與否,仍是一個會攪拌起情緒的問題。

單身不可怕,騎呢關係更可怕——從《文學單身動物園》中看單身的多樣性
書評 | by 謝豬 | 2020-10-21
《文學單身動物園》起題取自歐洲科幻愛情片《Lobster》的中文譯名,雖然各章節間缺少連結,既不分時序,也不分古今中外,卻呈現了單身的「多樣性」。單身的定義原來可以很廣闊,界線也可以很模糊:就算真的流落孤島,偉大的文學家們還是會寫一百封寄不出的情信跟心裡的對象聯繫,所以「絕對」單身是不可能的。

【新書】《文學單身動物園》:男作家都是愛情寫信師,珍奧斯汀卻說別相信情信
書評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08-20
讀《文學單身動物園》這本書,看古今中外不同名人如何在情感關係中跌盪或自強,或者不禁輕嘆:在愛情面前,我們都是一樣的人。

【新書】《文學單身動物園》編者序
書序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4-26
我們感覺到單身在今時今日愈來愈普遍;在日本甚至發展出「超單身社會」的文化,一人燒肉、一人卡拉OK等等不一而足。「單身動物園」的名字甚至來自年前的一齣電影《Lobster》的香港譯名。回到五四以至幾百年前,「單身」可能是為人所詬病或側目的「罪過」;而隨時間過去,「單身」所遭受的外在壓力是否有減少?有沒有更能逃脫他人的目光?「單身動物園」的文章有時不避偏鋒,語帶偏激,因為我們覺得,獨身與否,似乎仍是一個會攪拌起情緒的問題。

【單身動物園】屠格涅夫︰你倆一雙,我原來是一個
單身動物園 | by Nathanael | 2019-05-29
「安心事件」雖已告一段落,但「唔熟唔食」或者「扮friend食老死」的事,其實三不五時都在身邊上演。跟托爾斯泰和杜斯托也夫斯基齊名俄國文學「三巨頭」的伊凡.屠格涅夫,自從25歲戀上有夫之婦以來,為了她一直單身至死;期間甚至多年都跟夫婦二人住在一起,或是在他們的房子旁為自己另蓋一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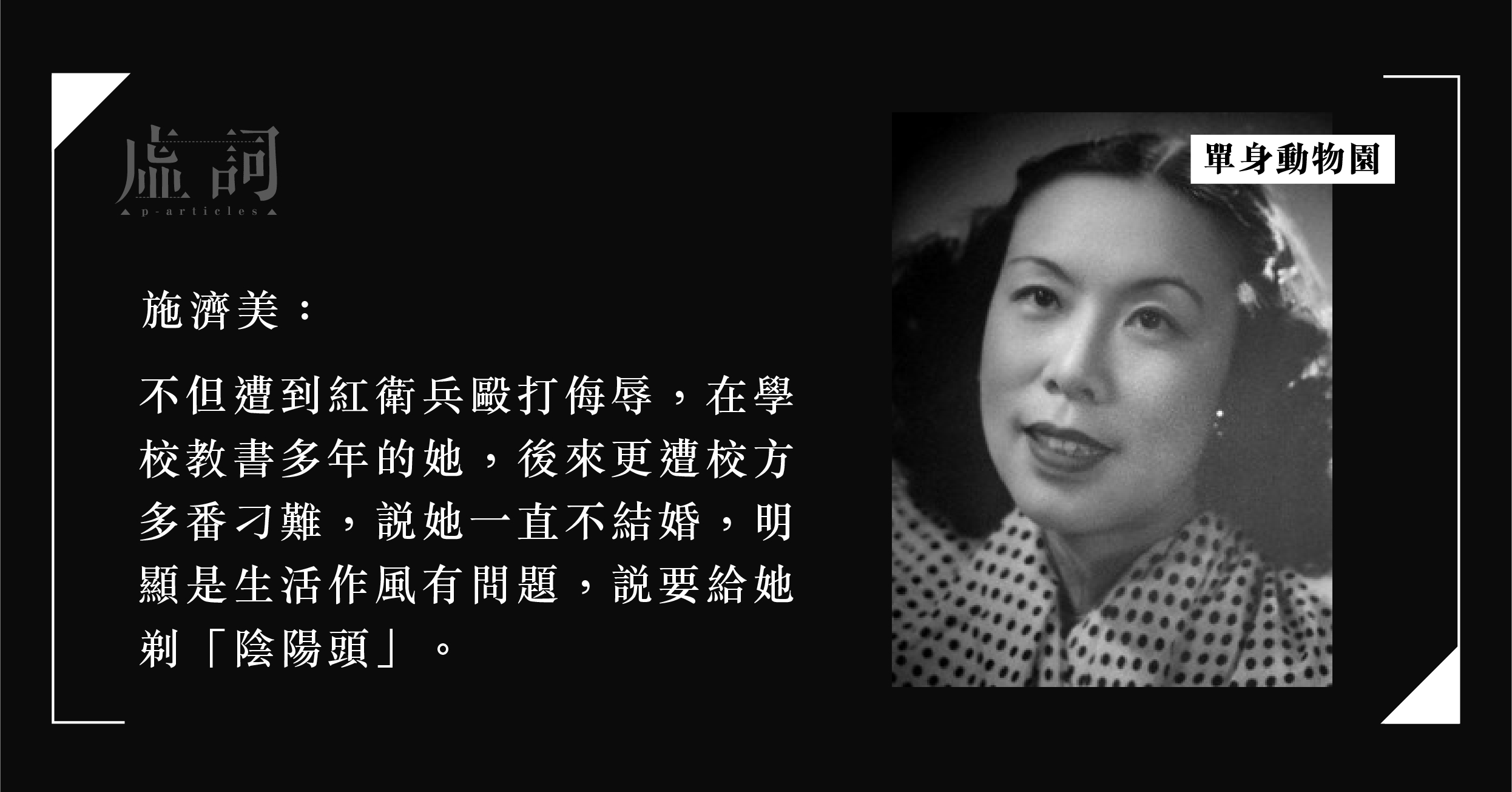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施濟美︰東吳莫愁,終身不嫁
單身動物園 | by Nathanael | 2019-04-10
誰是施濟美?從上海培明女子中學升讀東吳大學經濟系,施濟美不但是「東吳系女作家」的領軍人物,四十年代更與張愛玲及蘇青齊名,並稱「三大才女」。1946年,東吳大學某女學生參加《上海文化》月刊舉辦的「你最欽佩的一位作家」活動,「施濟美」三字躍然紙上(當年施濟美只有二十六歲而已!);在後來的「我最愛的一位作家」讀者調查統計中,她更名列第四,緊隨巴金、鄭振鐸及茅盾之後,可見當年她在上海文壇上的地位與名氣。

【單身動物園】珍.奧斯汀:婚姻圈套,我不入局
單身動物園 | by Gasol | 2019-04-01
當你尋找珍.奧斯汀的作品時,很容易會見到一本「神書」,叫作《男人皆如此——珍.奧斯汀教你戀愛秘訣》。這本書暢銷多年、成為不少渴愛女性的法寶,其作者洛琳.韓德森(Lauren Henderson)大學時期就曾以珍.奧斯汀作品中的求愛儀式撰寫論文;而她的作者簡介這樣寫道:「目前定居紐約,同時與一位像亨利.蒂爾尼(Henry Tilney,《諾桑覺寺》男主人公)一般的男士有著幸福的戀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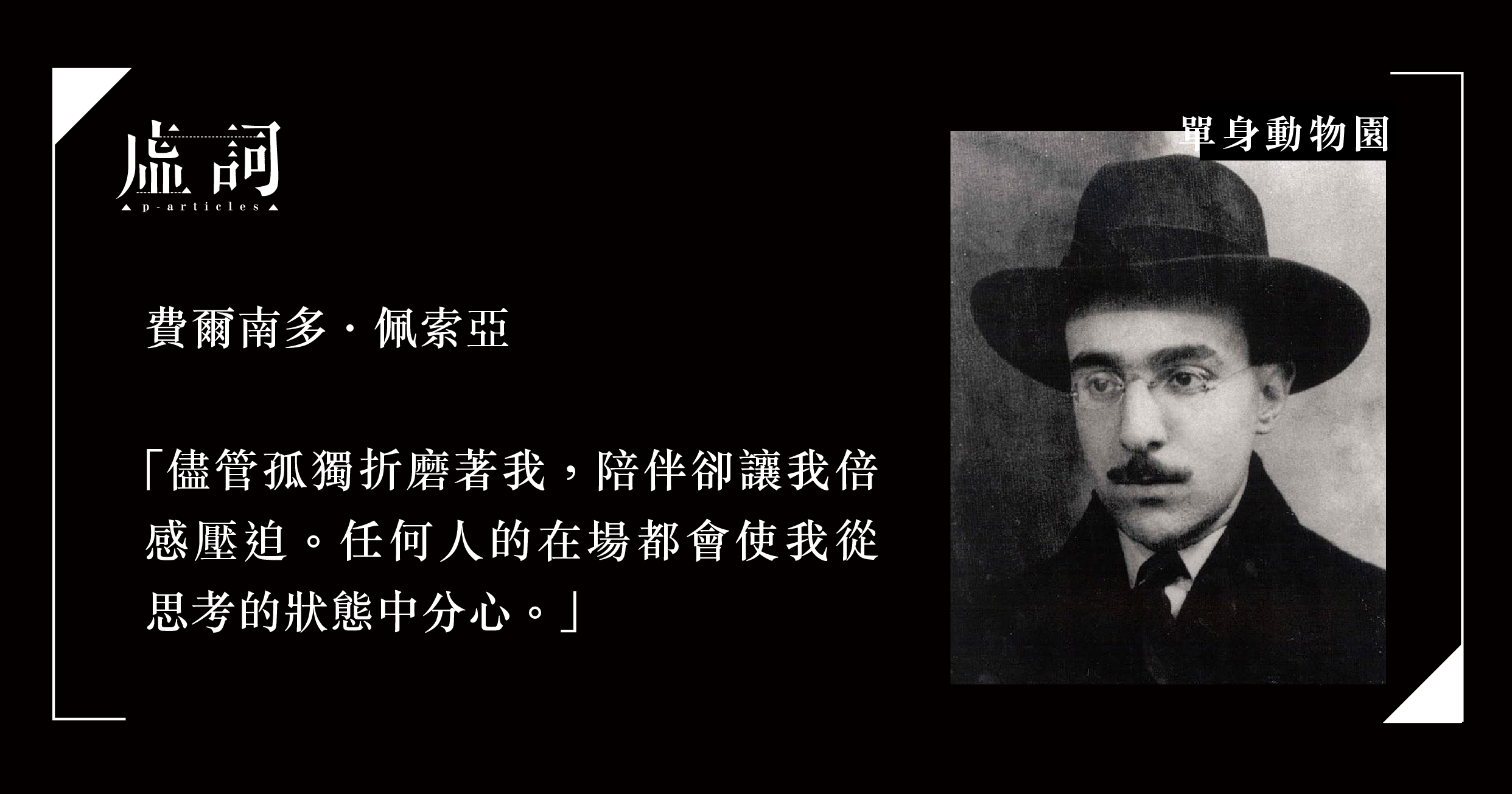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佩索亞:高貴的秘訣是不要靠得太近
單身動物園 | by stoudemire | 2019-03-11
對後人而言,披著七十五個「分身」度過短暫一生的作家佩索亞是神奇的,甚至有人懷疑他在神秘學研究中獲得了超能力。但他仍在世的時候,卻是成日挫敗、自覺多餘的「魯蛇」(Loser)——從里斯本大學退學、辦印刷廠失敗、應徵圖書館工作都被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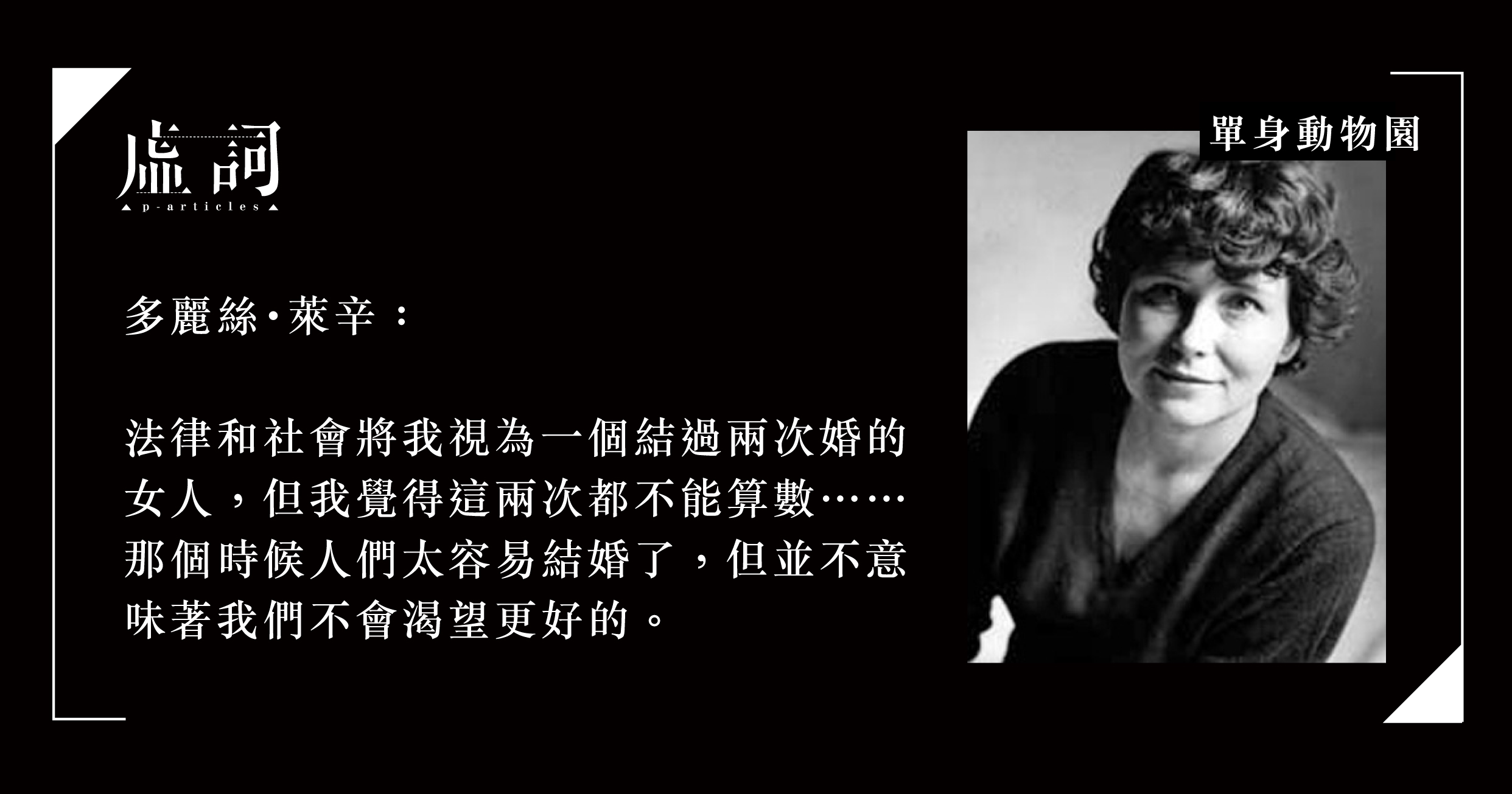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多麗絲・萊辛:結了兩次不算數的婚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 | 2019-02-18
以《金色筆記》名噪一時、於2007年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小說家萊辛,一生結婚兩次,卻極力否認這兩次婚姻的實效性,到底其中經歷了些甚麽?

【單身動物園】Joseph Cornell:聽說太理想的一切都不可接觸——錯失草間彌生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 | 2019-02-03
新年流流,大批親戚正在湧來。除了「拍拖未」、「結婚未」這類常規問題,還有一種更惡劣的,一上來就試圖擾亂大家的感情生活,劈頭蓋臉拋出一句:「做乜同佢一齊呀?」聽到這類滿懷惡意的「關心」,你會怎樣答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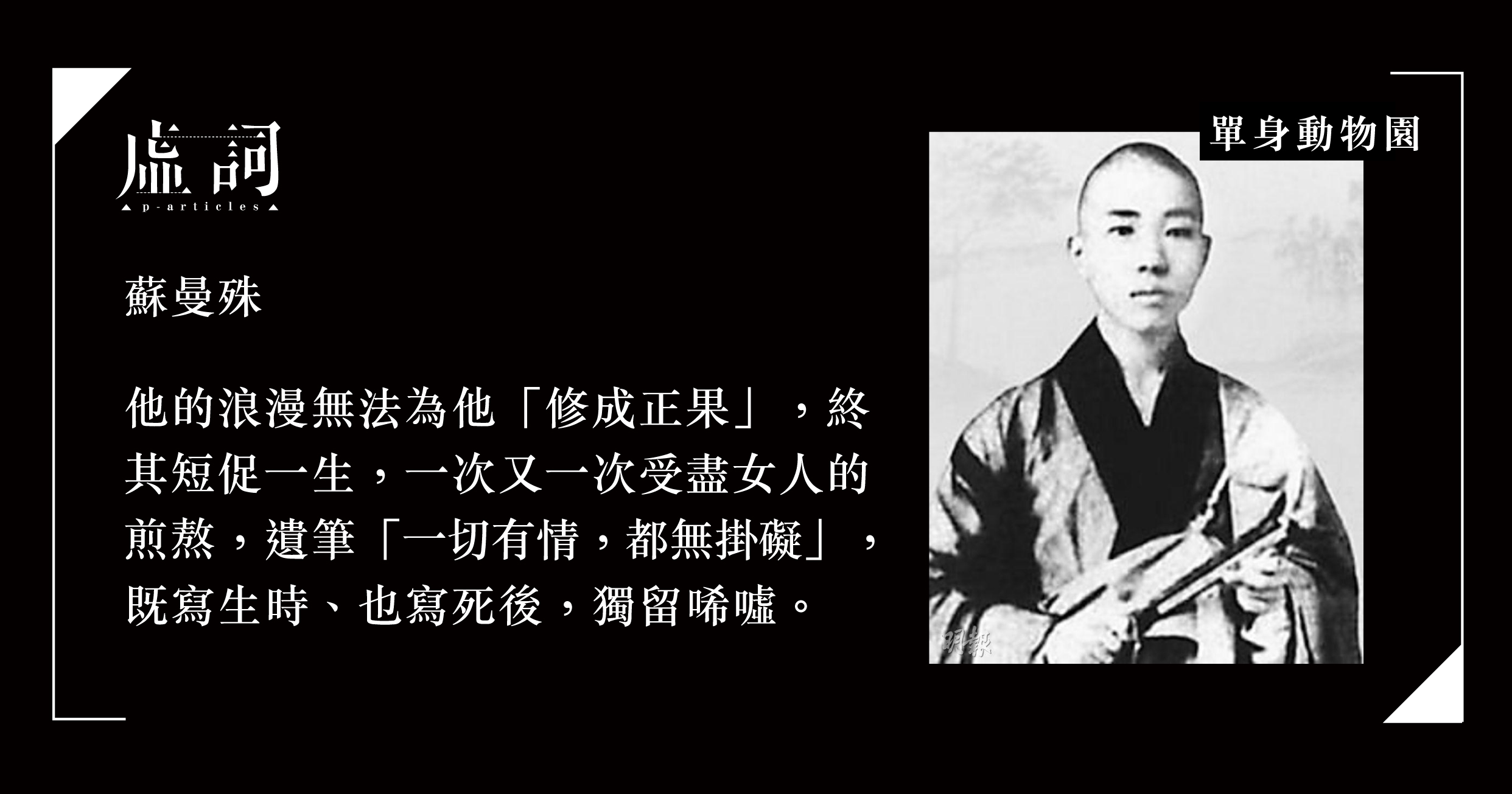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蘇曼殊︰民初情僧,無情不似多情苦
單身動物園 | by Nathaneal | 2019-01-21
本名子谷,法號曼殊,在詩僧、畫僧以外,蘇曼殊更是浪漫至極的情僧,可惜他的浪漫無法為他「修成正果」,終其短促一生,這個「短命情種」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受盡女人與單思的煎熬,遺筆「一切有情,都無掛礙」,既寫生時、也寫死後,是遺憾,也是他是畢生故事提煉出來的哲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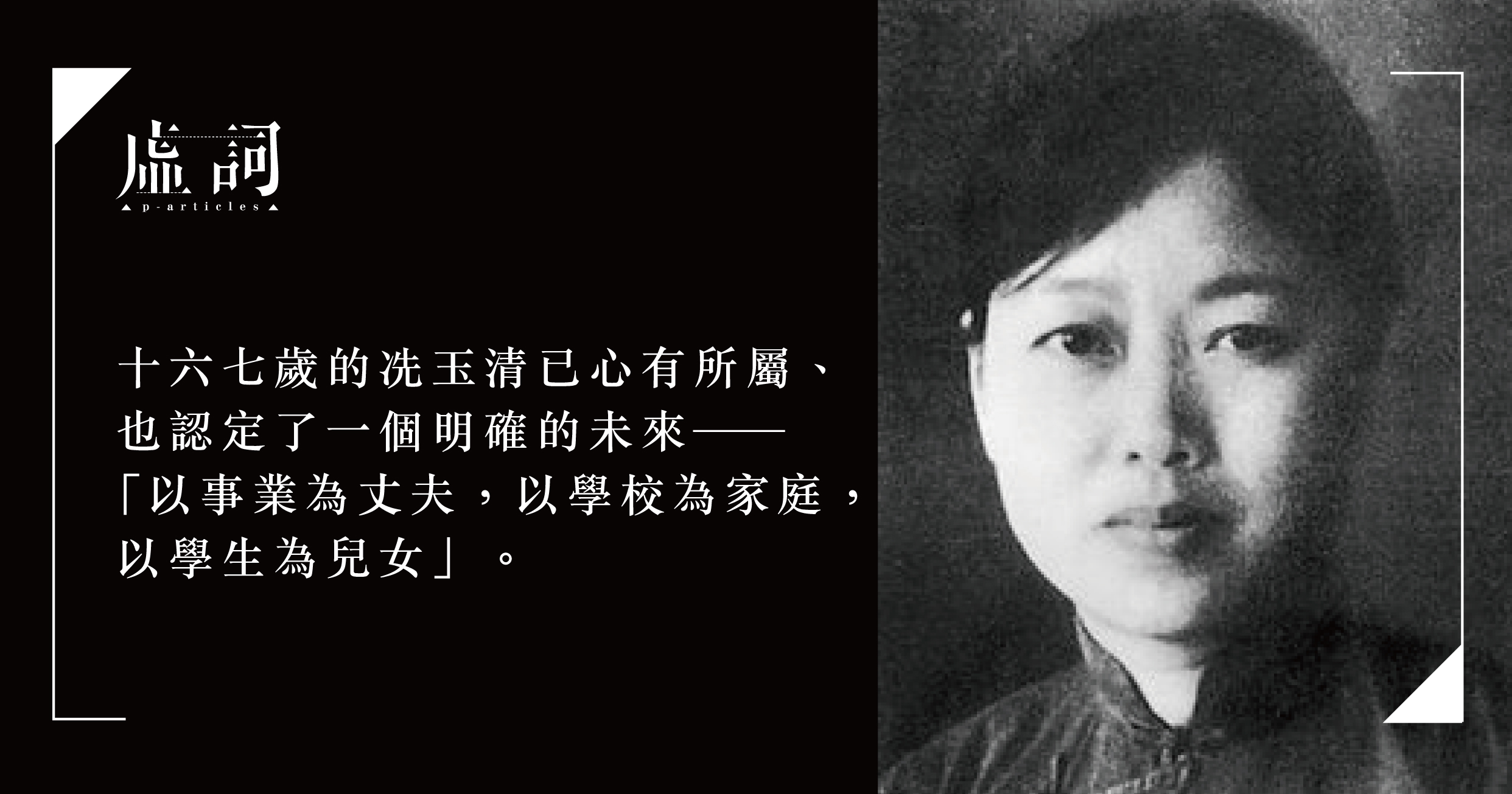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冼玉清:不結婚,又如何?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9-01-07
「嶺南第一女博學家」、「千百年來嶺南巾幗無人能出其右」……廣州嶺南大學(後被合併成為中山大學)的中文教授冼玉清,如今已被冠上這許多正面名號。然在世時,這位一生不婚的女性,不論在教學生涯、還是日常生活中,都常被流言蜚語包圍著,經歷諸多風波與阻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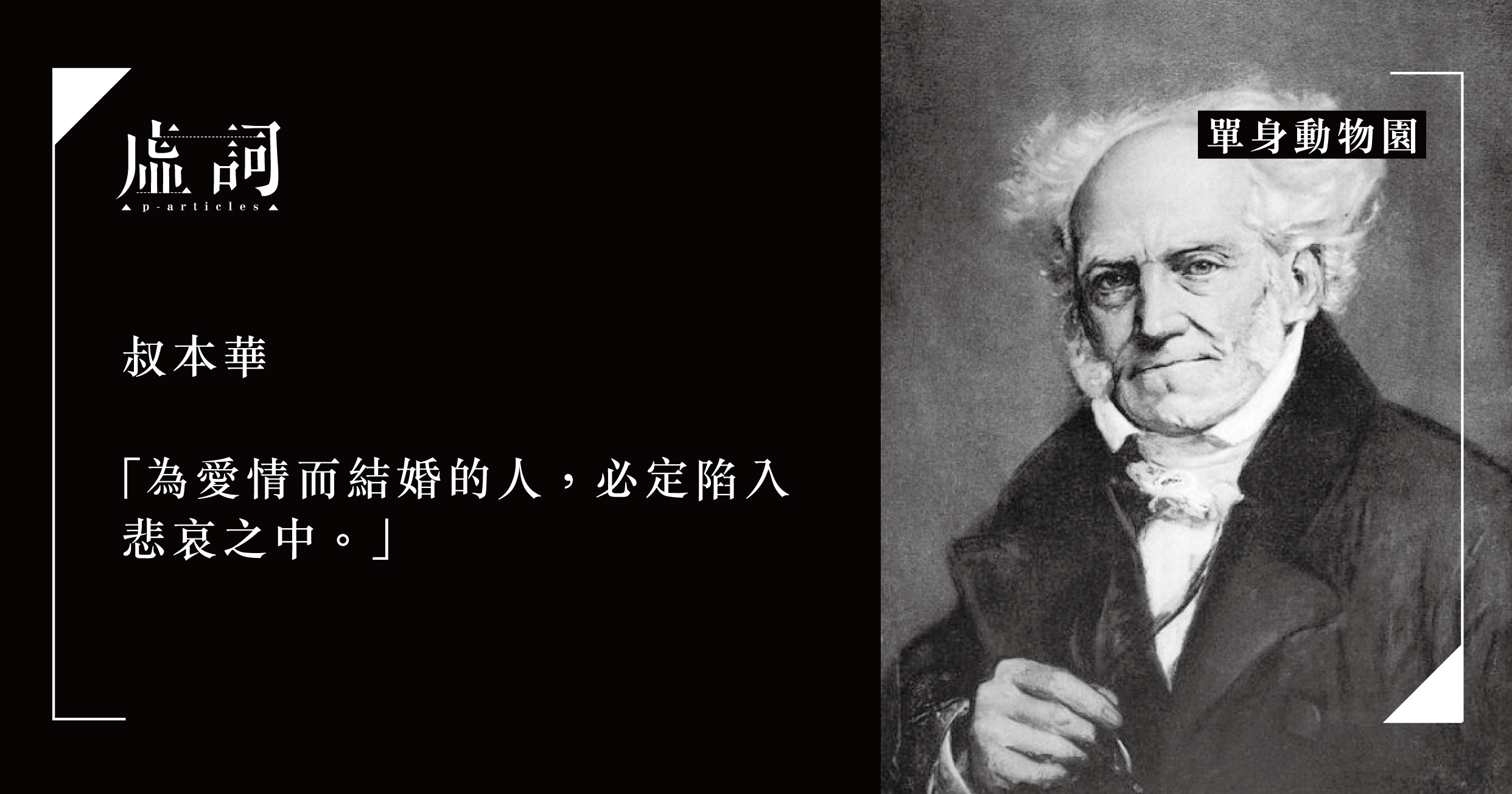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叔本華:厭女哲學家
單身動物園 | by Arthur | 2018-12-24
叔本華在〈論女人〉一文中幾乎把女人踩得一文不值,文章若是發表在今天,大概一堆「厭女」、「性別歧視」、「政治不正確」的標籤就要往他頭上貼,更會惹一眾女權份子的大力撻伐。相信人生只有痛苦的「悲觀哲學家」叔本華,在他七十二年的人生中,到底發生過什麼事,才讓他對女性怨恨滿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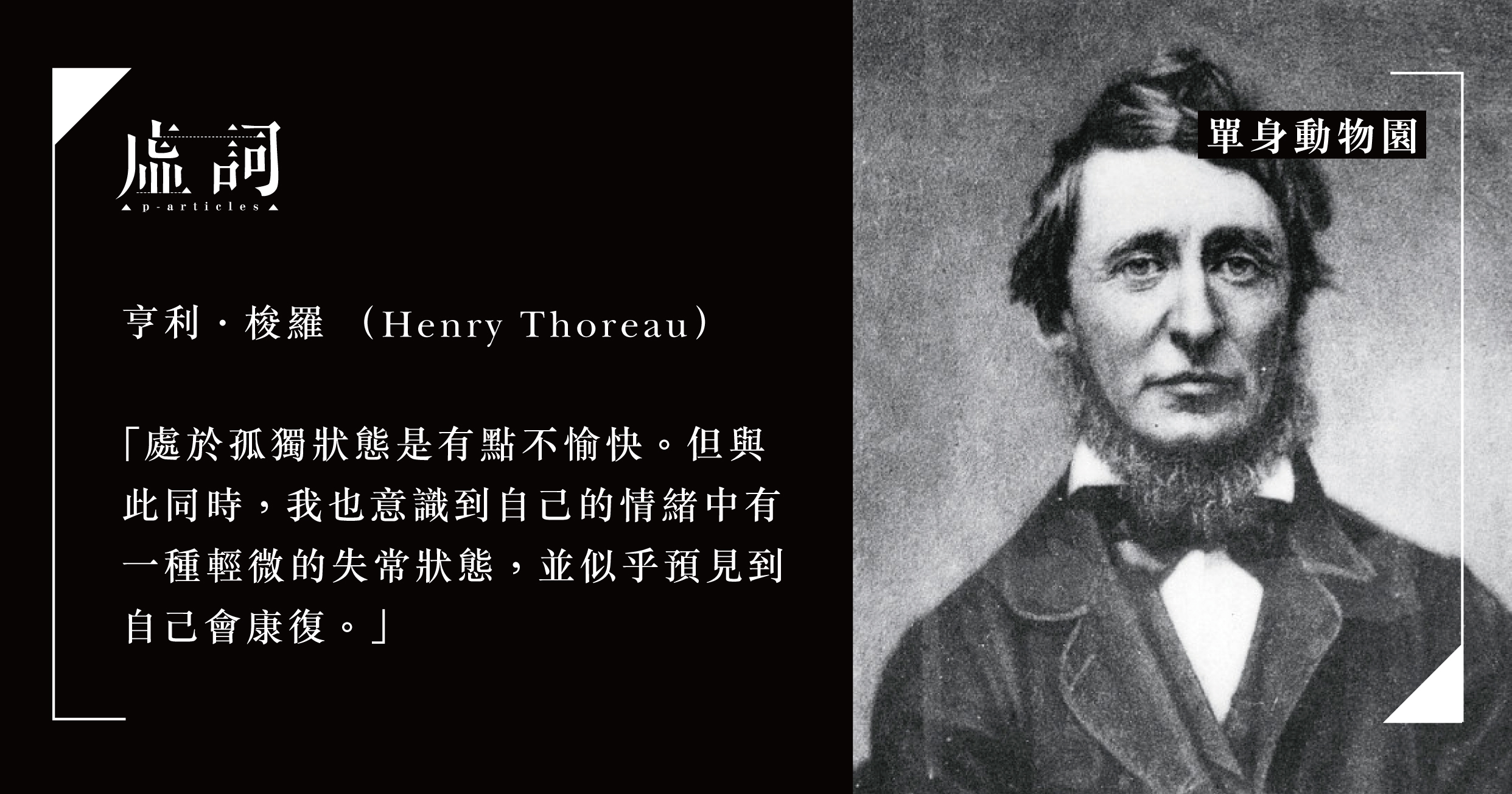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梭羅: 隱青鼻祖的不婚反抗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12-10
據說如今每個文青都有一本《瓦爾登湖》。偏愛歸隱、嚮往獨居,現已成為一種文化現象(也是消費趨勢?)然而寫下這本巨著的梭羅,當年是形單影隻,拿一柄斧頭,就跑入了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山林裡,自此開始長達兩年的「野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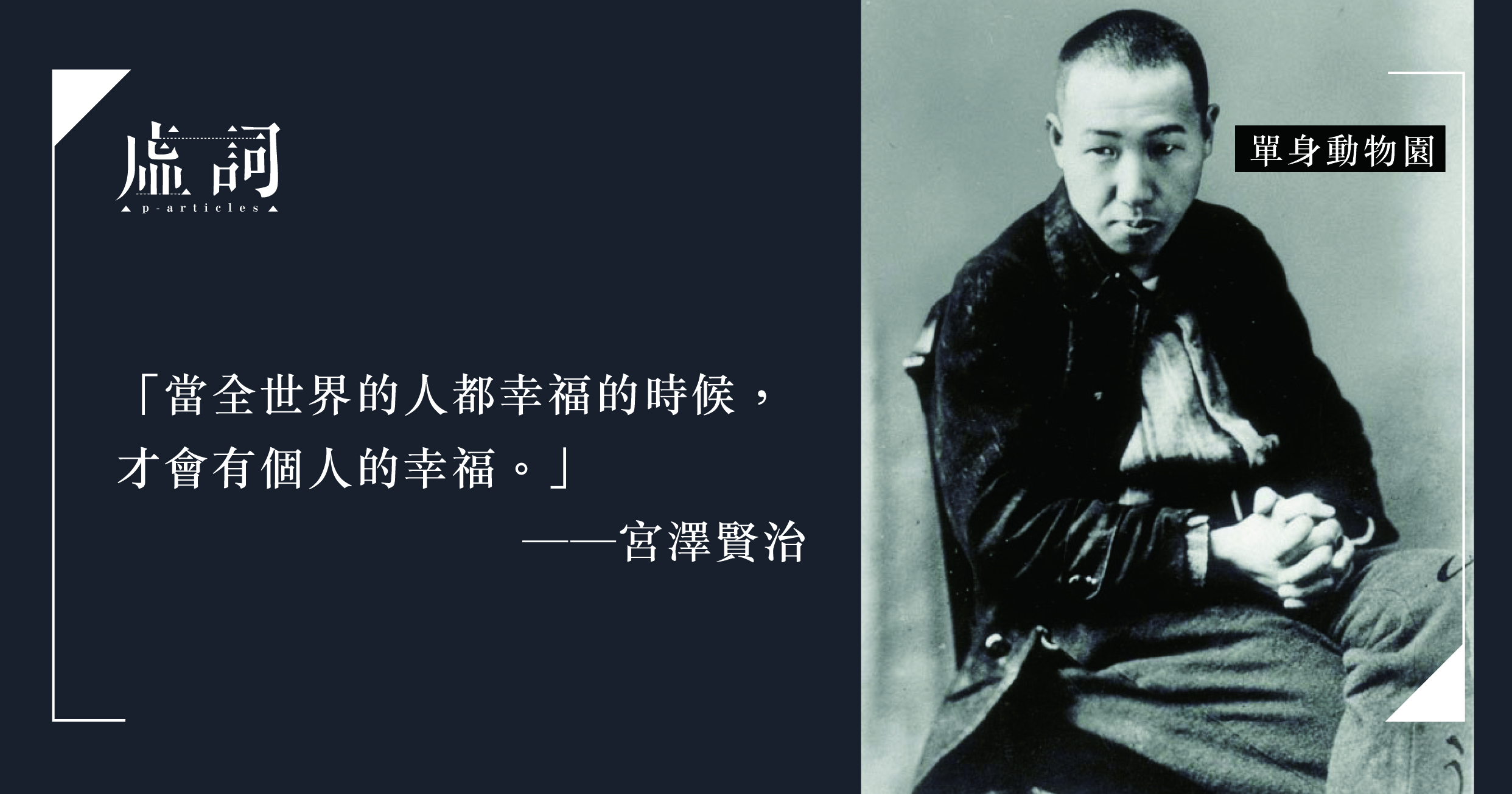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宮澤賢治:幸福究竟是甚麼?
單身動物園 | by Giovanni | 2018-11-28
「當全世界的人都幸福的時候,才會有個人的幸福。」宮澤賢治說。這位出生於日本東北部岩手縣花卷市的國民級作家,以森林、田野和鐵道構築起一個獨特奇趣的世界觀,他所寫下的詩句,彷彿醞藏著撫慰人心的魔力,每當風雨飄搖的時刻,都會有人把它拿出來重讀一遍。童話詩人宮澤賢治終年三十七歲,他的一生都在追尋真正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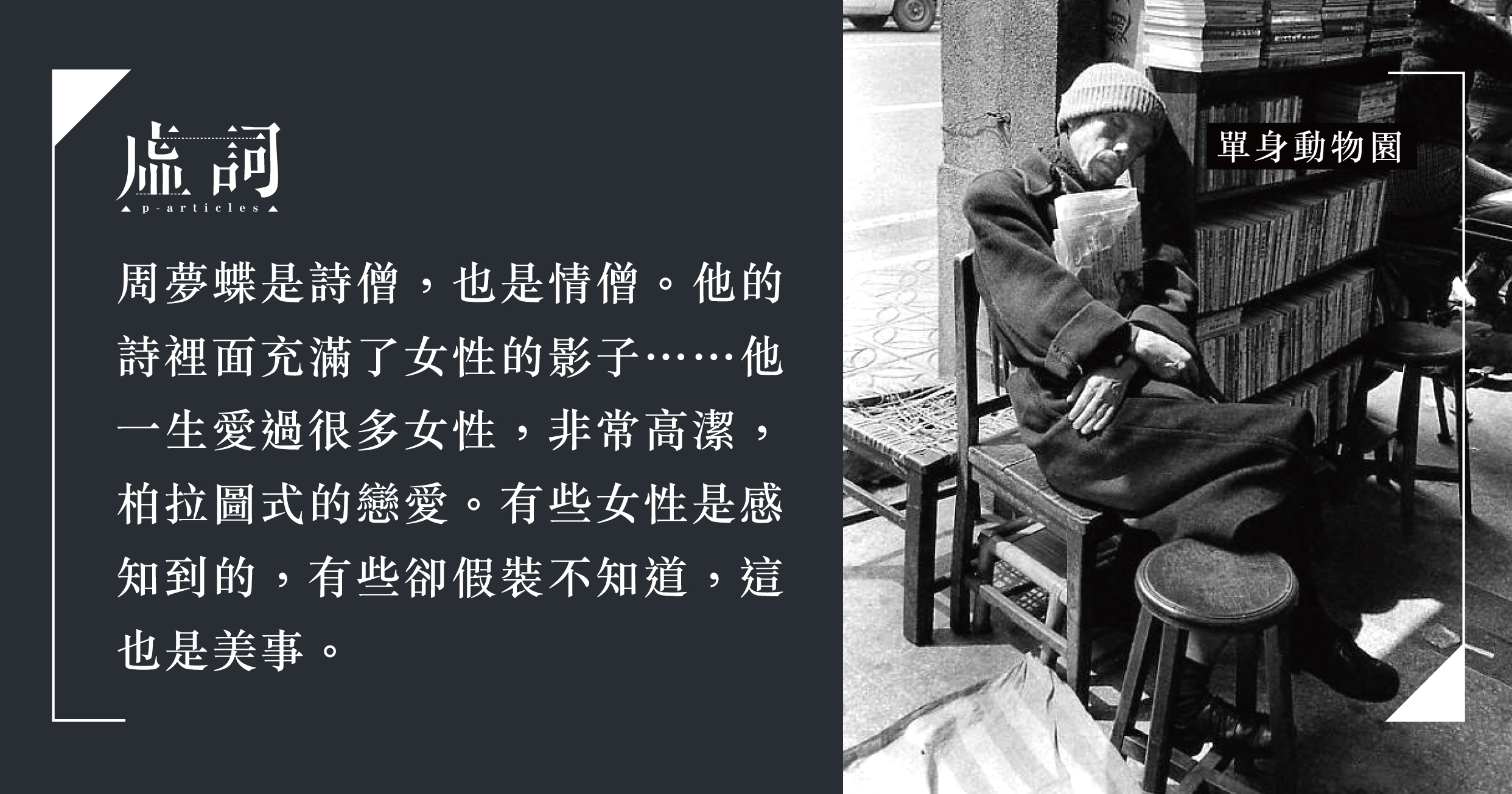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周夢蝶︰獨身也可是情僧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11-11
「他是詩僧,也是情僧。他的詩裡面充滿了女性的影子……他一生愛過很多女性,非常高潔,柏拉圖式的戀愛。有些女性是感知到的,有些卻假裝不知道,這也是美事。」詩人瘂弦曾經如此評說周夢蝶,「我們對待周夢蝶,要把他當作一個詩人來看,宗教裡的異像,宗教裡的境界,都擴大他的詩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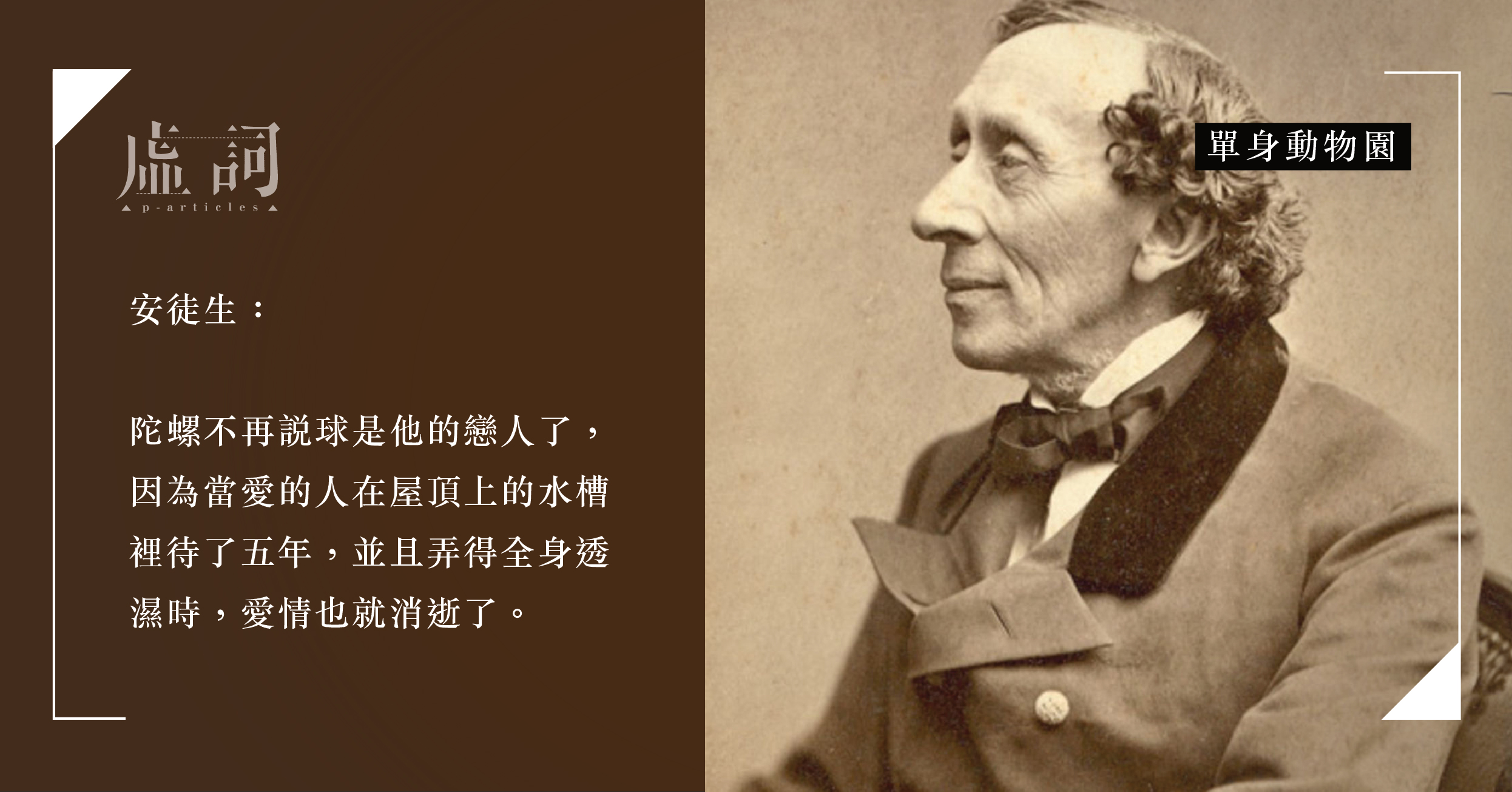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安徒生:單戀基因與悲傷童話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10-27
日前看到一則租屋信息:北京朝陽區安徒生花園,南北向,兩居現代化裝修,僅售2800萬。看到以自己名字命名的高檔小區,不知道童話作家安徒生會做何感想?實際上,安徒生常年在德國、意大利、馬耳他、希臘等各國漂泊、旅居,租屋是常態,而那個溫暖堅固的家、家中等候他歸來的妻孩,對他而言可能只是〈賣火柴的小女孩〉中因過於寒冷而產生的幻象。

【單身動物園】林逋:仙氣宅男無愛書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9-01-03
獨身,一個非常現代的概念。對於長期為「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控制的古人而言,終身不嫁不娶,已經構成了一宗嚴重的罪名。《禮記》道:「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天地萬物陰陽相合,理所當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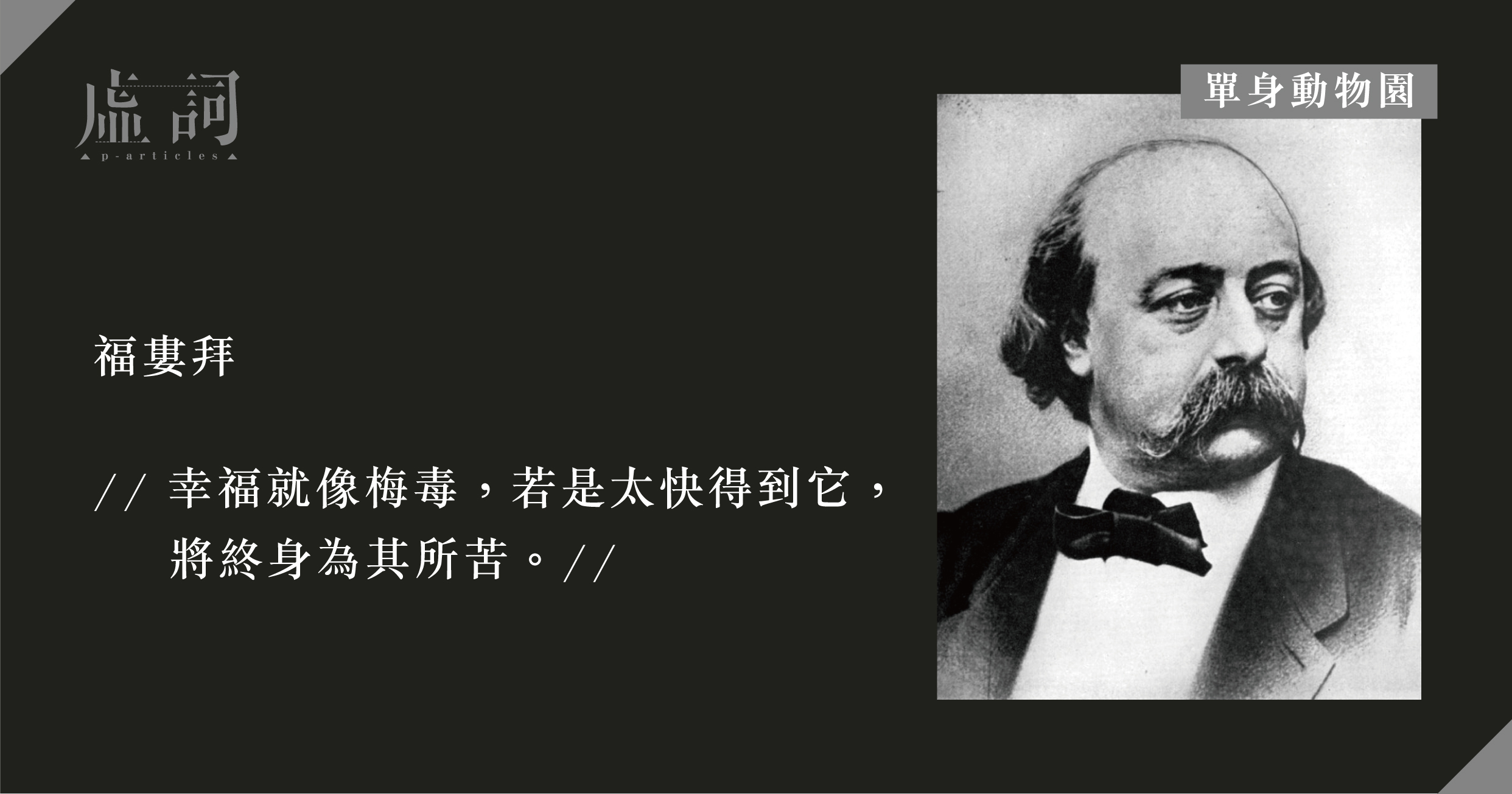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福婁拜:愛一個人就該避而不見
單身動物園 | by Perroquet Lulu | 2018-09-22
1880年5月8日,古斯塔夫.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在他克羅瓦塞的居所中孤單離世。左拉在他的訃聞裡寫道:「盧昂有五分之四的市民不熟悉福婁拜,剩下的五分之一則不喜歡他。」這位臃腫肥胖梳八字鬍的禿頭大叔,外形的確不討喜,而他寫的書也在一段時間被認為傷風敗德,但他的獨身卻非因他的外在條件,事實上,這位性情古怪的作家,終其一生都不乏伴侶。

【單身動物園】呂碧城:生平可稱心的男人不多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9-01-25
龍榆生稱她為「近三百年來最後一位女詞人」,英斂之讚其「能闢新理想,思破舊錮蔽,欲拯二萬萬女同胞出之幽閉羈絆黑暗地獄」,如今人們卻只為她冠上「民國剩女」的名號。倘若對呂碧城的了解再多一點,恐怕要覺得羞愧不已——這位二十歲就籌設「北洋女子公學」,三十五歲開始遊歷歐美各國,四十餘歲皈依佛門、完成不少佛學著作的神奇女性,又怎可能是被「剩下」的呢?

【單身動物園】卡夫卡:孤獨是對我巨大的誘惑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08-27
卡夫卡,捷克語中「寒鴉」的意思。在世四十一年,弗蘭茲·卡夫卡三次訂婚、三次悔婚,最終因肺病在療養院中離去,更在遺書裡要求摯友將其大部分創作、日記、信件都銷毀。「落葉聚還散,寒鴉棲復驚」,或許可作他一生寫照:本有可停棲之處,「書寫」卻總將其推離安全線外,把他拋入徹徹底底的孤獨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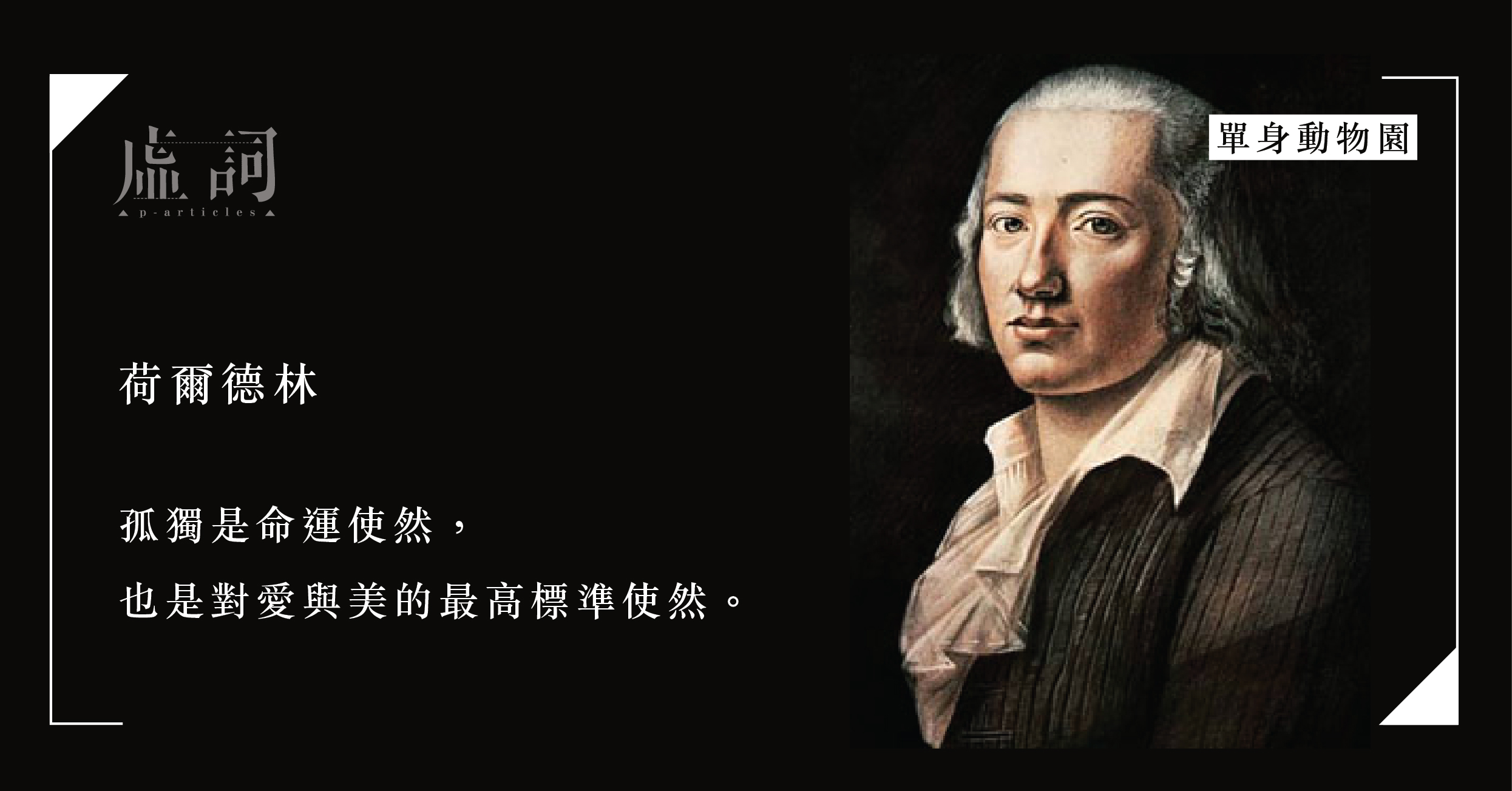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荷爾德林:讓我熄滅對你的愛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08-27
Umnachtung:大腦沉入夜色之中,也是精神疾病的意思。荷爾德林生命最後的三十六年就是在此黑夜中度過的,在塔樓中,隱遁、孤獨、瘋狂,構成了他的詞群。「我們卻被註定 / 得不到休憩的地方 / 忍受煩惱的世人 / 時時刻刻 / 盲目地 / 消逝、沉淪……一年年墜入渺茫。」在進入黑夜以前,荷爾德林也曾有過幾段顛沛的戀情;然而種種徵兆,也揭示著詩人孤獨的宿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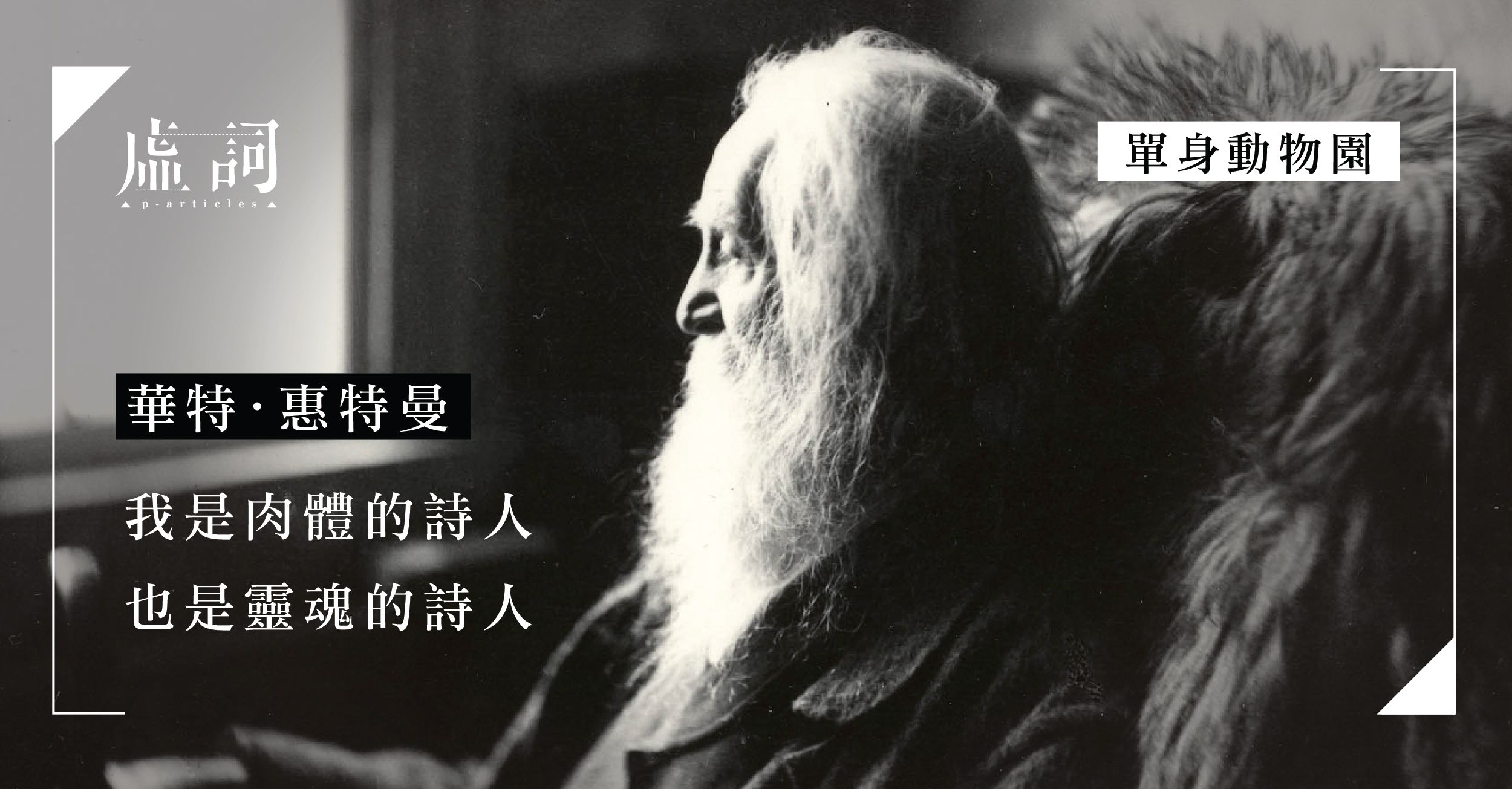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惠特曼︰我愛自己的肉體多於他人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08-27
華特·惠特曼的歷史名號數不勝數:「國民詩人」、「美國現代詩歌之父」……評論家瑪麗‧貝倫森也曾說過:「沒有惠特曼,沒有草葉集,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國。」其詩歌中的自然、民主、勞動精神影響過無數人。另一邊廂,其作品也以多性愛、肉體描述見稱,《草葉集》更曾因為「有一些詩的言語過於露骨」而被起訴、短暫地成為禁書。上述種種,都使得我們對這位矛盾重重的大詩人產生更多層次的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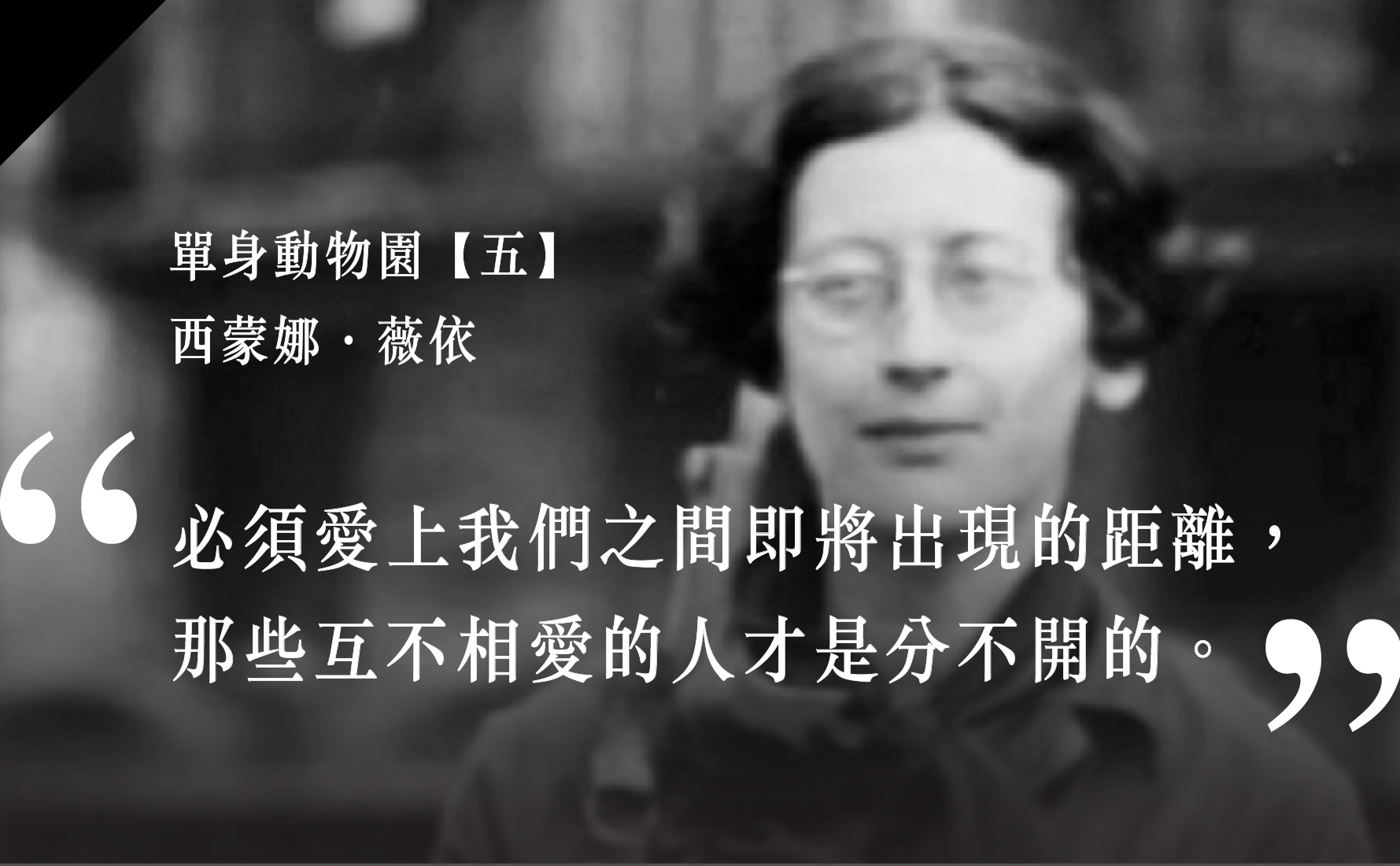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西蒙娜·薇依:黑斗篷裡的少女「老學究」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08-27
二十四歲的薇依辭去了相對舒適的學院教職,為了親身面對世界的苦難與不平等,薇依在艾士頓的五金廠工作開始了她的「女工生涯」,此後勞動、參戰,從未停歇。如此直到三十四歲,薇依羸弱的身體終是抵不了過度節食與結核病,在英國一家偏僻的療養院中黯然離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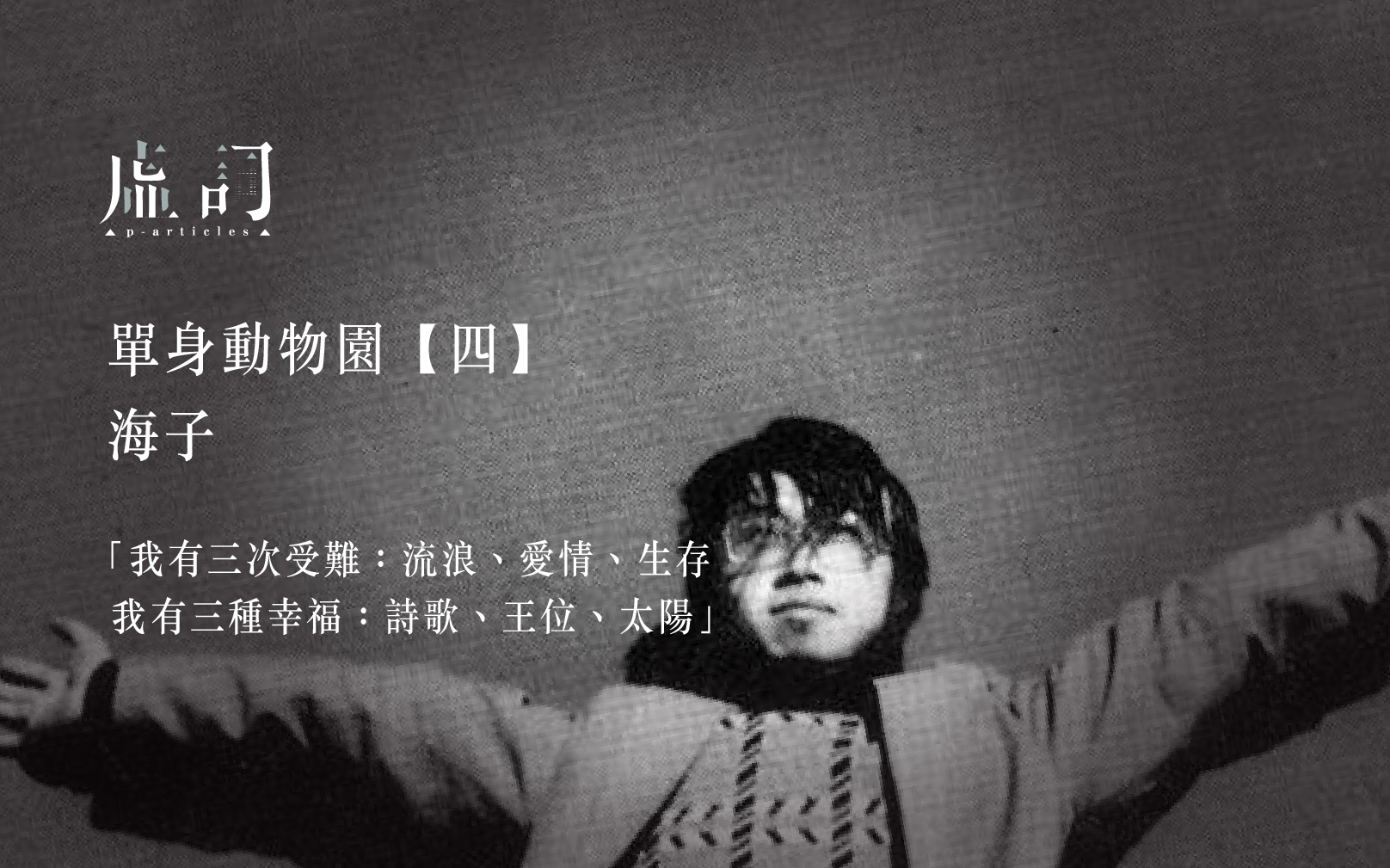
【單身動物園】海子:請別拿我的情詩去表白
單身動物園 | by ksiem-cheung | 2018-08-27
1989年3月26日,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以前,山海關的火車鐵軌上,靜靜躺著一位25歲的青年。他的胃裡只有幾瓣橘子——後來人們說那象徵著太陽;而他隨身攜帶的只有四本書︰《新舊約全書》、《瓦爾登湖》、《孤筏重洋》和《康拉德小說選》,也成為一代文青的標桿讀物。

【單身動物園】普魯斯特:讓我留在回憶的放映室
單身動物園 | by Bergotte Ma | 2018-06-24
去年情人節,一條短片引起了文壇哄動。在那條長一分十一秒的黑白影片中,可看到衣香鬢影的一對對男女絡繹不絕步下樓階,為首是一對穿婚紗和禮服的新人,樓階兩旁聚滿圍觀群眾,直至三十五秒左右,一位穿灰色長外套,戴圓頂禮帽,臉上留著八字鬍的纖弱男子形單隻影匆匆走過。雖然只在畫面逗留了三秒,但一位眼利的加拿大電影教授希華特翰(Jean-Pierre Sirois-Trahan)卻認出那人正是法國文學界王子——普魯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