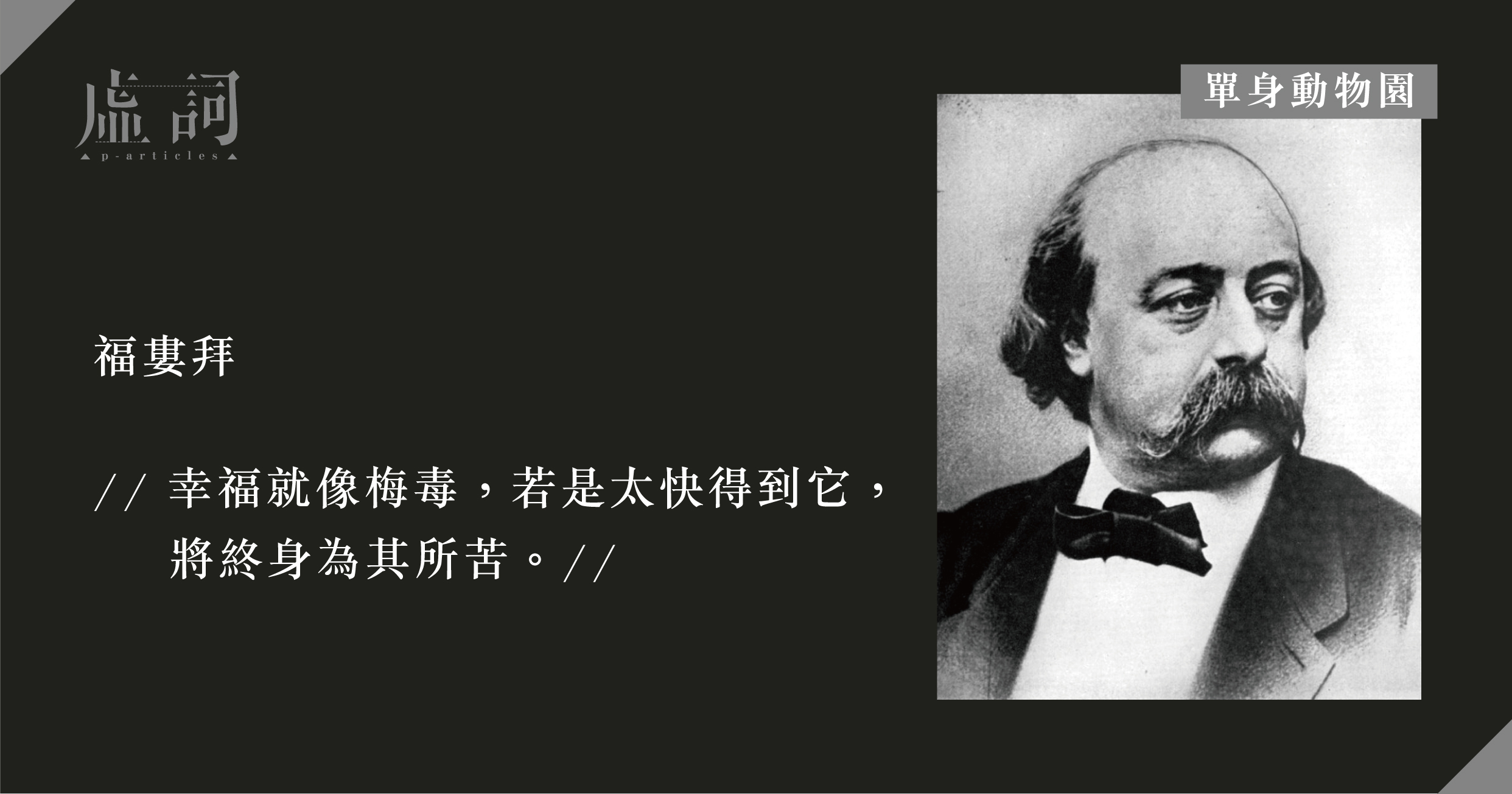【單身動物園】福婁拜:愛一個人就該避而不見
單身動物園 | by Perroquet Lulu | 2018-09-22
1880年5月8日,古斯塔夫.福婁拜(Gustave Flaubert)在他克羅瓦塞的居所中孤單離世。左拉在他的訃聞裡寫道:「盧昂有五分之四的市民不熟悉福婁拜,剩下的五分之一則不喜歡他。」這位臃腫肥胖梳八字鬍的禿頭大叔,外形的確不討喜,而他寫的書也在一段時間被認為傷風敗德,但他的獨身卻非因他的外在條件,事實上,這位性情古怪的作家,終其一生都不乏伴侶。
初戀:願吻你吻過的狗
福婁拜生於中產家庭,父親是醫生,他則被送到巴黎讀法律。他父親的想法與今天大多數中產家長無異,對於這位鍾情文藝的孩子實在不怎麼認同。後來福婁拜因為神經癲癇症發作而中斷學業,回到克羅瓦塞休養,這對他而言無疑是一種解脫,使他獲得創作所需的孤獨與寧靜,他飽受煎熬的巴黎求學期,最大的收穫可能就是認識了雨果。那年是1843年。
時間回溯到七年前,1836年,那年他十四歲,在都維勒度假期間,邂逅了令他終生魂牽夢繫的女神——伊莉莎.施雷辛格(Élisa Schlésinger)夫人,沒錯,她是別人的老婆。戴著大草帽,身穿細棉布洋裝的美麗夫人芳齡二十六,身邊跟著一隻大紐芬蘭犬,福婁拜看著便旋即墜入愛河,可惜她是德國音樂出版商的妻子,這同時令他陷入無盡煎熬。
他那無從宣洩的激情只能向施雷辛格夫人的狗傾訴,當他帶著狗在沙灘散步時,他會在某個隱密的角落蹲下來抱住狗,然後親吻那個施雷辛格夫人剛剛吻過的位置,可能是鼻尖,可能是腦袋,並在牠耳邊呢喃,說著便熱淚盈眶。儘管如此,他仍然與這位女士保持聯絡近四十年,而這段回憶則被他化作《情感教育》情節︰主角腓德烈克是熱愛文學的法學院學生,在一次歸家的航程中,邂逅了一名畫商的妻子,並被她深深吸引……
「他平生沒見過那樣富有光澤的深色皮膚,那樣誘人的身材,或那樣能夠被陽光穿透的纖纖玉指。他滿懷驚訝地望著她的針線盒,彷彿那是一件寶貝。她叫什麼名字?住在哪裡?有著什麼樣的身世和過去?他渴望看一看他家裡的擺設、看一看她穿過的所有衣裙和知道她都是與什麼人來往,她肉體的吸引力在他的心裡勾起了一種讓人痛苦的無邊好奇心。」
結婚?太變態了!
1836年的夏天,一直繚繞灼燒著他的心房,然而卻是他一生中經常回憶的珍稀寧靜時光。他說︰「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高貴的房間,我已把自己的磚封起來。」有說這段戀情令他此生再無法愛上另一人,但當然是誇大其詞。無疑,福婁拜是一個被矛盾統合的人。龔固爾如此評價他的友人︰「他雖然天性誠實,對於自己所說所為所愛所憎卻從來沒有完全真誠過。」
他過著布爾喬亞的生活,卻對布爾喬亞深惡痛絕;他仇恨政府,卻接受了國家頒發的十字勳章;他熱愛藝術,卻不認為藝術有任何意義(甚至像聳立在沙漠裡的金字塔般毫無用處);他渴望友誼,卻終日離群索居;他愛一個人,卻可以完全不跟她見面——這裡說的是另一位與他淵源甚深的女士,詩人路易絲.高萊(Louise Colet),順帶一提,她也是別人的妻子。
1846年,福婁拜與高萊夫人在雕刻家普拉第那的家相遇,福婁拜時年二十四,高萊夫人三十五(巧合地跟施雷辛格夫人同齡,還一樣是九月出生)。兩人不到一星期便搭上了,在往後二人的書信來往中,留下了更多讓後人了解福婁拜的線索。他曾在給路易絲的信裡寫道︰「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就是沉思、閱讀、坐在都維勒的海邊觀賞日落,或和朋友邊走邊聊上五六個小時,不過因為他(阿弗列德.勒.波提凡)結婚去了,我已經失去了這個朋友。」
從這裡可以一窺福婁拜對結婚的看法,他曾經對跑去結婚的阿弗列德.勒.波提凡抱怨︰「你在做的事很變態。」也曾對路易絲.高萊說︰「如果我是女人,我不會將自己綁在一個愛人身上。一夜情,可以;但是親密關係,免談。」以至後來路易絲的丈夫去世了,他也不願跟路易絲結婚,更告訴她應該去嫁給另一個人。
福婁拜一直跟路易絲.高萊保持若即若離的關係,有時甚至避而不見,他說:「真正的愛人可以十年不見仍然相愛。」然而,這或許只是反映出福婁拜自身的恐懼,他害怕路易絲入侵他的孤寂,害怕她佔據他的心靈,他害怕她,因為她太了解他,更是害怕自己會徹底愛上她。1855年,福婁拜與路易絲.高萊斷斷續續九年的交往終究決裂,他在最後的信裡對她說:「我就像隻公虎,牠陰莖頂端的剛毛經常會割傷母虎。」
或許,最美妙的戀情永遠是萌芽中的戀情,一如《情感教育》裡的腓德列克與友人戴斯羅回憶他們一生中最美妙的時光,那是多年前他們計劃去妓院的過程,如何仔細地燙髮、採花、滿心期待,而那次妓院之行卻從未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