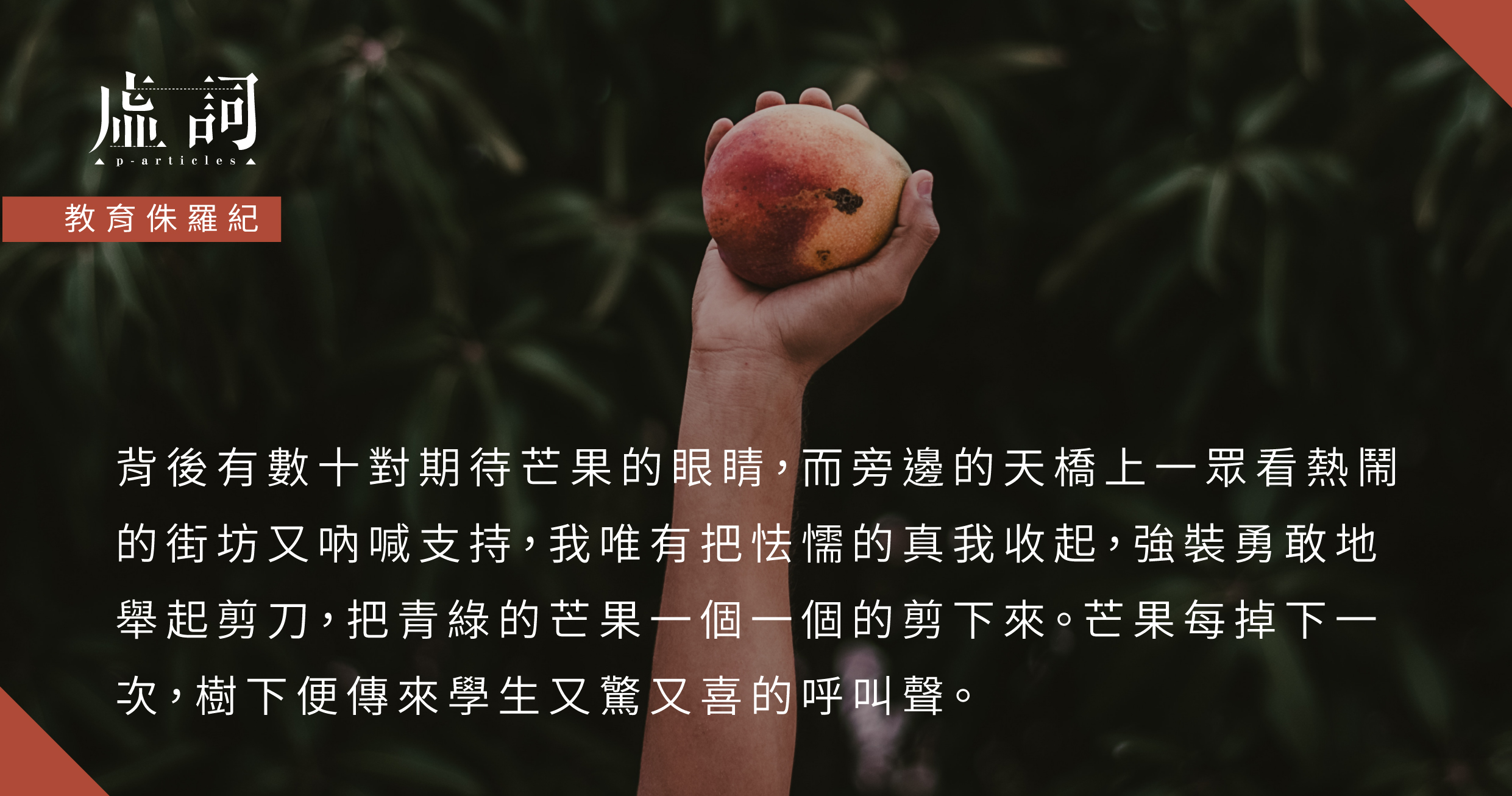【教育侏羅紀・師生關係】芒果樹——我教過的那間私校
剛來到這所跟喧囂的元朗商場只隔一街之遙的私校工作時,我不覺它有甚麼特別之處,要數印象較深的,是這裡的每一個地方都比一般中學小。可是,這裡麻雀雖小,五臟卻是齊全,三層高的白色校舍,有十多間大小不一的教室。地下一層是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雨天操場和教員室門口相連,穿過操場,盡處有一小舞台,後台旁邊有條只容得下兩人並行的小通道,每次上周會前,師生都走這條小通道通往和幼稚園共用的禮堂。從禮堂的側門走出來,會看見一個籃球場,球場鋪上藍紅相襯的保護層,醒目得刺眼,因此師生們都很難留意到球場旁邊,還種了數棵木棉和一棵芒果樹。
學校的禮堂是由教會擁有的,平日由幼稚園和中學部協調使用,已有三、四十年歷史,建築風格兼融中西,雖然室內是西式教堂設計,但安置報時銅鐘的鐘樓,卻是中式的亭台樓閣,綠瓦飛簷。禮堂平日會用來上周會之用,到了周日,教會便會開放禮堂讓教徒來進行主日崇拜。校方會隔周為學生安排周會,輔導組和宗教組同事會找來講者跟學生作演講分享。淡黃的燈光把如教堂的禮堂映照得肅穆安祥,亦同時喚起學生的睡意。此時,我作為班主任,職責便是克制自己不少於學生的睡意,用眼神示意眼皮半張的學生努力撐開眼睛,以及用正手和反手的巴掌,配合恰當的力度拍醒已昏睡去的學生。
學生其實是有精神奕奕地上周會的時候的,例如講者是位美女,又或者學生興致活潑,在周會進行時進行橡皮圈射擊大戰。遇上學生幹頑皮勾當的時候,便是我做偵探查案之時,我一發現情況異常,便要當場抓住小賊,加以盤問,從他們口中套取名單,以抽出其餘同謀伙伴。把他們一網成擒後,接著便是做訓育工作的時候,說說道理,說說規矩,最後我還要陪小賊們一起留堂,在禮堂做清潔和搜索每一條橡皮圈的下落。當班主任如當牧羊人,別人打瞌睡時你仍然要一眼關七,察言觀色,留意臭羊的行為與反應,出事時也要有留堂偵緝劣羊的耐性。
開花結果野孩子
學校如一座小城堡,四面都有圍牆,難免令人想起圈羊的圍欄,牧羊人把羊兒圑圑圍困在一片草皮上。師生身處教室內,又被四面白牆牢牢圍著,人自然很難提得起勁。我班班房的其中一面牆壁,尚有一排窗子,我們可以在那一排僅有的窗子望到剌目的球場,那是學生唯一的通氣處,學生們上課時,總會不時向窗子望望放空,我從來也不阻止學生這樣做,因為那是人之常情。
我在這所學校主要負責教授預科的中國文化和文學科,經常要講解先秦諸子的學說,學生一聽說我本課要講論語孟子便會呵欠連連,靈魂已先告病假飄向離學校一街之隔的商場去了。我有一位男學生,同學暱稱他「阿雞」,他亦是我的班長,當初選他只因他相貌溫文,略為蒼白的臉龐帶書卷氣,而且平日在老師前懂得自控,較少說粗話。但他有一壞習性,就是愛在上課時打瞌睡,不論上課下課時都掛起睡眼惺忪的眼睛。我教先秦諸子時,他必定是首名入睡的頭號種子。但有一次是例外的,那一天我要教莊子,一說起道家,便可以談談莊周夢蝶和知魚之樂,師生可以天馬行空,有理無理都可以辯駁一番,學生的反應會比教儒家時精神。
我那時正打算教道家萬物順應自然的概念,我可能也在圍牆中給悶瘋了,上課中途,突然生起怪念頭,叫全班學生走到窗前,一起望向出面的球場以及更遠的地方。我要他們在望風景發呆的同時,找一樣窗外的東西去反映自然之道。因為大家都要站立,班長阿雞是清醒的,他一聽我的發問,便說只看到眼前的球場,而其籃球給訓導老師沒收了,球場上甚麼好玩的東西都沒有了,哪會有自然的東西?我叫阿雞不要急著告訴我,繼續發呆,繼續看。再過了一會,學生開始發現球場旁邊原來還種了木棉和芒果樹,靠街的圍欄還有杜鵑攀爬著,雖然當時只是四月下旬,但香港早暖,因此花已紅了,芒果也結了。其中一個學生說:「SIR,開花結果,那算不算自然之道?」
我現在已忘記他們還找到甚麼反映自然之道的東西,腦海裡只記得一幕風景,畫面中的學生都很年輕,像窗外掛在樹上還未掉落的芒果。一排的芒果傻傻的站在窗前東張西望,他們都沒有睡意,只為老師提出的無聊課題去尋找毫不重要的答案。而老師最在乎的,其實是他們一顆顆反射著外面世界的眼睛。
雨天操場的角落,有一個簡陋的小舞台,左右兩邊放了兩個八十年代購入的擴音喇叭,餘下的空間只容得下十人在台上表演,再多的話便會擠得不能把幕簾關上。很多人都忽視它的存在,台上鋪上了三分厚的塵埃,學生用舞台前,都要先用濕毛巾大肆清潔。台板上留下的只有一個大人的腳印,那是訓導主任留下的。平時很少用得上小舞台的場合,只會在學生犯下嚴重事情,訓導主任因此要全級學生在台下罰站接受訓示時,才會有人踏上這小舞台。
學生有時也會上小舞台的,那是聖誕聯歡會,學生們會忽然發現學校有這麼一個小舞台,當天學生會會在小舞台舉辦音樂比賽。學生都愛看表演多於上課學習,到了那天一定不會有學生缺席,學校會赫然熱鬧起來。男的會偷偷用髮泥漿成箭豬頭,女的會偷偷上口紅畫眼線,面頰會變得緋紅。學生正值青春期,一定會把握可以犯規打扮的時機,我是教道家的,早已明白有時候要順其自然,要尊重動物的求偶期,對學生的反叛行為已見怪不怪。但令我眼前一亮的,卻是我的班長阿雞。他當天的打扮不再溫文,也漿起了箭豬頭,帶領一班箭豬頭樂隊成員,跳上了小舞台唱起BEYOND的歌。他穿起了白色的OASIS紀念TEE,子彈項鍊在他瘦削的胸前跳舞,拖著光影的手指在電子結他弦線上精神飽滿地躍動,歪歪斜斜的擴音喇叭發出他如曠野孤狼的歌聲。他在台上大聲叫觀眾呼喊他的名字,但那不是我們平日稱呼的「阿雞」,他的手舉得老高,歡呼著:「大家好,我叫三鷹!」我聽到後也跟著叫他新的名字,誰會認得台上的他是平日的睡雞?小舞台上的三鷹才是我清醒的學生,我那一刻終於明白阿雞平日在課室裡不清醒的原因。
那天我和一班學生都為了阿雞吶喊了半天,跟著他的歌聲唱歌,跳動著在圍欄內很少活動的身軀。小舞台發出的紅黃燈光,超越了光年,照耀著一班人日後的青澀回憶。
球場是學校最開揚的地方,它的一邊是校舍,另一邊面向大街,上面建有一條行人天橋,這條天橋和校舍平行緊貼在一起,校舍內的木棉、芒果樹長得高,部分枝葉都會伸延到天橋的欄杆,街坊走過,有些會順手把花和果子摘去。正因為校舍和天橋是如此的親近,所以天橋就如球場的觀眾席,學生在校舍的球場打球,就如在街坊前打表演賽,學生自然特別認真賣力。
我班學生是看「籃兒當入樽」長大的,本來上體育課時,愛打籃球,都不太懂得打足球,後來知道看「足球小將」長大的班主任只愛打足球,他們便轉打足球,並邀請我在體育課和他們一起打球。他們上體育課的時間,我剛巧沒課,而且他們的體育老師又是我老友,沒甚麼需要避忌,所以我也喜歡這個師生同樂的安排。因此,他們每周的體育課,都會上演師生足球賽,那個時候,不少街坊路過都會在球場旁邊的橋上憑欄觀戰。
師生同心 熱血救芒
但是有一天,我們沒有打球,師生賽取消了一次,因為學生發現球場旁的芒果樹長出芒果來啦,靠向天橋那邊的果子都被早起的街坊順手摘去了,他們提議趁果子未被全部摘去,救亡我校的芒果,而拯救行動時間就是他們上體育課的時候。
我和體育老師對望了一下,都感到為難,因為果樹長得好高,足有兩層樓高,我們雖然可以用校工在修剪樹葉時攀爬的木摺梯爬上去,但如由學生攀梯子剪芒果,他們一個閃失摔下來,那明天學校名字便上頭條了,那可不是學生說不要緊便可了事。但當望見一堆學生興致勃勃的樣子,我們又不想掃他們興。於是,站在校工的梯子上的,便變成了他們那位自小便畏高的班主任。至於學生的工作呢?我有如此安排:部分學生負責指點班主任在樹上落刀的方位,而班長阿雞則負責帶領同學,每兩人分成一組,在樹下各用雙手拉著冷衫的一端,把冷衫拉成一張救生網,一見班主任朝枝椏間一剪,便飛跑過去把芒果接著。
整個行動佈局,有如我小時候玩過的卡片遊戲機──沖天大火災,那根本就是一個遊戲設定。箇中分別只在於遊戲角色是接人,我的學生則接芒果。我站上有兩層樓高的木梯子上,只感到微風的力量也足夠把梯子吹得搖搖欲墜,只怕學生要接著的不是芒果,而是他們那位不應該在體育課出現的班主任。我當時心裡膽怯得不得了,還要拿著特製的長剪刀向頭頂上該死的芒果落刀,搖擺的果莖出奇的堅韌,而且又出奇的幼小,一刀很難俐落地把果子剪斷,當中的難度完全超出計劃時的預期。可見遊戲的設定和實行,要臨場才知道當中的分別。
我那時又要瞄準,又要平衡缺乏運動的身體,弄得我汗流如雨,比打球還要來得費勁。但由於背後有數十對期待芒果的眼睛,而旁邊的天橋上一眾看熱鬧的街坊又吶喊支持,我惟有把怯懦的真我收起,強裝勇敢地舉起剪刀,把青綠的芒果一個一個的剪下來。芒果每掉下一次,樹下便傳來學生又驚又喜的呼叫聲。這些聲音喚起了我的男性荷爾蒙,膽子好像大了起來,繼續舉手朝青色的果子飛快的剪下去。
旁邊的體育老師拍下了我們剪芒果的情景,但由於要舉起相機拍向天空,他只拍下了逆光的照片,相中人全都是黑影子,看不清樣子。但是,那毫不要緊,當時我居舉臨下,光線充足,下面抬頭望著我的眼睛,學生期待芒果掉下來時的期待之情,全都記在我的腦海裡。
剪下來的芒果,小部分掉進學生的冷衫上,大部分都掉在地上,皮開肉綻,兩者下場都一樣,都跑到了老師和學生的肚子裡。果肉跟果皮一樣青綠,酸澀得很,和想像的甜美預期有很大的落差。校工告訴我,芒果剛摘下來就是這樣酸的,要吃甜果,時間和環境都很重要。芒果放在米缸裡一段時間,才會變金黃,果肉才會變甜美。我把這個說法轉告學生,學生都說芒果的甜酸都不重要,能在上課時間偷偷摘芒果已開心透頂,比上自修課時玩「天下太平」好玩,而且,芒果由自己摘,特別好吃。我正想更正他們摘芒果的其實是他們的班主任,但班長阿雞已搶著說:「在學校睡了那麼久,到昨天才知道球場旁邊,原來有這麼一棵芒果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