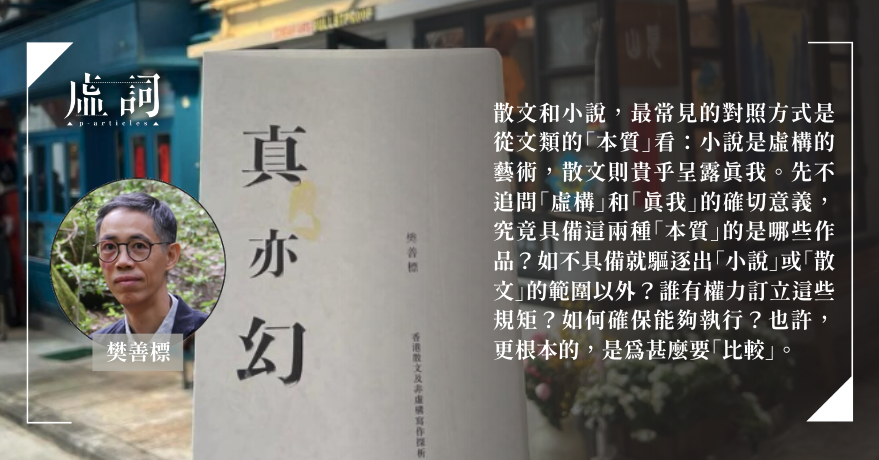翻覆波瀾真亦幻 ──《真亦幻:香港散文及非虛構寫作探析》前言(節錄)
書序 | by 樊善標 | 2024-02-08
一
散文和小說,用具體的作品來比較,固然可以不勝其異,也可以不勝其同。但最常見的對照方式是從文類的「本質」看:小說是虛構的藝術,散文則貴乎呈露真我。先不追問「虛構」和「真我」的確切意義,究竟具備這兩種「本質」的是哪些作品?如不具備就驅逐出「小說」或「散文」的範圍以外?誰有權力訂立這些規矩?如何確保能夠執行?也許,更根本的,是為甚麼要「比較」,為甚麼是和「小說」比較。
「散文」遇上「小說」,並非很古遠的事。東漢末年曹丕的《典論‧論文》提到:「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1]把八種文類分為四組,各指明相應的寫作要求。據說除詩文外,曹丕還撰有志怪小說《列異傳》,但他開列的八種文類沒有包括小說。曹植在詩文上的聲名超過乃兄,他對小說也不陌生,《魏略》記載,曹植初會名士邯鄲淳,施展渾身解數讓對方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項正是「誦俳優小說數千言」。[2]有趣的是,曹植當時精赤着上身,還表演了擊劍、跳丸和胡舞,之後穿戴整齊,才繼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等,[3]刻意把今天相提並論的「文章」和小說隔開。
這種區隔並不偶然,六朝文學評論鉅著《文心雕龍》全書共五十篇,其中二十一篇以文類為篇題,但沒有小說。明代的《文章辨體》和《文體明辨》,所辨文體多達五十九類和一百二十七類,連佛道二教張貼在道場的榜文也包括在內,卻排除了小說。明末時有「四大奇書」(《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的說法,《紅樓夢》更為清代文人所稱道,[4]但在晚清小說界革命之前,文人雖然可以寫小說,名山事業還是在正統的詩文。文章和小說雅俗有別,不可同日而語,也就不需要互相界定。此後,新文學運動的領導者在打倒傳統文化時,把文類的位階顛倒過來,抬高小說,貶抑文章(古文、駢文),兩者才有了相遇的機緣。
古代的「文章」和現代的「散文」不完全是同一回事。一九二二年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裏說:「這五十年的白話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說。直到近五年內,方才有他類的白話作品出現。」[5]他總結五年來──即新文學運動之後──的白話文學成績,按文類分為四點:白話詩、短篇小說、白話散文、戲劇與長篇小說。把長短篇小說合起來,就是後來所謂的新文學四大文類了。值得注意,胡適這裏指出除了小說,其他白話文類都是剛剛誕生的。他接着評論新生的「白話散文」:「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6]在胡適的文學發展藍圖裏,新文學和傳統文學是斷裂的,白話散文作為一個文學文類,也是從沒有共識處開始的,所以他要借助周作人的論說定義散文的「文學性」。現代散文史的最初二、三十年,不妨視為作者紛紛藉創作探尋「散文」如何成為「文學」的時代,贏得典範榮銜的作者也就創造了散文的「文學性」。而在探尋和典範化的過程中,白話小說早就成形,穩穩當當地作為對照面了。只有這樣追溯,才能解釋為甚麼我們總是拿小說來與散文比較。如果現代的小說以虛構為再明顯不過的標誌,「本色」的散文最好反其道而行。
散文文類的「本質」既是逐漸形成的,它自有可能在不同的條件下繼續變化。因此,對讀者來說,文類標籤不能永遠保證內容的「真實」;對作者來說,取信的工夫更需要在文類經營之外。沒有恒定的權威可供依賴,作者和讀者必須更積極地投入讀寫的關係裏了。[7]
二
黃錦樹二○一三年在報上發表的〈文心凋零?〉說:「抒情散文以經驗及情感的本真性作為價值支撐,文類的界限就是為了守護它。讀抒情散文不就是為了看到那一絲純真之心、真摯的情感、真誠的抒情自我,它和世界的磨擦或和解。這興許是中國抒情詩遺留下來的基本教養吧,那古老的文心。黃金之心。」這是有感於一再發現徵文比賽得獎散文大幅虛構內容,黃氏甚至提出「文風敗壞至此,或許文學獎的散文類是該考慮取消了」。[8]唐捐(劉正忠)在報上以〈他辨體,我破體〉回應:「文之類型、體式陷於混淆,要務在『辨體』;流於僵化,則要務在『破體』。在實踐上,這兩者最好同時顧及。」又說:「台灣主流的報刊文學獎,常具有新人獎的意義,一律採用『單篇匿名參賽』,以示看文不看人。……它可能會引發不安、製造亂象、鼓勵膺[贋]品,但也可能強化文類的生長能量。」[9]後來二人各自撰寫學術論文延伸己意,把評論徵文比賽擴大為深究散文文類的性質。[10]
童偉格、胡淑雯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一的〈編序》裡說:「一篇傑出的華語現代散文,首先是一篇看不出技術斧鑿之痕的作品;它唯一該具備的,是一道作者的聲音之流,衷誠地,鳴訴一段本真體驗,而使人共感於無論是記趣、憶往,或者,即使是那般艱難的傷逝與受創。」又說:「這部選集的編選範疇,除了一般認知的文學創作之外,也將涵蓋或許作者並無文學創作意識的自傳、傳記、報導,及任何就我們所知、能及時索讀的『非虛構的白話文寫作』。」[11]朱少璋〈虛構與撒謊〉則認為:「散文基於修辭的考慮而稍作『虛構』,並非不行,但散文的主體內容若與事實不符,就不能美其名為『情節虛構』,而該算是『撒謊』了。」[12]由此可見,在特定編選原則下,對散文真實性的要求變得更強烈,但在其他情況下,太多的偏離也未必容許。
各家所談大抵是在應然的層面。黃錦樹認定某些珍貴的價值──「文心」──絕對不容放棄,但如何強制作者遵從規範?劉正忠不完全否定虛構,他接納「破體」是着眼於文類將來可能有的發展,但怎樣的「破體」值得欣然接納?朱少璋主張細察虛構的內容,再判斷可否寬容對待,是折衷之道,但仍然要回應衡量標準的問題。不過在執法之前,是否應該先回到實然的層面,看看現有的散文作品──包括「非虛構」寫作──,假使弔詭地真有虛構成份,它們如何虛構、為何虛構,那些虛構對一般讀者和研究者可以有甚麼意義,以及虛構和散文的文學性有何相干?
三
本書各文大部份以散文或非虛構寫作為對象,但並非成於一時,各篇有其獨立論旨,不過多少總觸及這些問題:在沒有絕對約束力的紀實文類契約下,讀者可以怎樣披文以入史,可以怎樣看待紀實中的凌虛,作者又曾經怎樣尋求文學性的認證。現在聚攏成書,正好在散文的虛實和文學性這個主題下稍作梳理,並略為補充。
散文紀實的契約儘管沒有絕對約束力,但在一般情況下,作者不至於恣無忌憚地捏造。讀者如沒有確鑿的證據,也樂於預設作者所說為事實,因此展卷之時往往帶着認識真相的心態,要是閱讀時空遠隔的作品,更有重返歷史現場的期待。「輯一:世相」有三篇論文因編選《香港文學大系》的散文卷而撰。「大系」是一種獨特體式的選集,寓有藉文存史的任務,而其中的「史」要是僅僅用來附和既有的歷史論著或論述,那就未免多此一舉了。體察歷史的深邃,呈現過去的肌理,或流於大言不慚,但確是當時的目標。因此嘗試「配合時空背景及作者行事來重讀那些作品,毋寧是想細察:作者的紛歧感受、思考、主張,甚至幻覺、錯覺,以及在當時環境下有意無意的藝術創造」(〈人在亂離時〉)。所謂時空背景及作者行事,又以連繫發表場域者為重,乃從媒體、載體入手。「自然副刊不是孤立的,它從屬於報紙,報紙又連結在更大的商業、政治、社會關係網絡中,而在這些關係網絡上活動的是人」(〈香港散文的生產與變遷〉)。作品是活動成果之一,也就留下了種種連繫的痕跡;反過來,作品意義的詮釋,也當參考那種種連繫。這樣,諸如意識形態的歸屬、對國家民族的功過等大問題,就不致過於簡化地一分為二了。並讀薩空了、蕭紅、葉靈鳳、徐遲、穆時英等在同一場戰爭裏的作品,更令我感到需要探尋他們在底層的共通處:「複雜的心情在複雜的環境下如何表達」(〈如果遠方沒有戰爭〉)。人決非只有一個向度,這或許也是探討散文文學性更底層的問題吧。
輯一另外兩篇論文,〈抗戰時期見於香港《立報》的「五四」紀念〉以更廣泛的非虛構寫作為研究對象,擴展文化史學者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 的觀點──「把報紙理解為考察某一時代人的『探尋意義的方式』的憑藉」,──以考察層層中介(香港社會、香港《立報》、副刊園地、編輯人員等)與意念表達的關係,也旨在重申,同一時代往往並不是只有一個眾志同心追求的意義。在方法上,這和前面所說的閱讀原則是一致的。另一篇〈文學史「如何香港」的設想〉討論前行學者怎樣面對「主體性」概念的複雜和弔詭。這是研究香港文學史的基礎,也是我嘗試藉散文體察「世相」時,感到步步荊棘的原因,很希望能夠尋得出路,但到現在恐怕仍只能借用篇中所引述陳國球教授的話:把它「『問題化』(problematize),目的在於啟動思考,還未到解決或解脫的階段」。
[1]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縮印胡克家本,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721。
[2] 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王粲傳〉裴松之注引,頁603。
[3] 同上注。
[4] 參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篇「清之俠義小說及公案」,《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9卷,頁278。
[5] 沈寂編《胡適學術文集‧新文學運動》(北京:中華中局,1993年),頁134。編者注:「本文作於1922年3月3日,原載1923年2月《申報》五十周年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同上書,頁94。
[6] 同上書,頁160。
[7] 本節原題〈散文文類「真實性」之源〉,刊於《字花》第74期(2018年7、8月號) 「目擊者」專輯,頁53-55。此處行文略有修訂。
[8] 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年5月20日。收入黃錦樹《論嘗試文》(台北:麥田出版,2016年)。
[9] 《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年6月6日。
[10] 黃錦樹〈面具的奧秘:現代抒情散文的主體問題〉,《中山人文學報》第38期( 2015年1月),後收入《論嘗試文》。劉正忠〈現代抒情散文新論〉,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情動與批判:現代文學/文化中的語言、身體與政治」學術研討會(2019年12月)報告。
[11] 童偉格、胡淑雯〈編序:靈魂與灰燼〉,童偉格、胡淑雯編《靈魂與灰燼:臺灣白色恐怖散文選‧卷一 雪的重述‧萌》(台北:春山出版有限公司,2021年),頁12、13。
[12] 載《字花》第74期(2018年7、8月號) 「目擊者」專輯,頁50-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