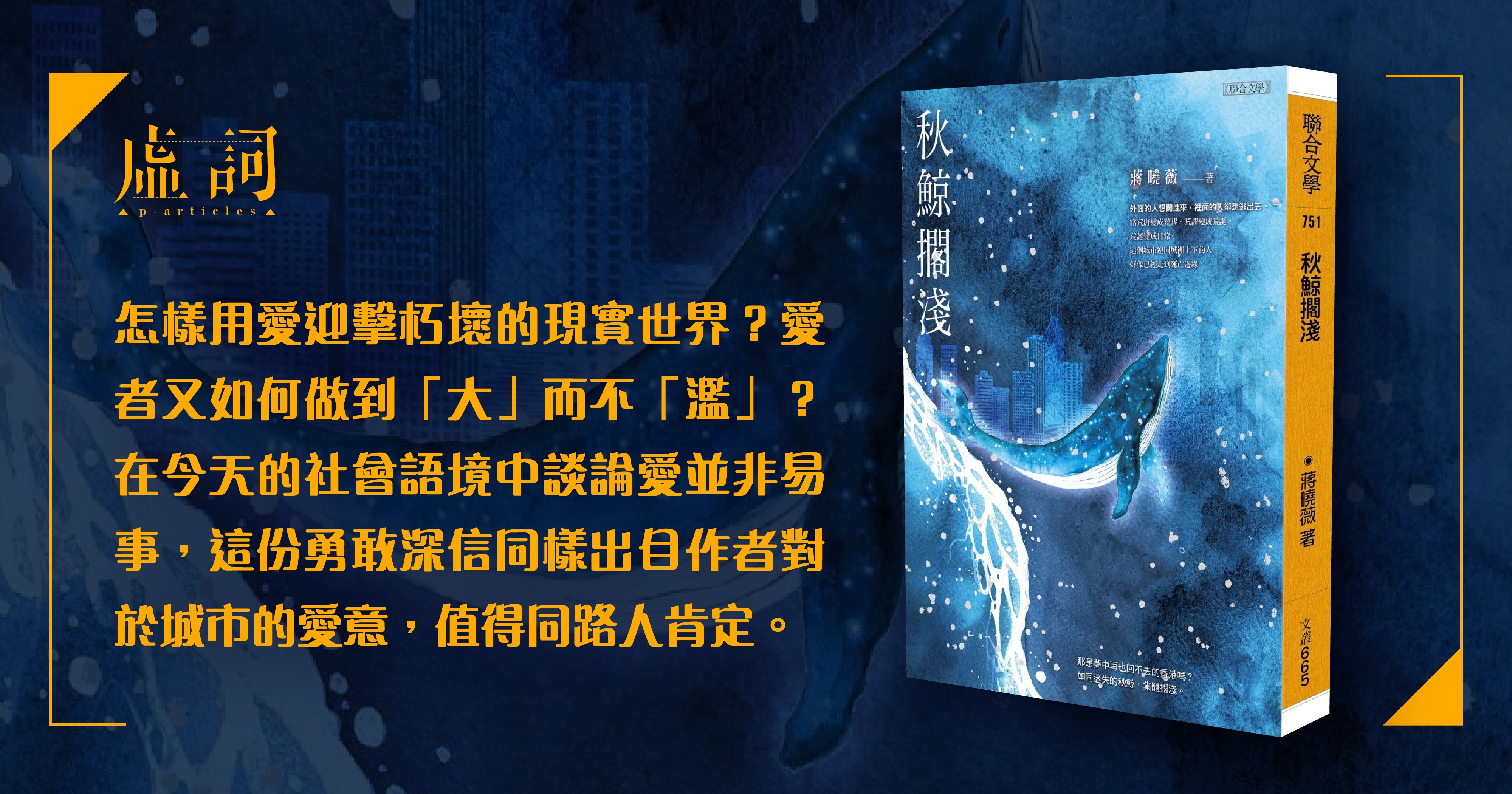某個讀者對《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的錯讀經驗
讀過謝曉虹新著《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之後,陳韻紅則以「錯讀」的形式,對書中內容有另一番聯想,並延伸到其他文本脈絡,如描寫電腦程式軟件被實現化的《玲音》,如《少女革命》中著名的學生會宣言。為擺脫曖昧而透明的殼,箱中女孩注定要戰鬥。 (閱讀更多)
單身不可怕,騎呢關係更可怕——從《文學單身動物園》中看單身的多樣性
書評 | by 謝豬 | 2020-10-21
《文學單身動物園》起題取自歐洲科幻愛情片《Lobster》的中文譯名,雖然各章節間缺少連結,既不分時序,也不分古今中外,卻呈現了單身的「多樣性」。單身的定義原來可以很廣闊,界線也可以很模糊:就算真的流落孤島,偉大的文學家們還是會寫一百封寄不出的情信跟心裡的對象聯繫,所以「絕對」單身是不可能的。 (閱讀更多)
李智良就是這麼annoying
書評 | by Melody Chan | 2021-01-21
所有你小心翼翼蓋好不要溢出來的對地球的不滿、對生活的厭惡,所有你努力維持著光潔的門面,他都要翻開放大,他都要叫你看看自家的後巷和灶底:你睇下你? 你睇下你?你聽唔聽到呀? (閱讀更多)
【無形.張愛玲分重作】葡萄仙子和其他
書評 | by 邁克 | 2020-10-07
邁克談張愛玲,話題落在馮睎乾整理的張愛玲晚年未完成散文《愛憎表》,「讀者有幸再一次漫遊祖師奶奶的童年和少女歲月,夕陽無限好的unplugged版在手,除了可以對照《私語》和《小團圓》,還能够找到種種夾縫裏的小趣味。」《愛憎表》裏引了兩句《葡萄仙子》歌詞,後者乃是中國流行曲之父黎錦暉一九二二年編寫的兒童音樂劇,原來張氏曾在《金鎖記》寫過,一九七六年寫給鄺文美的信上再提過一次,九十年代初散文又提,想來都與張愛玲念念不忘的童年回憶大有關係。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