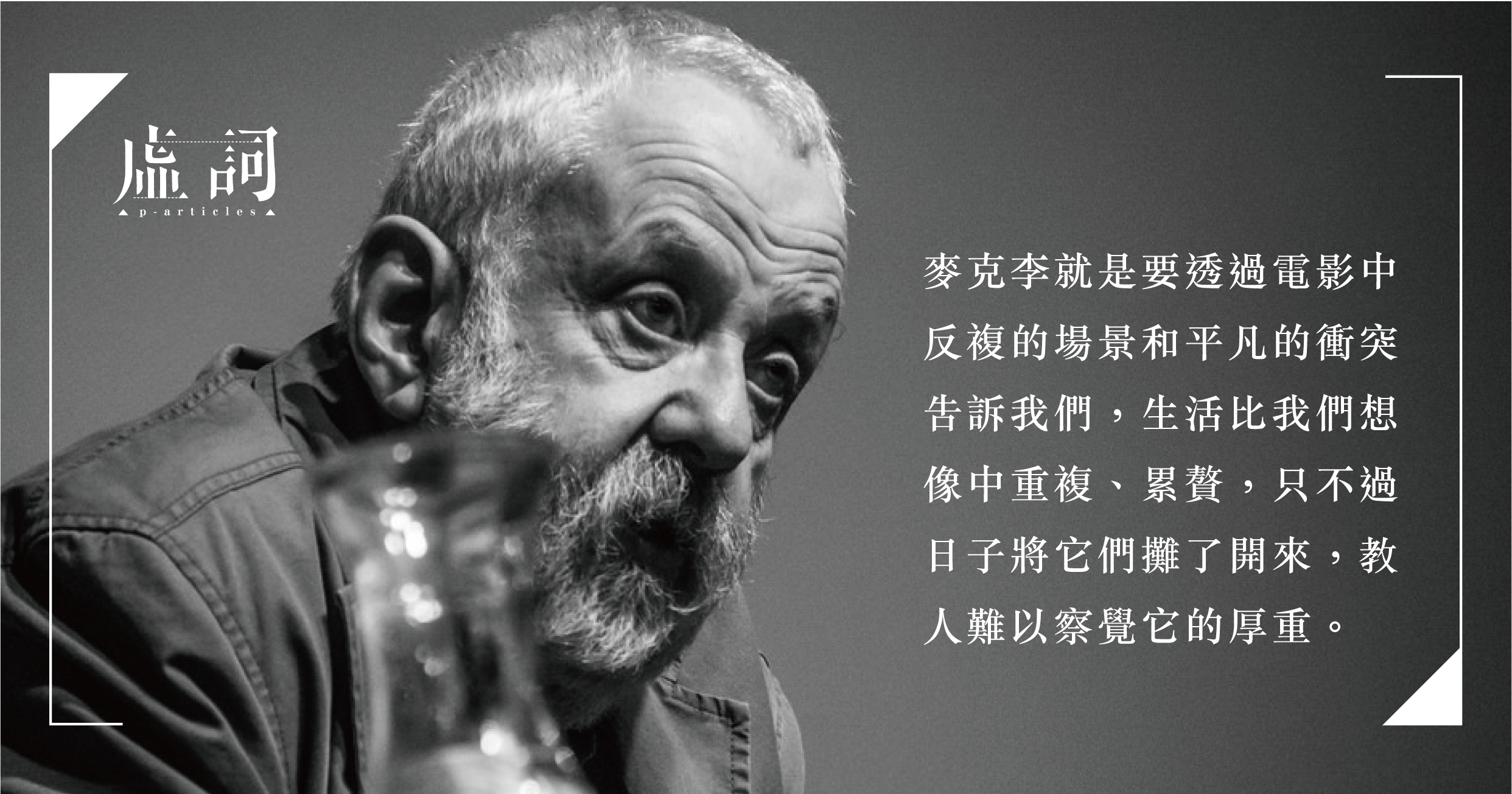英國導演邁克李︰電影是地上之鹽
試幻想和苦悶喝酒,它必然會先挑眉問,怎麼,你以為喝這個就能稀釋我?真真切切地打開話閘子以後,它才會開始神情恍惚,道起它的身世來,像所有曾裝作毫不渴望被理解的勞動者。年少時,它曾是敏感而脆弱的新感覺派,隨日月磨損,也有了後現代主義那種毫無表情與悔意的扮相。不過,唯獨有一種叫現實主義的姿態,如今看來過分直白,甚至被視作不怎麼「高明」,遠遠地擱在時間裡,鮮有人問津。如今想來,卻讓它覺得自有一股氣燄僨張,如肚中黃湯,久懷不滅。
時間回到六十年代英國,天色依舊灰濛。十七歲的邁克李離開曼徹斯特,懷著看見世界的願望來到倫敦。和其他許多熱愛電影的年青人一樣,看過尚盧高達的電影後,他被法國新浪潮徹底俘虜了,後又受到英國新浪潮的洗禮。唸戲劇出身的邁克李開始重新審視自己所受的傳統戲劇訓練,和那些受錄影廠所限、重視戲劇張力的精美劇作,再看看手邊採訪用的廉價輕身攝影機,也許在想,何不走就這樣到街上去?
摺疊人生的重量
向旁人推介邁克李的電影是一件難事;這年頭,誰想看過分真實的戲?畢竟我們都演過。李的作品極富「廚槽現實主義」色彩,而這種風格之所以叫廚槽,是取其平凡、平庸之意。此類電影的情節多在日常場景裡進行,擺脫了「佳構劇」的波瀾壯闊,直面現實生活的淡泊荒涼,以透視中下階層的艱苦與掙扎。乍聽之下,一切都似乎非常無趣,但若我們就此質疑這種電影的可觀性,是假設自己了解生活。邁克李就是要透過電影中反覆的場景和平凡的衝突告訴我們,生活比我們想像中重複、累贅,只不過日子將它們攤了開來,教人難以察覺它的厚重。
在《折翼天使》(All or Nothing,2002)中,邁克李透過三戶公屋家庭的故事揭示跨代貧窮的悲劇,場景僅在公屋前的空地、三家客廳、的士站、護老院間來回。透過不同的載客鏡頭,觀眾可以一窺作為的士司機的男主人翁Phil的枯燥生活。他載過時髦的女孩、為外遊感到興奮的小孩、失意的男人,本人駕駛時的表情卻一貫地空洞、困惑而憂傷,彷彿只有後座的時間是流動的。Phil無業的兒子不是在看電視就是在公屋前的空地遊蕩,以女兒為主的劇情全都在其工作的護老院發生;資本主義是一股無形的力場,錢能走多遠,他們就能走多遠。雖然電影少不免將中下階層的生活典型化,但場景的有限突顯了勞動階層有限的活動空間和社會流動空間,人們忙著生的同時也是忙著死,無日無之。

《折翼天使》(All or Nothing,2002)
電影方程式的叛道者
邁克李電影的劇情算不上是「劇」情,沒有高潮迭起,發展稀鬆平常而隨機,可是情感的累積卻處理得異常好,像玩層層疊一樣:平凡劇情的遞進不著痕跡地將角色推向衝突,角色的掙扎在觀眾反應過來以前已迅速瓦解。1993年的《赤裸裸》(Naked)可說是邁克李最荒奇的作品,電影講述了一個落拓潦倒的Johnny在不明情況下從曼徹斯特潛逃到倫敦,繼而遊蕩並展開了一連串的奇遇和與對話。Johnny的遊蕩完全沒有目的,「奇遇」的日常場景平平無奇,僅限於友人家、大廈大堂、遇上的人家中和街道等場景,九成情節皆由對話組成,予人感覺在看視覺化的《柏拉圖對話錄》。
這種設計與一般電影不同,一開始並沒有疑團、難題、危機或是衝突需要藉著劇情來解開;聽上去可能無稽,但外力的影響幾乎是不存在的,一切都以人物的話語、行動為主軸。Johnny一開始到訪舊相識的家,認識了舊相識的屋友Sophie,便開始攀談起來,他問Sophie會不會將自己形容為一個開心的人,然後又問:「你有沒有想過⋯⋯我的意思是,你未必知道⋯⋯但你可能已經走過人生中最開心的日子,而能瞻望的只剩下病苦與煉獄?」「啊,媽的。我過得一天是一天。」「是嗎?我有時候會選擇跳過某些日子。」後來說到人類孜孜不倦的太空計劃,Johnny不禁問,「究竟他們期望在上面找到甚麼是這裡沒有的?他們覺得把尿射得夠遠,就能找到長鬍子的猴子和牠那些毫無意義的垃圾想法嗎?」舊相好從工作回來以後,Johnny問她在倫敦的工作怎麼樣,潛台詞是,當年拋棄曼徹斯特的一切所換來的生活好嗎?她說還好,Johnny若有所思地問,「一切都如妳所願的一樣嗎?」「對。」「那妳所願的是甚麼的?」舊相好回答不上來。Johnny嗤一聲地笑,轉頭對Sophie說,「噢,對不起⋯⋯妳聽到嗎?她說一切都如她所願一樣,可是卻不知道自己所願的是甚麼!」遇上對未來充滿憧憬的高尚住宅守衛,他便大談世界末日即將到來,說到切爾諾貝爾在俄文裡是「茵蔯」(wormwood)的意思,而茵蔯在《啓示錄》裡從天而降污染水質,導致龐大人口死亡,又說到六六六隱藏在商品編號裡這種不真不確的謠言,用盡一切誑語來表達「我們根本沒有未來」、「我們根本他媽的一點都不重要,我們只是一個糟透了的主意。」《赤裸裸》和邁克李其他的電影一樣有冷峻的灰調、枯燥重複的生活規律、無法排解的性苦悶,可是Johnny有別於以往受困於體制的人物,既瘋癲卻在苦口婆心的促請人們──包括其他電影裡的角色──好好地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是否真的「不得不如此」;自己和別人所認為是生之要務的事,到底可能意義全無。

《赤裸裸》(Naked,1993)
邁克李的作品重新定義了電影體驗,因它的最終目的不是劇情,而是過程本身;隨著電影的推進,觀眾並非要期待看見一件事情的結果,而是要花兩小時與人物共同度過一段日子,變相將自己的人生暫停,倒帶,配上顯微鏡再看一遍。這也是為何邁克李精於描繪戴卓爾時期中下階層的無業情況、孤獨、人生的虛無、沮喪(dejection)和苦悶,因他擅於經營。大眾對邁克李塑造角色的技巧讚嘆不絕,可是李自己曾在專訪強調他的戲並非關於角色、也不僅屬於英國,而是關於「一個人存在的整體意義」(the whole thing of being what you really are),是全世界的共同悲劇。
對於被不被歸類為獨立電影、要不要保留一種曲高和寡的藝術情懷如此種種,邁克李大概毫不在意。對於電影票房,邁克李則笑言,那是自然在意,因為「我拍電影就是為了要讓人看的。」之於為何既然如此還一直拍小本電影,則是因為他那讓不少投資者卻步的製作方式——為了設計出真實、自然(organic)的人物,在電影製作階段,邁克李的電影並沒有劇本。他會用數月時間和演員不斷進行即興對話(improvisation),例如《折翼天使》就用了半年時間演練,實際拍攝則只用了三個月時間。邁克李所追求的是一個完整、立體的人物,一個在電影時間以外亦擁有生活的人物。根據角色設定,《赤裸裸》中的Johnny曾從事需與屍體接觸的職業,邁克李亦曾與演員到停屍間汲取靈感,但這層資訊在電影中完全沒有透露過,僅屬人物的人生經驗,亦是那些台詞的原始養分。
平凡即顛覆
我對現實主義電影的價值曾有過很多疑惑,正如我不相信米蘭昆德拉所說的「致知是小說的唯一道德」一樣。畢竟每一個故事都這樣可貴,用電影和小說來開闢現實中沒有的、用世界所無去探索世界所有的,豈不是更好?因此我一直無法回應友人的質問:「如果這部電影跟我的人生一樣,那我何必來看?」但也許是因為像看自己的人生,難得地份外分明的看,才至於為電影中濃重的沮喪而流淚,看著人們有大把不值錢的時間等著水沸煮茶,無所謂有聊無聊,才不期然為日子的某些空白而耿耿於懷。這是邁克李所認為自己的電影具備的「顛覆性」,一種地上之鹽的顛覆,平庸而必要,微小而不可缺少,以一段導演生涯來演繹《東京物語》(1953)中一段輕巧而迅速失卻的對話:「人生真是令人失望,不是嗎?」「是呢。」

(麥克李 Mike Le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