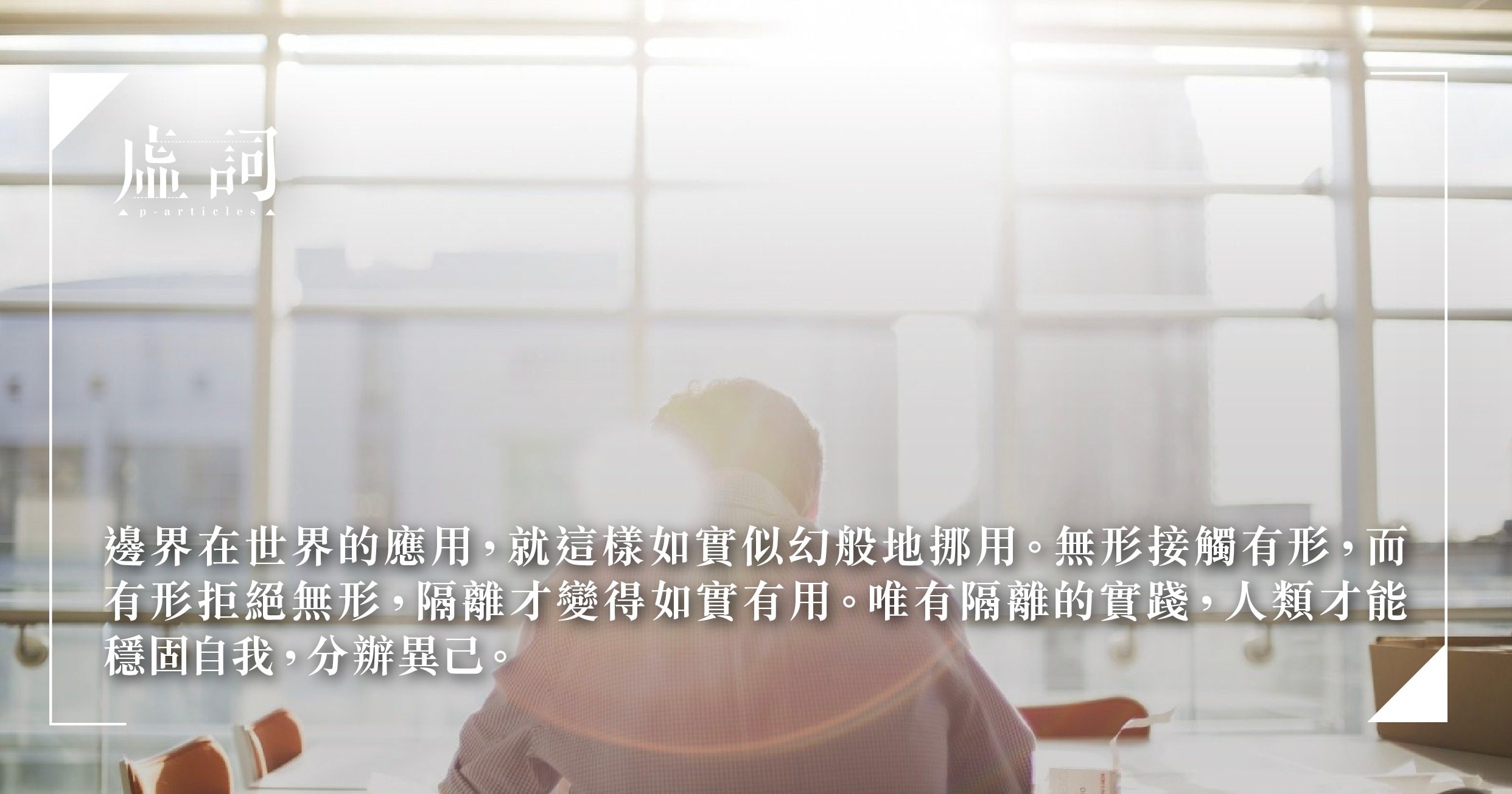隔離
小說 | by 蔡正軒 | 2022-04-07
最初是家兄開始注意到狀況,心跳突然加快、全身發抖,然後就卧床不起。後來是姊姊,咳嗽連連、周身不妥、軟弱無力。一切都來得措手不及,卻又不像真實發生,彷彿有一隻無形的巨手,忽然出現又突然消失,不曾存在卻又留下存在的痕跡。
母親說是廣播提及的新型流行疾病,有極高的傳染性,能夠在人們之間輕易寄宿,不需任何的許可,便能夠在人體之間穿越過境。由一個身體,穿越至另一個身體,也只需毫秒之間。而深信不疑的母親,也以毫秒之間的時間下感染。那有力的聲線,隨着廣播的聲浪愈來愈大,則相映得愈來愈小,彷彿即將就要消失。身體則倒卧在客廳的沙發,被厚厚的棉被包裹起來,誓要把自己隔絕起來。
家中唯一未被感染的,則只剩下我和父親,還有家中的龜。而我們則被他們重重地隔絕開來,透過他們重重的隔絕自己來隔絕我們。有某位專家提出:「為了減少感染源頭,應當實施隔離措施。甚至是逆向隔離,把一些甚至是未被感染的人群隔離起來,在非常時期實施非常手段。」
五十呎的房間在五百呎的公寓裏,則成為了兩人和一物的非常手段。我就在那晚深深地思考,細小的空間如何好好地過活下去,好好地渡過這段被他們定義的非常時期,也是說來奇怪的非常時期。
畢竟日常時期突然就變成了非常時期,而昨天才剛好正常地生活、談天說地,今天卻突然被住進了一個細小的隔離空間。明明只是一些不甚奇怪的身體症狀,普通不過的事情,卻突然被告知需要把兩者分離,把自己和別人分割,建起一道無形的牆壁用於隔離,隔離看不見的病毒。
病毒就突然憑空出現,卻又以看不見的原型活著。他們說病毒是生活在無形的空間(空氣)裏,所以我們能夠想像到的地方,都有可能存活着它們。就好像電子螢幕的螢幕前、廁所用於洗手的梓盤、喝水的水杯和手抦,甚至是把飯菜放進口裏的匙羹,都有可能佈滿着不斷散播的病毒。
而房外的家人則把剛煮好的晚飯放在房門之外,父親便把飯菜拿進來後把房門關上。當中大概只有兩秒鐘的時間與外界接觸,用於窺探外界的景象,然後就再次把空間分割。
在房間細小的空間裏,不太能感覺到時間的存在,縱然有着掛牆的時鐘把分秒分割,也都並不太過實在。我想這也算是非常時期的詮釋,便是難以詮釋時期。而早上醒來不久後便送來早飯、早飯後繼續躺卧在床上、午後則送來午飯、飯後或許選擇改變一下坐姿、最後晚飯便送了進來。也許就是這樣的生活,時間才會在生活中漸漸退場,淡出至難以區分時間在生活間的功用。
空間的認知也會被迫改變,世界的範圍會逐漸收窄至房間的大小。而在隔離的初期還會透過網絡與外界接觸,只是當閱讀到多變的網絡新聞,與不變的五十呎的房間互相對照,便會開始疑惑外在世界的真實。當網絡新聞還在如雷擊頂、世界末日,房間的窗前依舊照映着那四方框下的風景。
隔離的第三晚,我便開始懷疑父親的真實性。當黑夜來臨、聲色褪去,父親躺卧的上格床,在晚上開始寂靜無聲。而在下格床睡覺的自己,則在黑夜裏往上凝視。只是當視覺習慣黑暗之後,物與物之間的邊界就會逐漸消融,融入黑暗的領域。彷彿本來便不曾存在,房間就只剩下自己。
連呼吸的聲音也漸漸消退,寂靜無物。靜靜地躺卧在床上,黑暗的延伸彷彿在告示世界只剩下黑暗。就算心知父親睡在上方,卻也產生存在的疑惑。既然無形的病毒能夠存在,那麼有形的父親為何不能虛假。
況且日間的時間,父親也幾乎從不下床,也並不作聲。只有進食時才能看見父親,彷彿家人只有凝視時才會出現,而病毒也在凝視時才會染疫。也就在並不凝視的當下,病床上的家兄、姊姊和母親,便已不成形在客觀的世界裏。
然後便有了一個奇妙的幻想,假若眼睛捕捉畫面的能力,超過畫面成形的速度,是否就能看見家人的影像在眼前慢慢成形,就像家人只是一片隔離於外的移動紙片,而不是一個活生生存活於世的生命。
那麼就能夠理解,最近幾天總聽到房外傳來消毒噴霧器消毒時的聲音,和傳來一股誓要把生物隔離於外的異樣氣味。因為房外的世界,已經變成了一個隔離所用的集中營,而非本來的家。家人也換成了在四周巡邏的消毒人員,在那五十呎的隔離空間外,對着我們噴灑用於消毒隔離的消毒藥水,彷彿並不是要抺去那無形的病毒,而是一群有形的我們。畢竟無形的病毒本來無形,而有形的我們卻可以標示,標示有形的我們為可視的病毒,把我們視為可視的恐懼。在未知還沒有來臨之前,先撲滅未知,把未知定性為病毒,並連同恐懼一一除去。
而一切都只發生在我漸入夢鄉的朦朧意識間,在夢裏我卻變成了無形的病毒,失去了本來應有的身體,但仍存在於無邊的虛空之中。並由一處瞬移到另一處,轉入一個五十呎的房間之內,凝視一具熟睡着的有形軀體。它就像一具把外界完全拒諸門外的有形死物,透過刻意地把邊界畫出,仿效成活著的模樣。而無形的活物,卻被它看待成不曾存活。
邊界在世界的應用,就這樣如實似幻般地挪用。無形接觸有形,而有形拒絕無形,隔離才變得如實有用。唯有隔離的實踐,人類才能穩固自我,分辦異己。
而日光卻仍然如常地從窗外射進細小的房間,照射在地板上挪動的抺布。藏於抺布底下的龜,則在抺布的範圍內四處試探,試探牠最新所侵佔的領地邊界。而早上的我則略感喉嚨痕癢之意,微咳了兩下。龜則馬上從布內探頭盯視,彷彿在看着一堆無形之物,準備侵犯牠剛好劃下的領地,預備將其隔離。
而我則透過牠彷彿像看到了有形的病毒在空氣裏四處擴散,房外則傳來噴灑消毒藥水的氣味,宣示誓要把隔離的行動再次升級。我則試圖幻想自己逐漸分離,把身體的器官分門別類、各派自管,然後消融自己的無形意識,依附在那有形的死物裏,偽裝成身體仍然原好無缺,而不是由那因被凝視而被存活的病毒接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