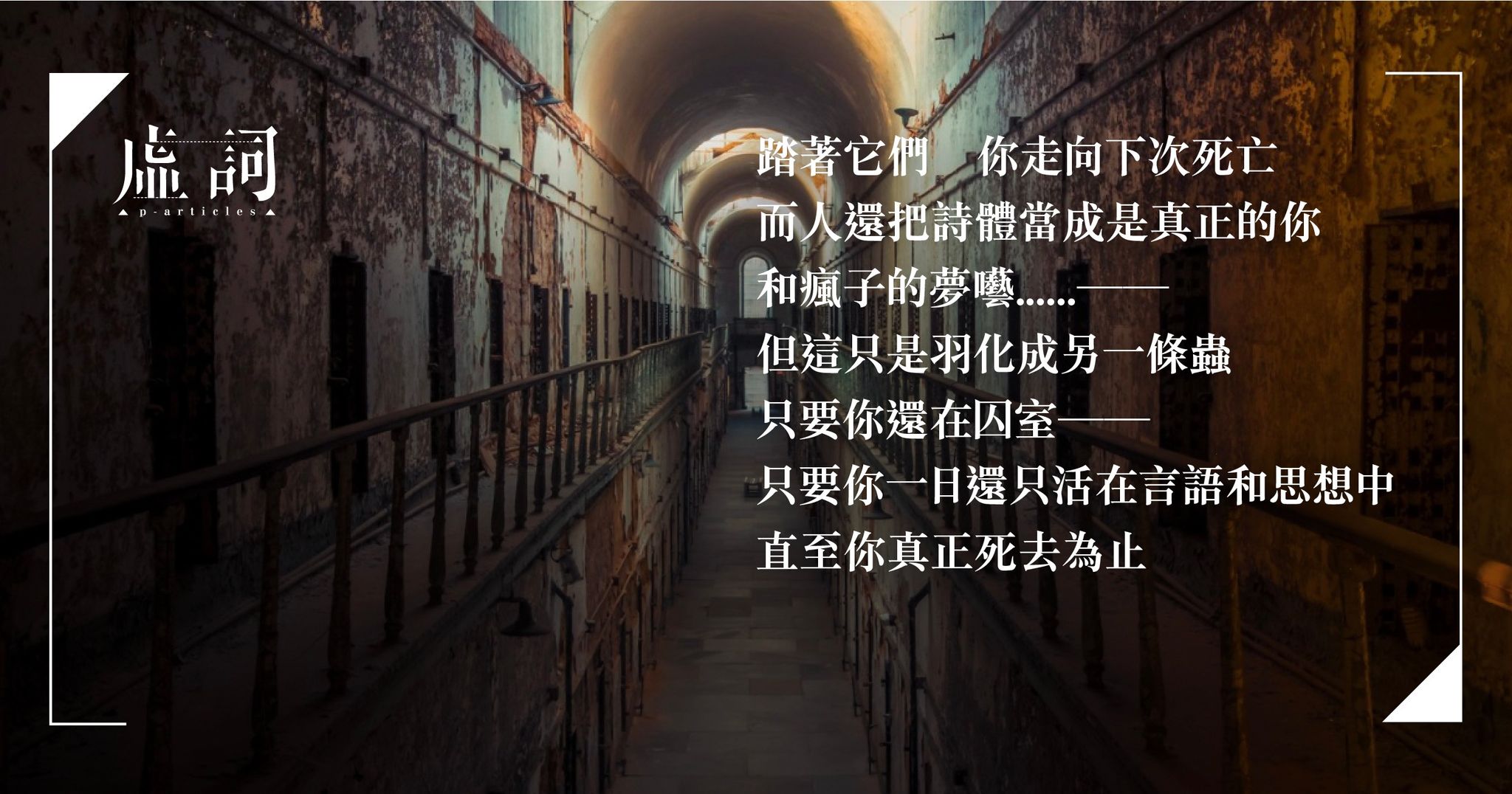〈懺悔錄〉、絮語
〈懺悔錄〉
我永遠愛你,對不起,希望能再見——獻nkw
1.
禿鷲在頭頂盤旋
太陽把屍體橫亙在大地各處
當黑色的雨
從大地下到天空
下到宇宙盡頭(而宇宙永遠膨脹)
擊中我模糊的身體 讓靈魂溼透
沒有地方寬恕我們:
屋子 高山 河川海流沒有攔住 雨
或哭泣
只是亙古迄今地沈默著
我於是狂奔 朝著夢裡——
夢裡所有事物如潮浪醒來 向我槍擊
遠處的戰爭 寫滿塗鴉的歷史 從無到無
像一切開始和消逝無聲的風 充滿青筋的陰莖......
一切是槍 準星向著我 一發接一發
沒有愛情 紅玫瑰綻放 一朵接一朵
我們該說什麼?當槍口塞著我們的嘴
當我們的耳朵只向自己敞開 當我們只唱自己的歌
這花海究竟爲誰燃燒?——
無處可逃......
夢裡甚至沒有一座關山讓我疲勞!
只片紅休掃僅從伊 留待
舞人歸
2.
禿鷹站在你身上 爪深入肉中分食著你
當紅 棉花無 聲落 地被 行 人踐
踏成碎 肉連同灰 燼化 作春 泥
種出日 後的 死
者 就是你們所說的春天嗎?
沒有額上的印記 人們就會爭殺一隻隻落水狗
好以血和暴力鍛造時間——過去 現在 和將來
只得退後一步 你吊起自己 像吊起一隻木偶
以思索 一次次擰乾自——它
以迎接下次洪水 每次它都浸歿得更深
無緣無故
笑是它在笑 哭是它在哭
死是它在死 走向它
不是走向你
凡無的 連它 所——有——的都要奪去
除了
凡有的 還要加給它 叫它有餘
——苦
但都無關痛癢了
一切都不是你的
如拂過你的風
如頭上三尺
地下六尺之事
一切都不是你的了
甚至不用閉上眼睛了
(那裡只有空洞兩個
通往過去 和未來)
現在 只有孤絕
當人只活在言語和思想中
只活在口中——無論是誰的口——囚
一號囚室:它人
肉袒伏斧質 你承認你殺人了
把自己完全敞開 內臟和罪孽全然剖出
但沒有上帝會給你額頭以印記
只有復仇和遺忘——人間的規則
如苦鞭鞭笞你的身體
把你的身體磕爛在牀鋪上
你的罪孽卻絲毫不減
沒有誰赦去你的罪 沒有寬恕
你才發現 人加冕你的荊棘之冠
賜給你的新衣
是無可擺脫的
正如絲索不總是讓人操縱木偶
當情感如巨浪淹沒你——身旁的人之時
你才發現 你——你們的內臟
從一開始 便全只是石頭
刻滿罪惡
二號囚室:自己
拿起筆 但總在之後
你才端詳每次厄運 每宗罪行
以罪人的口吻寫下詩
剖析一切
然後羽化 留下空洞的詩體
是你殺死了它們
踏著它們 你走向下次死亡
而人還把詩體當成是真正的你
和瘋子的夢囈......——
但這只是羽化成另一條蟲
只要你還在囚室——
只要你一日還只活在言語和思想中
直至你真正死去爲止
......
你看著自己的手
感到自己四分五裂
如土委地
你掃了自己一地還滿
梅? 捧起自己
自己就從手中流逝
你究竟應如何擁抱自己?
3.禱詞
你究竟在哪裡
當我如今以謙卑和悔意空出自己
懇求著你
僅僅是你
你究竟在哪裡?
一切如此空曠 除了你以外
卻容不下別的一切
雁群已經離開得七七八八
向南遷徙 我將留在北京
痛苦的首都
離雁將會對抗冬天
爲此 離雁需要回到你的身邊
而不是雁群 或詩裡
我會一直在死亡裡飛翔
直到沒有詩的季節
因爲 你 重新來臨——
或直到真正的死亡
來臨
絮語
寫詩越多,我就越覺迷茫。寫詩,能讓我表達自己最幽微、複雜的情感和掙扎。但越是想表達幽微、複雜的情感,我越需要琢磨用字,和內省自己的存在和心靈。最後寫畢,那些情感和掙扎,就成爲了詩,好似我把某部分的自己,交託給了詩,然後以最後一個字,爲它蓋上棺材蓋,亦因爲需要反省仔細、剖析自己,在寫作中,我不斷超越過去的自己。
藝術,可以幫創作者和其它人及自己溝通嗎?至少對於詩而言,我越來越不敢相信這個說法。隨著想得越多,讀得越多,見得越多,我的思想和情感就越複雜。我亦要用更複雜的文字來書寫自己。然而,當我寫下的詩越趨複雜,它就更難以被理解——更何況本身,就無人想理解它們——在理解的過程中,亦越容易被誤讀(暫時拋開詮釋學裡的問題不談)。如果誰藉由我的文字,看見了某些之前從未看見過的風景,我會感到榮幸,即使這些風景,不是我本身想藉其展示之事物。但畢竟,寫出來,公開自己的文字,不多不少,就是想被瞭解,想人們藉由這些荒涼乾癟的文字,看見自己。然而,寫得越多,公開得越多,我卻對一開始的文字越來越陌生,看著它們,就像看著陌生人般,閱讀它們,果真對瞭解我有何幫助嗎?對於近來寫下的文字,則我認爲抽象艱澀得,大概無人想去仔細閱讀它們吧;即使我剖析自己的工夫,似乎是越來越精密,但它人理解我,卻似乎是越來越不可能了——我理解自己亦然。自己變得越來越複雜,雖則我有越來越多的概念工具和創作技巧去剖析自己,但每每總不知道從何下手,要書寫多少,每部分要書寫得多仔細、具體,我纔算是坦誠地剖析和展示自己,給自己,及不存在的讀者看。用日常語言去溝通,則絕大多數人覺得我虛僞矯飾,那人們會覺得在詩中的我是更真實的自己嗎?但對於人們,我總感到困惑,當它人在批評我虛僞之時,我有時指出那並不是合理的評價,但總不被相信——我便感到吒異——居然有人比我自己更瞭解自己。我亦無法避免某些偏見,亦不能體驗它人之經驗。閱讀其它人的作品時,我真的理解了它們嗎?我於是漸漸覺得自我理解、被它人理解,理解它人,就像在攀一座不斷變高的山,而其成長的速度總比你攀爬的速度快。藝術的溝通功能,亦似乎變得越來越可疑。
我自己亦每每感到我的一切作品俱是垃圾,任何人都不應花費任何時間去閱讀它們——世上有無數更值得閱讀的文字。那麼,到最後,我畢竟是爲了什麼而寫呢?只是表達自己、抒發情感,把每日積蓄下的嘔吐之意,一下子傾注入沙子裡,繪成曼陀羅,在完成一刻,再自己把它們徹底圮墳嗎?
於是,寫詩,就像是對著鏡幫自己做化妝,你居然在過程中,慢慢進入了鏡中的世界,留下了本來的你和世界,在原本的世界裡,而鏡中的世界只是更荒涼,卻未必更真實;寫著寫著,甚至連自己位於何處,自己是誰,都不知道了。
你想,你早晚會進入語言更稀疏的高地,終身坐看云起時;但那和季節無關,你並沒進入無詩的季節,你只是悲傷地摒棄了語言。——但願你能一直寫作,即使只是像嘔吐般寫作,總比不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