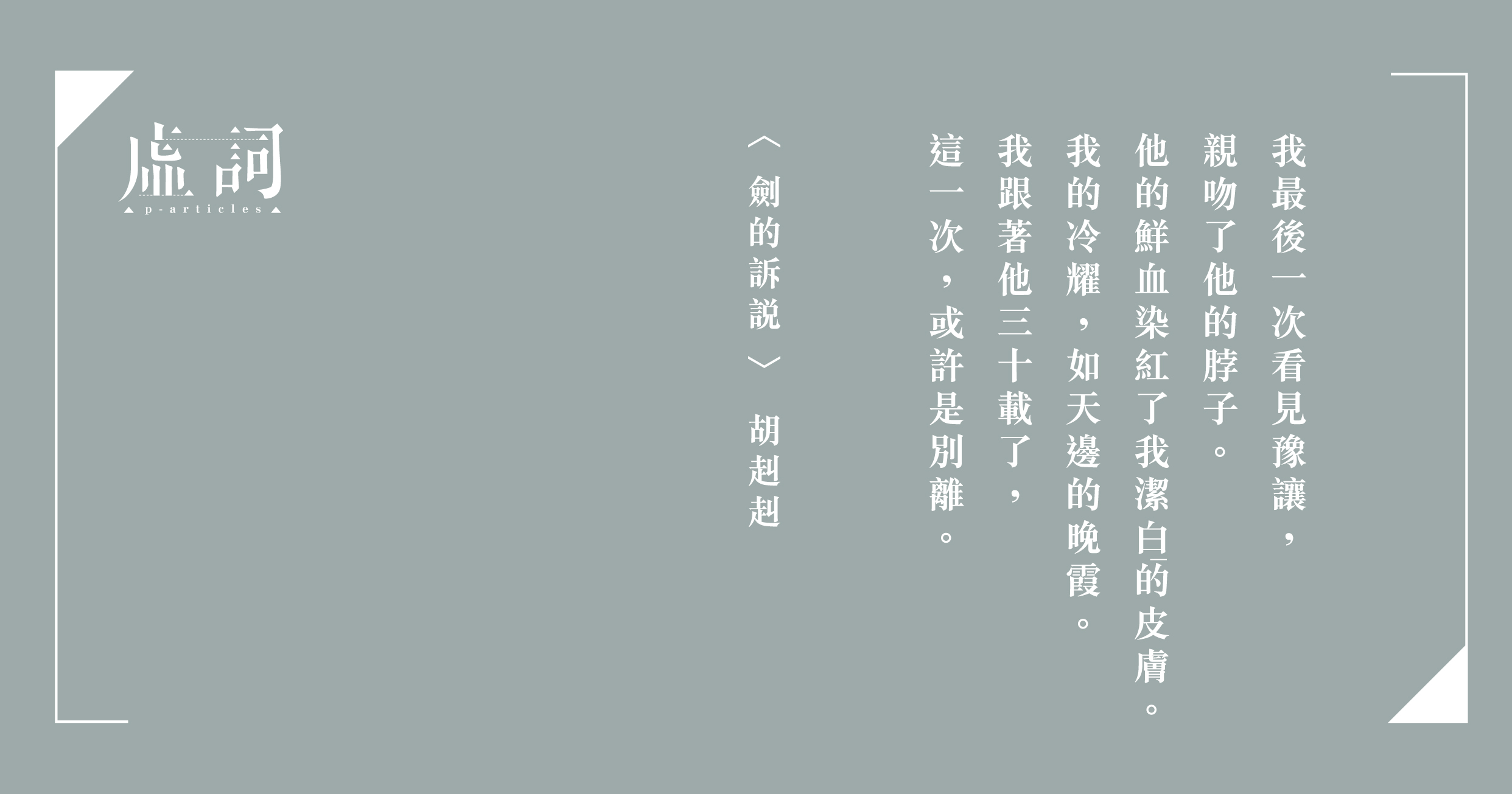劍的訴說
我最後一次看見豫讓,親吻了他的脖子。
他的鮮血染紅了我潔白的皮膚。
我的冷耀,如天邊的晚霞。
我跟著他三十載了,這一次,或許是別離。
豫讓的妻子是智伯賞賜的。
智伯大宴賓客,豫讓舞劍助興。
一片白光,籠罩在大殿上。
智伯擲杯,被劍擊退。每一滴酒都被劈成兩瓣。
酒香四溢,劍氣滿天。
智伯仰天大笑:得此勇士兮國不蕪!
眾臣子躬身附和:得此勇士兮國不蕪!
寒鴉掠過圓月。豫讓聽見一聲驚呼。
一條人影被智伯擲了過來。
一條人影如從圓月中淩空而來。豫讓收劍不及。
他向人影刺了過去。劍氣將衣袂摧開。
那身影霍然是智伯身邊的寵姬:娥非。
劍直奔眉心而去。智伯的心在顫抖。
他此時懂得了一個詞:花容失色。
這是他第一次正目看娥非,他忽然想變成一個詩人。
這一瞬間漫長得像一生。
劍在勢上,生死立判。
豫讓的手在顫抖。他應該感謝顫抖。
劍尖上移,刺落了娥非的發髻。
烏發散開,伊人閉目不醒,空中跌落。
豫讓奉雙手跪接。
智伯大醉前傳令:賜娥非於豫讓為妻。
我和豫讓曾經有過幾次人劍合一的經歷。
最懂他的人不是智伯,不是娥非,而是我。
最懂我的人呢?
他必得是一個超凡的劍客。
那一次在野外,豫讓生起了一堆火。
他把自己放在火上烤,終於烤成了炭色。
他把炭吞進了肚子,終於將聲帶灼壞了。
他知道沒有人能認出他來了。
娥非也不能。豫讓敲開自己的家門,乞討。
娥非拋出一盒糕點,將門合上。
糕點上的包裝已換了國別:智伯之國滅了,襄子之國取而代之。
國已亡,安可食。
糕點從赤橋上順流而下。
我默默地生銹,將劍光隱沒,烏黑無亮。
我和豫讓成為朽人和朽劍。
晉國改姓趙國。
智伯的人頭變成襄子的酒杯。
這是亂臣賊子懼怕的春秋。
義人行不義之事,必得以義待之。
襄子酒後如廁。遠遠看見殺氣,不敢近之。
讓左右搜查:豫讓被推出來了。
從他懷中,搜出了一把匕首。
「你為何要殺我?」
「我為智伯報仇。」
襄子沈吟良久,放還是殺?
放虎歸山,必有後患。
倘若殺之,則遭天下人恥笑。
此人良材義士,不如監視居所,擇機降之,為我所用。
豫讓是個好的劍士。他堅持裝修廁所時不帶劍。
以避汙穢。
這次行刺失敗了。
為了避人耳目,他在野外焚火自傷。
終於沒有人認得出他了。
然而事情並不一定真的是這樣。
趙家人一直在跟蹤他。
妻子沒認出他來,一個曾經是朋友的線人認出了他。
「你不是豫讓嗎?」
「我是。」
「你本可以投靠趙家,見機而行事。何必自毀身形呢?」
「君無二君,臣無二臣。若事襄子,即事二君,此一不義。既事其為君,又刺殺他,此二不義。」
線人策反失敗。
豫讓在準備致命的一擊。
赤橋上狹窄,僅容一隊通過。
襄子沒有前呼後擁的隊伍。
豫讓伏於橋下,準備一躍而起。
豫讓殘矣。身似炭,聲似啞。
他背上的長劍光芒隱沒。
我等待這個時機很久了。
國難,智伯死。豫讓逃山。他決計覆仇時說:「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那時我就想:「劍為寧死者鳴。」
有誰聽過劍器的轟鳴?
劍器嗡嗡作響。
襄子的馬在橋前受驚,前蹄高揚。襄子翻於馬下。
耳目上前報之:豫讓伏於橋下。
集市上眾散奔逃,一時間空無一人。
弓箭手、投擲手居高、臨下,鐵桶般圍於赤橋。
襄子抱拳:請義士現身。
豫讓緩緩起身。
三月的花開得正艷。
正是個緩緩歸的季節。
豫讓想起了娥非。
每當他練劍時,劍氣帶動故園的花瓣零落。
娥非悄悄用花籃拾起,然後放流於赤橋下,以水葬之。
時光的美好,在於珍惜。
佳人的命運、國士的前途,燦爛於一瞬。
既然命運早已註定,還有什麽值得牽掛?
豫讓御劍的境界,又高了一層。
襄子:「你仍要殺我嗎?」
豫讓:「要。」
襄子:「你殺得了我嗎?」
豫讓:「殺得。」
襄子環顧,傲然自雄:「你不能近我身,如何殺得?」
豫讓:「我只需要刺殺你的衣服。」
襄子大笑。立於橋上。
將袍寬解,拋向河下。
豫讓仗劍拔起,彈向衣袍。
豫讓快速刺出三劍。
一劍出,大地震動,地魂喪命。
二劍出,天光迸裂,天沖魄離。
三劍出,靈神激淩,靈慧魄出。
豫讓的聲音傳來:「我以命報智伯了。」
衣袍片片飄零。
襄子呆若木雞,打了三個冷顫。
三魂七魄已喪一魂二魄。
我刺向衣袍的時候,就知道這是永別。
衣袍點點落下,王威盡碎。
點點都是離人淚。
娥非悄悄拭劍的時候,劃破了食指。
這是我冰涼的一吻。
如今,我吻上了豫讓的脖頸。
他的鮮血染紅了我冰涼的皮膚。
我的冷耀,如天邊的晚霞。
(註:小說改編自司馬遷《刺客列傳》,豫讓的故事後以「斬衣三躍」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