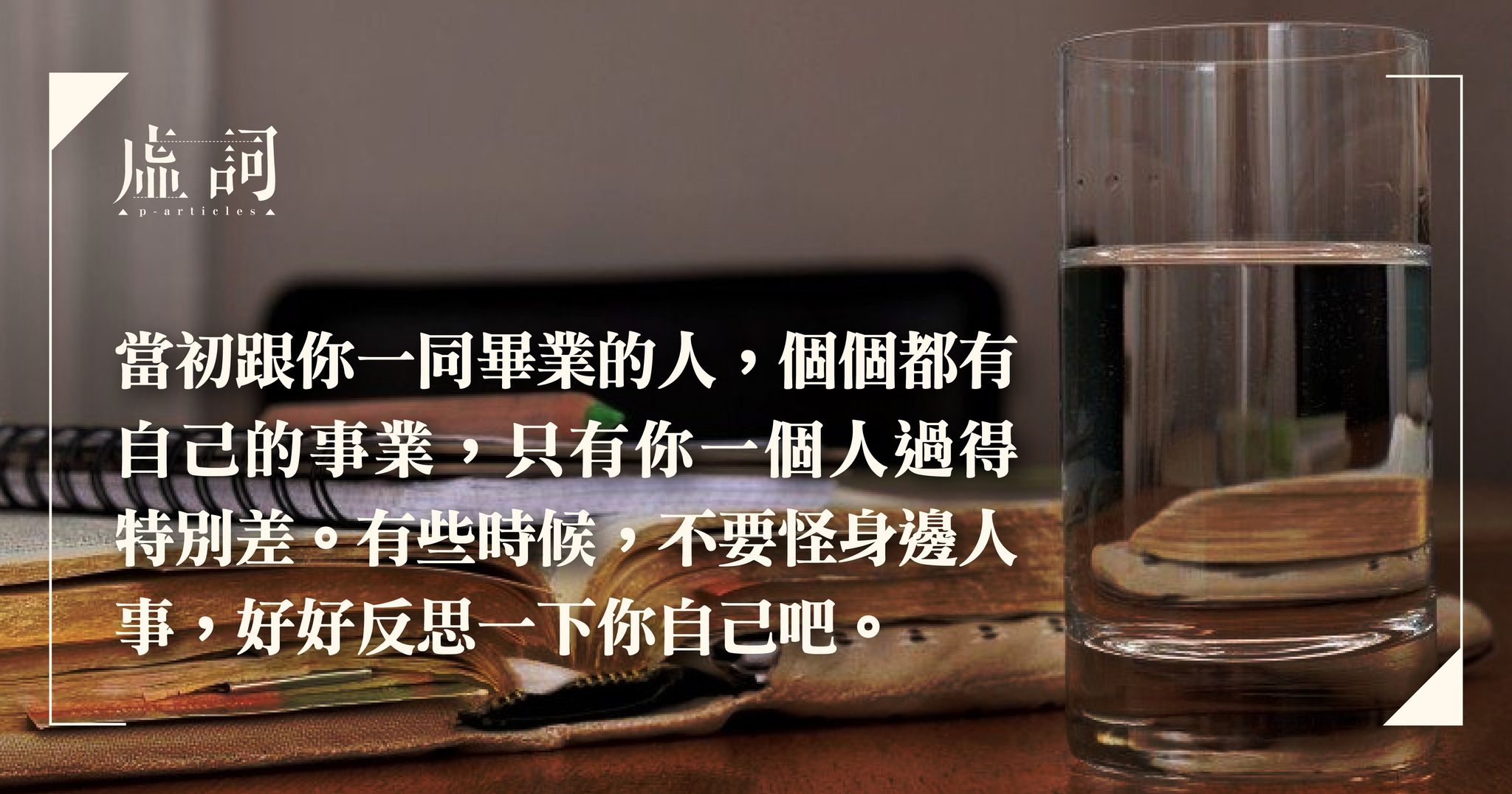中文系廢J的奇幻旅程
話說起來,我跟成劍並不相識。他的事蹟,是承風閒聊之間,斷斷續續講述過來。之後承風喜言成劍迷途知返,為賀其事,囑我做一篇文章。我見承風真切誠懇,不好推辭,遂應其托,將承風所述大概,稍加數筆,勉強串連各章節場景。唯其口述實在太過零碎,我又並非專業寫手,因此前文後理,總有不通之處。
至於成劍之事,奇奇幻幻,不予置評。不過看到成劍重新振作,由狂人恢復正常,往某地赴候補,作為朋友的朋友,理應替其欣慰。我雖然不是中文系的人,但也知道「讀中文系的人」是一道大題目,對成劍來說,似乎並不以中文人自稱,是不想、不願還是無可奈何,不得而知。
如果真要強行猜測,或許是因為無法忘記身分,但同時也無法承擔身分背負的期望。故以中文系廢J名之,中文系者,以示其眷戀不去;廢J者,以示其非學有所成,乃系中至弱之輩,所以一切行事,不能以此否認中文系的價值。系中自有能人,捍衛其尊嚴。
可不可以如此超譯,倒是無法說清。總之無論如何,成劍能夠「悟以往之不諫」,他應該也可以「知來者之可追」。是為小記。
「你可以當補習老師」
「我中文沒有5」
「但你不是中文系出身?」
「我中文沒有5」
「中文沒有5,你當初怎麼入中文系?我身邊的中文人,DSE幾乎都有5」
「你可以猜想一下」
「所以你真是讀中文系的人?」
「不對!我是讀中文系的廢J」
陳成劍滿斟一杯,舉高盡飲,後覺塊壘不澆,乾脆成支懟上,鯨吞而下,途中幾乎不用換氣。旁邊陪他的劉承風,見此情狀,不好意思打擾他表演,直到瓶酒將盡,才淡然說道:「不如你去中學做TA,反正你都做過,而且可以做住先,之後等你讀埋PGDE。」陳成劍起身行去雪櫃,又取出一打啤酒,「我們這群人,不是當老師,就是在當老師的路上。中文系和中文教育,都在同一道上。無咁易嘅,葉師傅!」陳成劍真不知道自己為何還能邊說邊笑。「等等,你先別說,這兩個字怎麼讀?」劉承風指這自己手機螢幕說。陳成劍湊近一看,見是「齟齬」兩字,順口說道:「嘴語」。「那這兩個呢?」劉承風拉到下頁,又指了「虈」、「(朱蟲)」兩字。「我不懂。」陳成劍開了罐啤酒,一飲一半。「你不是中文系的嗎?」劉承風說。「我真的不知道怎麼向你解釋。我好像在《山海經》見過,但詳細情況,無能為力。我覺得你可以請教字典系的人。他們才是專業。」言談之間,他又開了一罐。「我叫你上晉江文學城寫仙俠小說,你又嫌三嫌四。其他爽文你又話落唔到筆。雖然我不介意你一直寄居落去,但過多幾年你都成三十歲人,總要為自己打算一下。你讀中文系,總可以寫作創作吧?」這又是一個來自白堊紀的誤會,中文系又不是寫作系,解釋太多就沒意思了。劉承風的話,陳成劍有多少聽入耳,不得而知,總之他一頭栽到梳化,不省人事。劉承風見怪不怪,兀自收拾雜物,扶其進房。這一覺,直到第二日下午三點。
劉承風外出採購完物資,回來發現陳成劍躺在梳化玩手機,看樣子又開始一天的耍廢循環。「〈青春頌〉?好耐喇喔,2013年嘅事。」陳成劍手機聲太大,歌音外溢,劉承風一出來就聽見陳成劍播這首舊歌。「很奇怪,你不覺得嗎?角色換置了,風景也不同了。」陳成劍說。「你講話可不可以直接一些?」劉承風和陳成劍相處了好些日子,還是不太習慣他的說話方式,他常常無端就會短路,像是一團毛線梳理不出任何意義。用陳成劍經常自吟的金句來說,這好像叫「剪不斷,理還亂」。
「2013年,大學year1第一個Sem。以為未來一切可期。轉過頭來,流光易逝,頓成老餅。你有沒有看過那個MV?」
「個MV背景好似旺角行人專用區」
「那現在呢?」
「2018年殺咗區啦」
「那MV最後是什麼畫面?」
「幾個中年大叔久為生活所迫,抑壓之下,憤然反擊出走,最後不約而同來到行人專用區」
「許廷鏗那個牌上寫著什麼?」
「徵求追尋夢想的人」
「那個MV的背景是什麼?」
「旺角行人專用區」
「那現在呢?」
劉承風知道陳成劍又開始發癲,笑道:「大佬啊,你唔好咁癡線啦,神神化化,講一半唔講一半,我唔得閒理你,煮飯先。」劉承風知道重點不是旺角行人專用區,但確實所為何事,則只有陳成劍自己才清楚。又或者連他自己也不清楚。劉承風轉身行入廚房,不打算深究到底。陳成劍倒是跟著MV唱道:「誰亦會隨年變老,方懂得童年多好。等不到來年變老,才懷念,那種悠然腳步……」等到唱至「無懼雨水沾濕兩眼」,陳成劍兩眼忽然沾濕。
晚飯過後,兩人各有所忙。劉承風是真忙,陳成劍是真閑。他一人關在房裡,無所事事。想讀一下書,一時又拿不定主意。長篇太長,短篇太短。這樣想,中篇不就是最佳的解?好,我決定不看。陳成劍又自雪櫃取出幾罐啤酒,關回門,熄掉燈,拉罐一聲清脆,酒入騷腸,思緒開始奔逸,陳成劍一直很愛放任這群脫韁野馬,畢竟順著馬蹄亂跡,總有新天奇景。紅紅藍藍,黃黃綠綠,黑黑白白,灰灰蒙蒙。陳成劍望不穿,想不透,一陣厭煩,酒意篡奪思緒,竟其癱睡椅上,知覺盡失。燈光滲透窗戶,各種光影在他身上交替變換,而他,已無暇拉下窗簾。不過對他自己來說,光影灑遍其身,屬於放任?抑或不知道?還是不阻止?一切發問都是偽命題,一切都無關宏旨。不重要了,是嗎?光影依舊交疊成文。不言不語。
「淮左名都,竹西佳處,解鞍少駐初程。」吟詠之間,四周迷糊漸次剝落,學校已是一座空城,山上山下,無燈亦無人。所幸記憶尚未淡薄,乘著昏微月色,兩相輔成,昔日輪廓,依稀可窺,事所未慣者,唯在太過安靜而已。陳成劍身處下山近港鐵站的出口。他記得運動場附近有條上山小路,每當行進半途,人跡殊絕,遇到光所未照之處,赫然驚心,總以為暗中別有鬼物窺探,因而每有半途而廢的意欲。如今既然燈光全失,自身反似融成一份子。光暗比例不太平衡,陳成劍的影子也有點迷糊不清。我該不該寫篇短文,紀念與你告別?陳成劍對著那殘缺的影子說話。而影子當然沒有理會廢J之語。
他沿著小路上山,一直走到山頂圖書館,氣不喘,汗不流,恰有微風,略覺清氣。不過山頂也沒有剩下多少風景。這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無法判定物是人非。天光暗淡,路途本身就已經難辨,更何況四圍山色。《文心》第一篇說的是什麼?「日月疊壘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日月更替,天地交錯,所以才形之於文。文是與天地並生的。如果記憶可靠,沒有騙人,以前該是峰巒疊嶂,流川曲折,四時更替交織,真可謂各呈其色,各秀其態。而山的對岸,夜晚總見星燈錯落,珠玉遍灑。山體為夜幕所覆,隱而未見,而山路兩旁街燈,排列整齊,如一串勾勒出日間山體輪廓。這樣朦朦朧朧,反有另一番味道,這就是文織交錯!「東山可望,林泉生謝客之文;南國多才,江山助屈平之氣」。因文而生文,誠不吾欺。不過,這和當下的語境有關係嗎?此時此刻,此情此景,萬象俱收束在無邊永夜。上到山頂,他本來想慨嘆「天高地回,覺宇宙之無窮;興盡悲來,識盈虛之有數」,然而永夜漫無邊際,天地一黑,何嘗再見紋路?「校巴怎麼還未來?」陳成劍突然覺得不應該在這裡等校巴。可能不會來了。當然,我也回不去了。靠著記憶,陳成劍轉身摸索到圖書館後面的石碑,旁邊正是以前那座寒池。可惜他聽不到水聲,也看不到水光波紋,伸手觸之,池水早已經乾涸。在校兩年,難道真的沒有留下什麼紀念嗎?有的,有一首〈水龍吟.秋夜〉。詞作水平不怎麼樣。只不過既然寫在當日時空,重憶舊文,往昔歷歷,如在目前。他清了清喉嚨,並著詞與小序,獨自吟誦:
自本科修畢,旋入新校,兩年以來,學期倏忽,又復別去。無聊之日,課暇之間,多仗山頂書藏。後及收館之際,漫出路前,則夜色景致,每掀心懷。無語可記,殊惜光景空負;有言投筆,堪笑酸絮何益。惟見物聯類,因時感思,雖萬緒無方,亦雕蟲實懷。紙枉墨廢,權且寄調:
夜闌且聽跫鳴,燈昏莫照西風遠。港灣吐露,馬鞍馱影,寒池聲怨。曲水連天,頹雲墜地,秋華驚變。幻二年虛夢,樓成白玉,空聞詔,誰堪見。
遷客淹留舊事,笑才思,零篇殘卷。關河靜寂,未圓湖冷,塵飛車轉。路盡途窮,流泉低泣,帝鄉何願。念瑯嬛渺杳,蒼涯星落,遍山秋晚。
圖書館那邊傳來一陣玻璃碎裂的聲音,既聞動靜,陳成劍初而驚恐,後來又多了幾分好奇和興奮。他急急腳跑到圖書館門前,玻璃大門破開一洞,裡面太暗,目光無法穿透,亦無法逃離。陳成劍明白兩年學制,過得真是很快,所以無堂的日子,他總愛躲進小樓成一統。黃昏進去,夜晚出來。裡面的書沒來及讀完,畢業大限無情殺到,唯有中道而止。他長吁一口氣,無奈又被亂了心神。
正想離去,破口處,浮現一道紅光。陳成劍如趨光之蟲,目力再度為其牽引。借助月色,依稀可見,這是一道人影,更準確地說,是一道女子身影。更更更囉嗦地說,這是一個穿著紅衣,手持大紅燈籠,長髮垂肩又覆面的女子。陳成劍有些不解,明明光源微弱,何解她的衣服居然還是鮮紅欲滴?是燈籠的光嗎?還是衣服本身自帶發光物料?大紅燈籠高高掛?陳成劍心覺不妙,因爲這並不是一件好事。電影也是如此,那充滿節慶氣氛的燈籠,放置在一個鬼魅陰沉的天色之下,不是喜慶淡化了鬼魅,而是鬼魅消融了節慶。紅色喜事,反添加鬼氣。奇怪奇怪,怎麼會這樣呢?這種反差造成的美學效果,真的很有趣。他以前夢到一個小孩半夜出現在陰暗的走廊盡頭,那時也是可愛盡失,而別生詭異。陳成劍被思緒纏繞,一動不動。館內影子,卻開始漸漸移向他自己。每近一步,陳成劍就驚悚一分、興奮一分。好像早已中毒上癮,如癡如醉而又意欲遠離。你⋯⋯你真的要進來了嗎?影子沒有答他。提著燈籠,不知是飄還是走,總之漸往漸近,每行進一分,陳成劍的心跳就快一步。大約還剩兩三步距離,陳成劍左臉一疼,頭歪右邊。然後右臉又是一疼,反歪左邊。此刻天幕絮裂,如雪漫灑,大幅大幅地罩墜下來。陳成劍視覺盡失,天地一暗。
「醒啊!醒啊!」伴隨著聲聲嘶喊,陳成劍漸漸回來,日光刺眼又溫熱。整理好意識,正見劉承風在椅前不斷掌刮著他。如此來來回回,回回來來,重重覆覆,覆覆重重,先是刺痛生辣,繼而知覺呆滯,反應延遲。陳成劍捉住劉承風的手腕,說道:「撲你個街,吊你咩!」眼見陳成劍載譽歸來,劉承風覺得任務完成,也收手止刮。「還懂得醒來就好,幾驚刮你唔醒。」陳成劍一看牆上時鐘,不過下午一點,比他平時正常起身的時間,還差了兩個小時。「點解咁早叫醒我?定係叫刮醒我?童子軍跳彈床,咩事?」劉承風說:「咩事?快啲起身洗面,我幫你安排咗個interview,你執好自己,精精神神,唔好浪費機會啊」⋯⋯
黃昏,陳成劍見工回來。晚飯之間,劉承風問其結果。陳成劍答道:「那個HR,雖然問問題的時候總是一臉兇惡,不過她一定是裝出來的。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中途她問我拿學歷證書,語氣又變成客氣溫柔。其實,她那種兇惡態度很難場時間維持的,那樣會太過勞累,承受不起。不過佢嘅語速實在太快,根本聽不清楚細節詳情。」劉承風見陳成劍開始發病,仍嘗試拉他回來:「我是問你結果,見成見唔成,總有個答案。」陳成劍回道:「他們一開始叫我去春秋房。我沿路看到還有禮房、詩房,走廊盡頭又易房、書房。很奇怪。所以我問那個很惡的HR,她到底是今文經學派還是古文經學派,是尊周公還是尊孔子?我還主動建議,如果之後公司想擴建,不妨禮房一開三,分成周禮、儀禮、禮記。然後春秋房也可以一開三,變成左傳、公羊、穀梁。再加個孟子房、爾雅房、孝經房還有論語房等等,這樣公司就有十三經了。」劉承風嬲極而笑,說道:「陳生,你係咪有問題?讀中文系讀到你癲癲喪喪?難怪你一直失業耍智障,當初跟你一同畢業的人,個個都有自己的事業,只有你一個人過得特別差。有些時候,不要怪身邊人事,好好反思一下你自己吧。」陳成劍還在談見工的事,說道:「之後她叫我回去等消息,順便叫我練一下茴字的四種寫法。有趣,真有趣。」劉承風沒有再跟他糾纏,晚飯過後,劉承風一句話也不跟他講,整個房子只有街外雜音,靜得可怖。陳成劍倒沒有什麼特別感覺,反正他這個人比較毒,「冷戰」是沒有用的。
當晚,無所事事就是例行公事。陳成劍又要想辦法消耗如此長夜。因為「夜中不能寐」,所以「愁多知夜長」是正常的,而比較通用的方法就是夜讀,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彈琴。每次見工之後,無論結果,陳成劍總愛去逛一下書局。今次跟亦不例外。儘管長期失業,不敢胡亂添置新書,但日間他在書局看到一本《元白詩箋證稿》,觀其售價,居然不過67蚊。又要破戒了。怎麼總是忍不住手呢?購物是一種慾望,文學又何嘗不是一種慾望?他拿起新書,本打算一口氣讀完,但〈長恨歌〉一章沒讀幾個字,他的專注,很快就被窗外夜風吹散。涼意漸起,陳成劍方才驚覺2020年無端端就過了立秋。當初誰能料到,一年就這樣空廢過去。他放下新書,重新拿出魯迅小說全集。因為秋涼的日子,最適合食藥。尤其是「秋天的後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陽還沒有出,只剩下一片烏藍的天;除了夜遊的東西,什麽都睡著。」
戲臺上面,正上演著「秦瓊賣馬」的劇目。戲臺上面只有一個演員,戲臺下面只有一個觀眾。棚子不算大,只不過空排著那麼多長椅,回風流蕩,清冷如許。陳成劍對古典戲劇沒有多大研究,所以劇中唱詞,並未深究,而所演是何種戲劇,亦不甚清楚。但秦瓊的故事倒是略有聽聞。隋唐系列小說,一開始還是所謂的「按鑒演義」,即《隋唐兩朝志傳》之類敷演歷史事件。而明末袁于令的《隋史遺文》,亦即所謂由歷史演義到英雄傳奇的轉變。《遺文》之前,隋唐系列故事,還有一本《大唐秦王詞話》,昔日學生時代忽略了這個文本,不無可惜。到了清代《說唐》一出,則隋唐十八好漢,個個都幾近超級英雄。其神怪誇張的表現,於先前迥異,不過這本書好像也沒有顧及英雄之間的強弱平衡,一個李元霸,看上去就是前十七個人加起來也不夠他打。相比起來,排第二的宇文成都,倒是還勉強說得過去。雖然他也是一打三,但他是先跟排名四、五、六的雄闊海、伍雲召、伍天錫打完,然後才打輸排名第三的裴元慶,他看上去像個大BOSS,而李元霸就是個BUG,一個人打一百萬人,難怪夏志清說他是來顛覆戰爭小說的邏輯。順帶一提,《隋唐演義》前面部分,有不少抄錄自《隋史遺文》。至於今日改編隋唐故事的影視作品,有名之以「隋唐演義」,但實際上卻是《說唐》的故事。或許,《說唐》比較能夠刺激官感,而有「演義」之名因爲《三國演義》的關係,較為入耳吧。等等,剛才是不是去提到雄闊海?是那個壓死千斤閘的雄闊海?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怎麼又沒有食藥?陳成劍苦笑連連。
等到唱詞曲終,秦瓊演員呆立當場。陳成劍看到戲台後方,又是一道紅影。無需細想,她就是是上次那個女鬼。這次女鬼倒對陳成劍沒有意思,反而接近演員,伸出手臂,意圖觸摸。其手臂灰啞死白,指甲長度猶勝利爪。加上甲色油光通紅,遠看向是五把飲血匕首,懸在演員頸前。演員不聲不語,隔著面具,也無法看到表情變化。陳成劍覺得女鬼暫時不會騷擾自己,也樂得見死不救、袖手旁觀、置身事外。然而,此刻演員緩緩伸手摘下面具。面目揭曉的瞬間,陳成劍嚇得魂飛天外,椅子差點沒有坐穩。原來台上那個演員,面容憔悴,神色頹喪,分明就是陳成劍他自己。陳成劍望著陳成劍而陳成劍也望著陳成劍。女鬼的雙臂,如同兩條灰蛇,蠕動陳成劍全身。陳成劍驚恐之下,大喊一聲,戲棚為之一震。女鬼倒是不為所動,兩條灰蛇吐著五條蛇舌,漫舔著陳成劍胸腔近心臟位置,而陳成劍,幾乎無法動彈。如果這是一場夢,那麼如何醒來?陳成劍也不知哪裡併發的力氣,揮手奮力一拍,椅柄碎落數根。他拾起尾端略尖的碎木,對著大腿,咬牙插下。那一陣淒厲慘叫,戲台陷落,天地崩塌。陳成劍逃脫廢墟。醒時月明沒有星稀,烏雀不見南飛。夢遺歸來,沒有發現蟻穴和未熟的食物。
時間又白費了一個月。某晚,陳成劍正在修改舊稿。而劉承風推開房門,幫他端來宵夜以及啤酒。陳成劍移走稿紙,鋪上報紙,好讓宵夜安全著陸。「我記得,以前老母煮宵夜,一個出前一丁總配上四個菜,煎蛋、牛肉、青菜,還有已剝殼的蝦。」說完,他夾起一堆麵條,暴風吸入。劉承風笑說:「你都識講,那個是你阿媽」。陳成劍沒有理他,仍舊低頭,將一碗齋麵,吃得津津有味。一旁的劉承風,也有點懷疑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我想問一下,初雪輕寒是甚麼意思?照計,落雪就應該會好凍,你十度都怕到9縮,睇怕落雪你都應該會覺得世界末日。」劉承風無意見看到陳成劍的舊稿,不解他那句「初雪輕寒南國」。「起初是寫作初雪驚寒南國的,這樣就沒有理解的煩惱。但我真的很想寫初雪輕寒。正如你剛才所說,對我而言,或者對你而言,初雪未至,輕寒已遠。這是一場夢,所以夢境裡面,初雪輕寒。」說罷,陳成劍揚起那張稿紙,看其懸浮半空,再緩緩落來。稿紙上面,是一首〈臨江仙.夢雪〉:
初雪輕寒南國,銀妝無限江山。凍雲冷雨鬢眉殘。長流鋪白練,冰鏡照霜天。
莫見青絲催斷,鴻飛恨厭桑田。浮光易碎幻離煙。秋心多少事,夢覺莫新眠。
「對了,不瞞你說,我,過幾天要開工了,今晚會早睡,重新適應正常生活。」陳成劍說。劉承風老懷安慰,覺得他終於振作起來:「咦!恭喜恭喜。咩工?」陳成劍放下手中稿紙,說:「搬貨」。劉承風有點不太相信自己耳朵,「甚麼?」陳成劍開了罐啤酒,還沒喝下,見劉承風面露困惑,於是語氣平淡地重複一次:「搬貨」。劉承風有點欲言又止,這次倒是陳成劍比較多話講,:「搬貨幾好呀,起碼好過收銀。遇人太多,我會不習慣。搬貨比較少見人,搬完就收工,不用太多互動。而且這是正當職業,無分貴賤。只要靠自己努力賺來的,就值得驕傲。其實做運輸物流都唔錯,有經驗之後還有晉升機會,過幾年做到運輸主任,其實人工都幾和味」。陳成劍酒到唇邊卻又放下酒罐,笑着顯露準備開展事業的躊躇滿志。劉承風說道:「我當然認同。職業無分貴賤,賺錢多少,地位都是平等。行行出狀元,你之後事業有成,我都會替你開心。我明白、我明白。我說的不是這份工,而是你。如果你真的一開始就想去做物流,為什麼你要花六年時間讀中文系?其實你可以一早就開始你的事業,不用蹉跎這麼久。」劉承風說。陳成劍搖了搖手中啤酒,說道:「或許,這叫誤以往之不諫吧。」劉承風說;「你確定你沒有用錯字?」陳成劍說:「有點醉了,今天到此為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