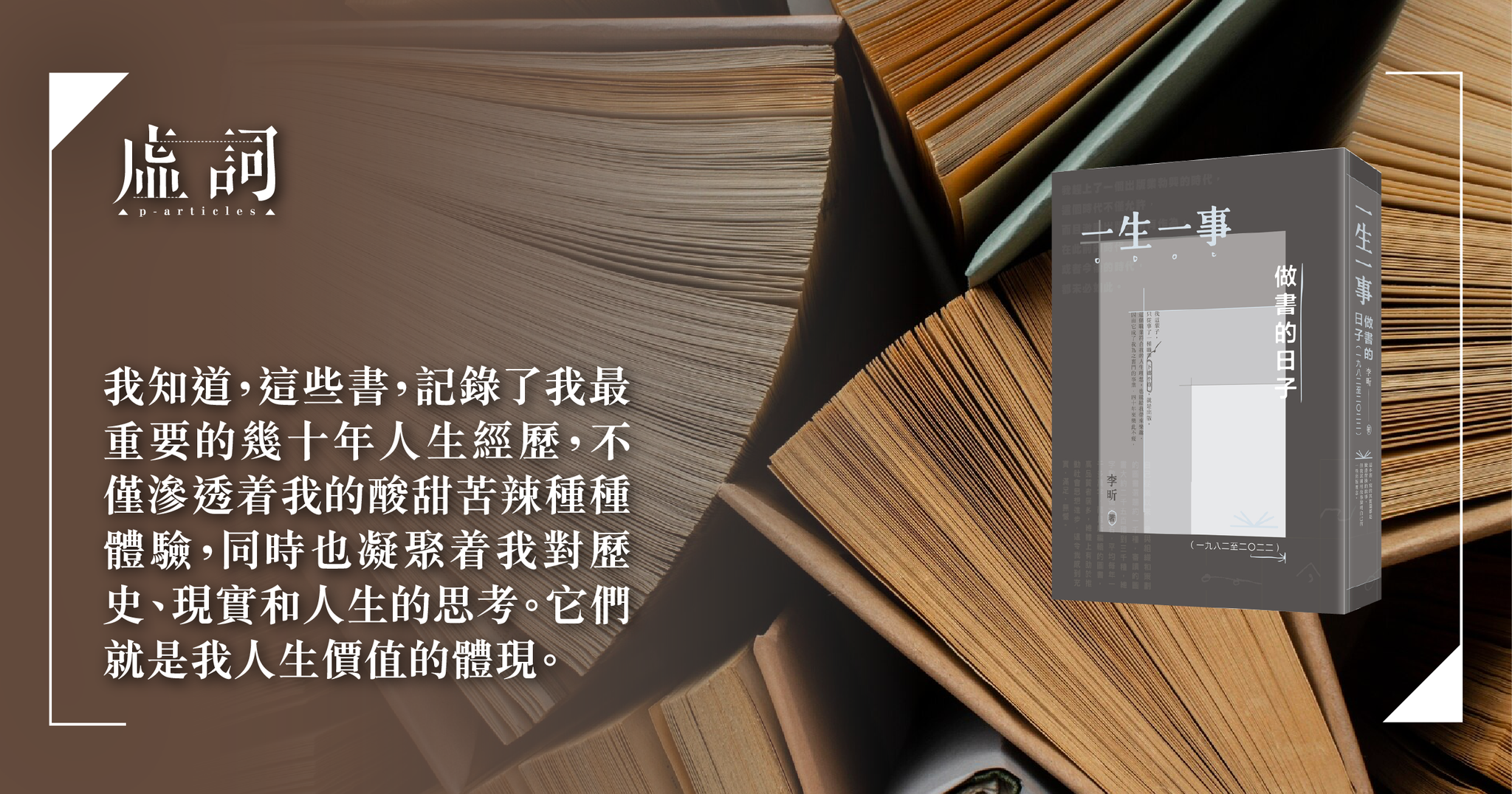【新書】《一生一事:做書的日子》後記
書序 | by 李昕 | 2023-11-06
這是我第二次動筆寫回憶錄。上一次,是在五年之前,我寫得非常簡短,只七萬多字,等於給自己的出版生涯列出了一個提綱。其內容大約相當於一篇長長的隨筆,所以我最初是準備將它編入我的一個隨筆集出版的。沒想到蒙深圳報業集團出版社的胡洪俠兄及汪小玲女士不棄,竟然把它當做一本小書單獨出版,書名叫《做書的日子:一九八二至二〇一四》。今天看來,那本書的確是過於簡略,許多重要的事情都沒有記錄下來。
當時我之所以動了寫回憶錄的念頭,還是因為受了老作家邵燕祥先生的啟發。我二〇一四年退休以後,陸陸續續寫了一些隨筆,講述三十多年「做書」背後的故事。文章完成後,我常常會寄給我特別尊敬的燕祥先生恭請指教。一次我到燕祥先生府上拜訪,他對我說:「讀你的文章,知道你經歷的事情不少。你應該系統地記錄下來。」我笑說:「寫回憶錄嗎?我還沒到年齡呀。」但燕祥先生卻說:「你可要抓緊呀。如果等你『到了年齡』,很多事就記不清楚啦。這事我是有教訓的。」他的話促使我寫了那本七萬字的小書。現在回想起來,我需要感謝燕祥先生。因為如果沒有那七萬字作為基本線索,這本厚度增加幾倍的新版回憶錄不可能順利完成。
當這本書完稿時,有人問我:「你寫這本書的目的是什麼?是總結自己,還是啟發同行?」我回答說:「可能兩者都有吧。」
從總結自己的角度說,我感到退休以後,自己的心態傾向於懷舊,主觀上也有寫回憶錄的動力。記得有一次,我為了重新編輯一本馮驥才先生十幾年前曾經出版的舊作,向大馮索取樣書,他在電話中嗔怪我說:「這書是你自己編的,怎麼會連樣書都不留?」他說:「我告訴你,你做了一輩子編輯,等到退休之後,最大的滿足就是欣賞自己編的書!你編過的書可要好好地收藏起來呀!」這些話,我當時聽了,並沒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今天,自己的確是像大馮說的,經常在「翻書憶往」,對着家中的幾組大書櫃發呆。我知道,這些書,記錄了我最重要的幾十年人生經歷,不僅滲透着我的酸甜苦辣種種體驗,同時也凝聚着我對歷史、現實和人生的思考。它們就是我人生價值的體現。我屬於曾經受過《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影響的那一代人,對於奧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虛度」的名言記憶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而今,在我編輯生涯告一段落的時候,我的確需要給自己走過的道路理一條線索,做一次盤點,進行一次至少是階段性的總結,也算是對自己的一次考試。當然,面對我曾經手(即以各種方式參與編輯出版過程)的三千本圖書,因其總體上已被社會、文化界和廣大讀者證明是有價值的好書,對於繁榮文化、傳播知識、促進社會思想啟蒙發揮了一點作用,我的自我考試是及格的。我感到自豪和滿足。儘管我一生沒當什麼官,沒發什麼財,沒成什麼名,我也仍然覺得,這輩子過得很值。特別是作為一個讀書人,我一生和自己喜愛的圖書作伴,從中不僅汲取了太多的營養,而且獲得了太多的樂趣。人們說,所謂幸福,就是快樂地生活。我無疑是一個幸福的人。
若說是啟發同行,我倒是不敢誇口說自己有什麼經驗可以介紹。在中國當代出版界,我屬於「生正逢時」的一代人,而且是其中特別幸運的少數人。我曾多次說過,做出版是需要有好平台的。而我先後在四家最著名的出版機構(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北京三聯和商務印書館)擔任編輯,享受到這些出版平台帶給我的特殊資源和特殊便利條件,時代和環境的雙重因素,使我有機會做成了一些別人或許難以做成的事情。所以我並不認為,那些所謂的「成功」就能給同行多少啟發。但是我的「不成功」、我的失誤也不算少,一些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事情,因為我個人的種種原因,而留下遺憾和懊悔。有朋友讀了我的書稿,說我這本書記錄自己內心的遺憾,可能比起表達欣慰和滿足還多些。我想,或許正是這些內容,可以幫忙同行們引以為戒。
今年是我從事編輯工作的第四十年,這本書是我四十年工作經歷的紀錄。它的視角當然是個人視角,我知道這自有其局限性。世人皆知,編輯總是需要與人合作的。好書通常不是一個編輯單打獨鬥的成果。一個好漢也需要三個人幫。我曾見到有老編輯寫回憶文章提及自己編了某某有影響的作品,因為沒有或較少提及他人在其中的貢獻而招致同事的非議,以致於引起朋友反目。我極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我身上,因為我一直對於幾十年來在各種情況下支持我的同事懷有感激之情。所以我在寫作時盡量注意,在一些有必要提及同事成績的時候,加入他們的名字。但是,由於這畢竟是一部個人回憶錄,受到敘述角度和文體的限制,我言及同事對於某書某事的貢獻,仍不可能詳盡敘說,有時只是寥寥數語,甚至一筆帶過。我希望這些同事可以從他們的角度,對我的回憶做出補充,這樣便可以對一些重要的場景進行立體還原。
這本書,寫的其實還都是做書背後的故事,但我試圖用故事說明自己的一些出版理念。這些理念是多位前輩出版人以言傳身教留給我的,對我一生影響至深。例如什麼是三聯傳統的精髓,我是從老一代出版家藍真先生身上讀懂的,而且終身受益。我在書中寫下了自己對於一些出版理念的固執和堅持,這或許並不能被所有同事和同行認同。我承認這應該也屬於見仁見智的範疇。但是,因為我的作品以記錄事實為目的,對於已經發生的一些爭議和分歧,我也並不迴避,而將它們留給後人評說。不過,所有這些都對事不對人,那些不得不講的故事,我盡力將文字收斂,以講事實為主,少做評論,盡可能保持客觀。在這本回憶錄中,我用了不少篇幅,來敘述我們是怎樣在「歷史的夾縫」中做出版的。出精品,出好書是我的一貫追求,這是我們以自己的出版物開啟民智、促進社會進步的途徑。為此一定要設法呈現作者富有學術文化價值的精神成果,但在當前環境下,同時又要避免違反出版政策和原則。我一直在實踐着老作家王鼎鈞先生贈給我的兩句話:「改變那不能接受的,接受那不能改變的。」我認為,無論遇到什麼困難,文化理想不可放棄,個人努力不可或缺。
當年的七萬字書稿完成後,需要一個序言。我想到了劉再復兄。再復兄與我交往三十多年,我們相知很深。但是他很忙,要讀的要寫的著作太多。我有些不忍打擾,猶豫再三後,才把稿子發過去。附言請他寫序,囑他「書稿不必細讀,序言不必寫長,美言不必多說」。然而他幾天後便回覆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說了不少令我愧不敢當的好話,使我感動不已。然而我更想說的是,讀者應能從這篇序言裏見出再復兄的為人和品格。在我結識的作家學者中,再復兄是一位永遠懷抱博大的仁愛之心的長者。他熱情、淳樸、善良,總是待人以誠,真情交友,內心常存感恩之念。所以他對我的那些美言,也可以看成是他對所有忠於職守的編輯們的讚賞和鼓勵。他喜歡和編輯交朋友,對於每一位曾經給予他一點微小支持的編輯,他都會心存感激。這些,讀者從他迄今出版了各種版本的著作一百二十多種,他仍然可以清楚地記起每本書責任編輯的姓名,就可以瞭解。我想起一九八五年我剛剛認識再復兄時,曾患一場大病,持續高燒一個月不退,在家休息,無法上班。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再復兄電話,他慰問我之後,告訴我他弟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需要內地買不到的外國藥品,可以讓他弟弟買了寄給我。我當時就流下熱淚,說感謝的話都泣不成聲。要知道,那時他已經是大名鼎鼎的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而我只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小編輯!再復兄就是這樣一位令人敬重的長者,有他為我作序,我感到深深的榮幸。因為五年前這篇序言的內容,主要是談他和我之間的交往,對於增補重寫後成書的《一生一事》仍然適用,所以本書仍然以此為序。
感謝香港三聯書店葉佩珠總經理和周建華總編輯對我作品的認可。兩年前我曾經在那裏出版過《那些年,那些人和書:一個出版人的人文景觀》,這次他們又欣然接納此書,令我極受鼓舞。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張軒誦先生,他細心檢查了全部史料,幫我匡正和彌補了一些錯漏。同時我也要感謝香港的持恆基金。這家基金是為紀念三聯老前輩藍真先生(和持恆學友)而創辦的,我的兩本書在香港出版,他們都在經濟上給以支持。香港三聯和持恆基金為我所做的一切,都讓我時時感受到三聯人的深情,讓我倍覺溫暖。
最後,我還想說,感謝我的家人對我選擇編輯作為終身職業的理解和支持,也感謝讀者多年來對我所編所寫圖書的厚愛。希望大家喜歡這本書。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