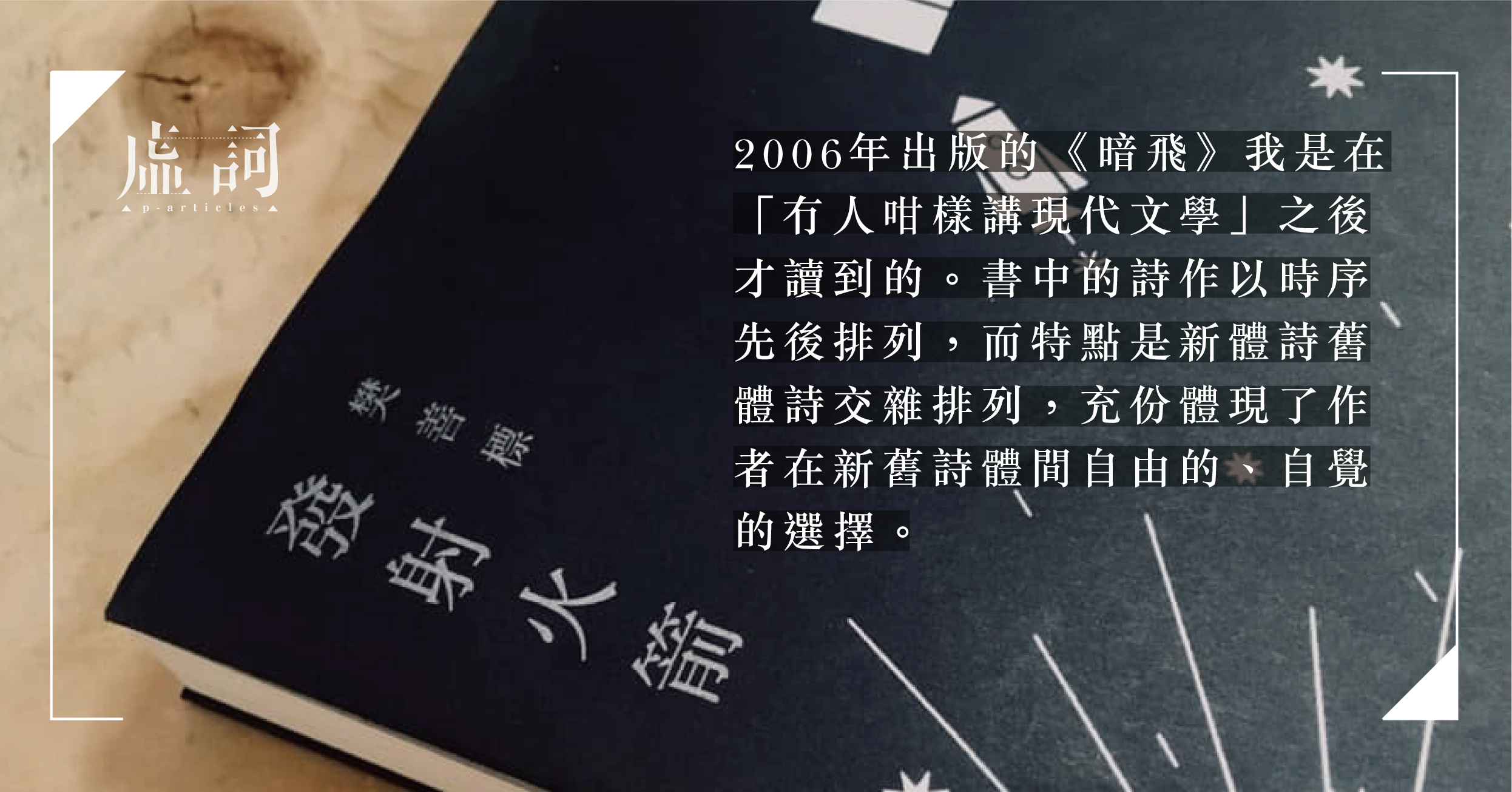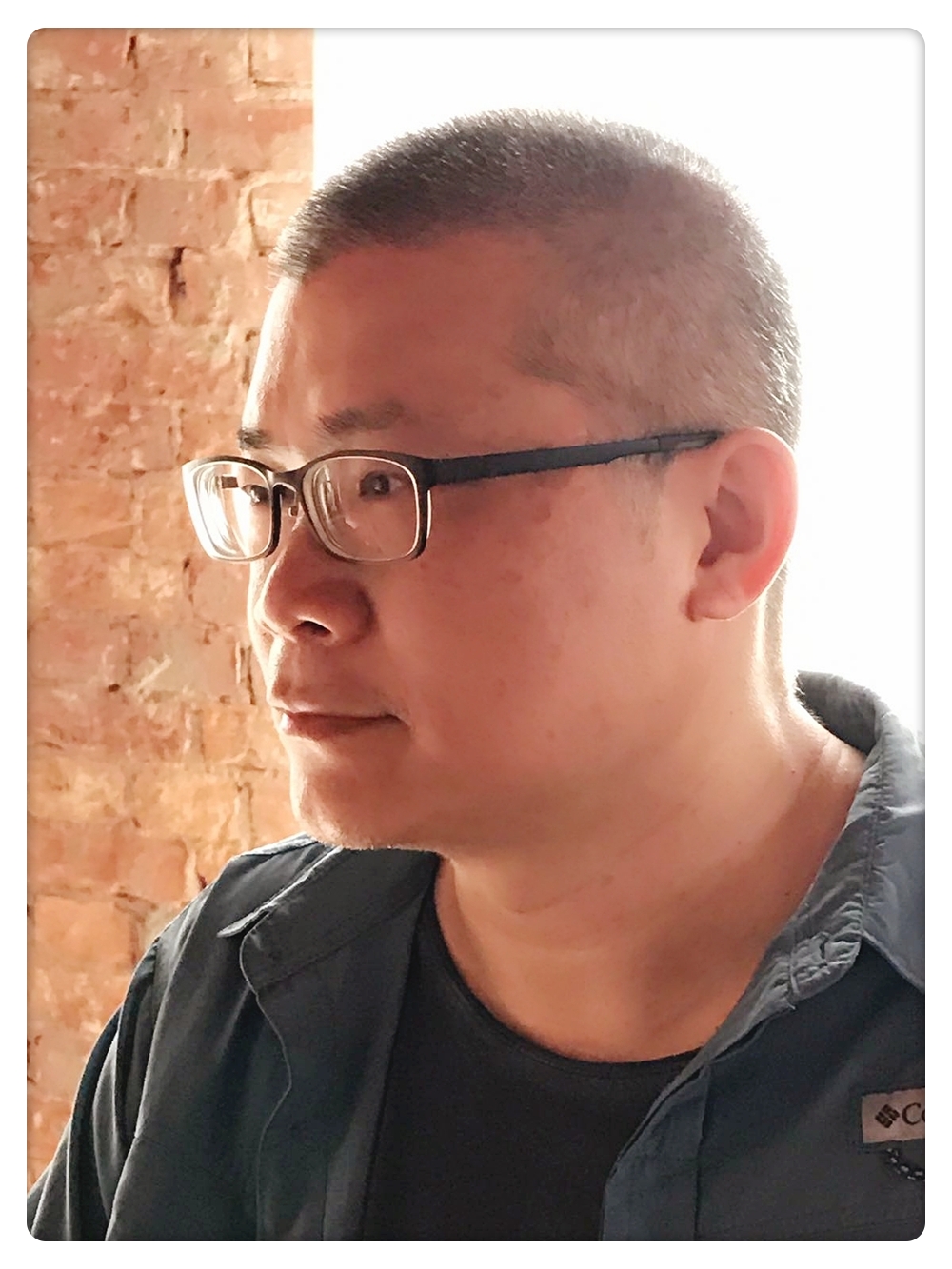跑野馬——從《暗飛》到《發射火箭》
好多年前我在〈樊善標暗飛到香港文學館〉說樊兄的《暗飛》「以創作成果重塑現當代詩歌真貌」,講的是事實。
還記得,當我第一次捧讀《暗飛》時,就好像遇上了知音,而且有點感動。「感動」的背景或原因不但曲折,而且相信也是很「個人」的:我大概在1998年開始攻讀博士學位,當時談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大都不談舊體部份,鄺健行老師卻指導我向這方面研究,認為可補學術空白,有意義。2002年我以論文「現代新詩人舊體詩研究」取得博士學位,當時做的結論其實一句簡單話就講完——現當代文學不等如新文學。而論文以詩歌為切入點,無非因為舊體詩在現當代仍然「不死」,而寫新詩的人又同時寫舊體詩,看似矛盾但又統一,是論證「現代文學不等如新文學」的上佳例子。今天再回看十多年前所做的結論,固然已是老掉牙的陳腔。近年出版的《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已為舊體文學開列了專卷,而各地研究者的觀念也有所改變,現當代舊體文學的專論,一天多似一天。回想2007年1月參加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我以〈林屋山民送米圖卷〉上現代作家的新舊兩體題詠為例,稍作論證,目的是要說明,現當代文學只包括新文學的觀念並不全面,也不符合客觀事實。研討會上兩位學者異口同聲提出反對,均認為現當代文學不應討論舊體,我連忙追問理由,而得到的回應是「冇人咁樣講現代文學嘅」及「對,沒這個講法」。
2006年出版的《暗飛》我是在「冇人咁樣講現代文學」之後才讀到的。書中的詩作以時序先後排列,而特點是新體詩舊體詩交雜排列,充份體現了作者在新舊詩體間自由的、自覺的選擇。〈約克和愛倫〉是新詩,〈荷塘漫作〉則用舊體,作者能按個別主題的特點、傾向與需要,選擇最適合的文學載體去表達。記憶中,金克木的《掛劍空壟》也是新舊體同刊的詩集。我常自恨不懂寫新詩,但樊兄新舊體既兼擅兼優又兼容,《暗飛》中的作品就是有血有肉的事實。自此但凡有人說現當文學只包括新文學,我會放棄重伸個人的論文觀點,而只會冷靜地請對方回去好好讀一遍《暗飛》。說到底,這其實就是「事實勝於雄辯」的道理。我花幾年時間做出來的結論,任何人都可以反對——反對得有沒有理由,已是另一回事。但《暗飛》所展示的是一種既成的事實,你可以故意忽略它或刻意繞過它,但不可能反對它,更不可能消滅它。我認為這是樊兄高明之處,而且一廂情願地認為他與我有著相同的文學觀,而《暗飛》正是暗中為我「助拳」、暗中為反對者製造「難題」的作品……主觀聯想作祟如此這般愈想愈逼真,因此而暗爽了好長的一段時間。
2015年中文大學辦文學夏令營,樊兄約我到校以「文學越界」為主題,為營友做點分享。記得到校那天,天氣大熱,樊兄專誠開車到火車站接我,我們還先到大學半山處的小餐廳喝咖啡談天。活動完了他又開車送我下山,管接管送,十分周到。那天我講的「越界」強調作者在「越界」前要先知道「界」在何處,對「越界」的成果反而談得不多,算是「保守派」立場。後來反思覺得如此分享可能違離了主辦單位的原意,講完之後好幾個月都不能原諒自己。至於第一次與樊兄合作,年份倒忘記了,依稀是在政府某圖書館的活動室談閱讀。我們各佔一半時間,各自發揮。他手持一本拿掉了封面的書向現場人士講故事,講到引人入勝之處,聽眾不停主動追問那是甚麼書,他才施施然套回封面:原來是「麥兜」。他在最新的散文集《發射火箭》中有一篇〈上課氣氛——自說自話的教授〉,自謂上課若論互動和歡樂,「膽敢說當仁不讓於師」——以我當年親身所見,確是事實。
「話不多,都靠心照」 《發射火箭》處處共鳴
《發射火箭》,重燃了當年讀《暗飛》的好些感覺,理性與感性上都得到無限支援,感覺上一點都不孤單。畢竟,我和樊兄共同關注的人和事特別多,讀他的文章,處處都起共鳴。他寫才女張紉詩、寫長洲宜亭;我在〈那一亭詩意〉也寫過這爿面海的小亭。80年代我大專剛畢業,有幸與風遠樓主李鴻烈先生共事,李先生給我講過若干女詩人的往事,好動聽。後來讀董橋的文章,知道他曾在宜樓讀書寫字,羨慕得不得了。一次有緣讀到張先生在便箋上題寫的〈苦蠅〉,書法好詩句好意境好,一讀就忘不了:「竹絲簾縫瀉秋光,纔伏詩魔返睡鄉。蠅似客愁揮不去,未成歸夢又斜陽。」連莊周的蝴蝶都要給比下去。張先生當年的未成歸夢,卻隱約補綴在樊兄的〈分寸感之再迷惑〉之中:樊兄說張先生曾在夢中跟他提及遺作《張紉詩詩集》卷四。低徊妖夢,不勝惘惘,我也曾做過類似的夢,與樊兄同樣是「一點都不覺得害怕」。2009年曼殊在夢中薄怨我把他的翻譯集出版計畫耽擱得太久,我一覺醒來知道必須盡快完成此事,同年即安排在北京出版了《曼殊外集》,總算了結一件心事。〈分寸感之再迷惑〉旁涉書生獵書傳奇的部份我讀得尤其起勁份外投入——「一時俊物走權家,容易歸他又叛他。開卷赫然皇二子,世間何事不曇花」——我在〈曇花雜錄〉也寫下了若干拍賣場上的書緣與軼事;有得,也有失。樊兄關注語文,〈語文人生活〉分章分節細論字詞用語;我也寫過〈咬文嚼字〉、〈瘋癲的文字〉及〈給偉大的校對工作者〉等討論語文問題的文章。在「關注語文」這回事上,我們都是「書生本色」,引經據典,以澄清文誤為己任:他說「慘緣少年」和「死飛仔」、「老泥妹」完全不是同一回事;我在〈「寄塵」都不是開玩笑的〉也說過:「慘綠少年」一旦成了尖東海旁「金毛阿飛」的代稱,就自然想不起那風度翩翩、意氣風發的青年才俊杜黃裳了。談寫作的文章我寫過〈談寫作的誠〉、〈發表與創作〉,成書者有《規矩與方圓》;樊兄是作家,當然也談寫作,長文〈與中學生談散文創作〉就廣涉寫人、寫景、說理、修辭等幾個重要範疇,寫得深入淺出、實用,實在無妨刪掉題目中「與中學生」四字。此外,樊兄喜歡把研究對象寫進散文,如張紉詩、十三妹;我也是同樣喜歡享受這一點點「反叛」,喜歡在研究與創作之間嘗試「越界」,所以我愛在散文中寫蘇曼殊、柳亞子、鄧爾雅,近年則愛寫唐滌生、十三郎。樊兄有一個「十三妹」,我有一個「十三郎」——這些別人看似是微不足道的穿鑿或巧合,卻足以令一個聯想力豐富的人明白甚麼是文學因緣。至於〈烏溪沙的海〉提及那道海濱長廊,我就住在附近。對,我曾在某個晚上,在這長廊上與樊兄迎面相遇。都是晚飯後散步的中年書生,又閒散又浪蕩:相遇,握手,問候,話不多,都靠心照;然後互道「保持聯絡」,萍聚,又雲散。
說「心照」不是信口胡謅的:2018年我與人合編散文合集《香港.人》,樊兄應邀為文集寫的〈(重畫)母親不肖像〉,我行使編輯特權得先睹之快。從文章知道樊老先生離世,樊老太的生活起了很大的變化。樊兄是兒子是局中人,又同時是作者是旁觀者,兩個身份把親情和心情都寫得異常真切又異常冷靜,此文業已重刊於他剛出版的散文集中。只是連日帶病看書,總提不起精神仔細核對《香港.人》與《發射火箭》所載的兩個文本到底有沒有不同,只好暫時擱下——讀樊兄的書,要細讀,只因他也細讀我的書。前此寄呈《艤舟集》請他指教,他讀後即給我電郵,提出書中案語兩處不恰當的地方,言之有理,令人佩服。2018年文學雜誌《字花》第47期改版,編輯黃怡小姐約稿,希望我能就散文的虛構元素寫一篇文章,我寫了〈虛構與撒謊〉,嘗試理清散文中虛構與撒謊的界線。卻原來編輯同時約了樊兄的稿,他在〈散文文類真實性之源〉中說:「如果現代的小說以虛構為再明顯不過的標誌,『本色』的散文最好反其道而行。」其實,樊兄的散文一向以來都非常「本色」,正因如此,多讀他的散文才會明白兩個中年書生在海濱長廊上「話不多,都靠心照」,是有可能,而且是有根據的。
只是不知何故,〈散文文類真實性之源〉並沒有收錄在《發射火箭》裡。這篇「集外」之文其實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樊兄的「散文觀」,據此再讀其散文,更易於心領神會。當然,作家對個人文集的安排心思,往往是出人意表的。比如樊兄說許迪鏘先生答允為《發射火箭》寫序,他因此就有了與伍淑賢小姐同等的待遇——箇中的類比關係真是又間接又風雅,完全是《世說新語》那個年代的思維。許先生亦不負所託,序文談創作的部份固然又詳盡又仔細又到位,偶涉二人交往的片段,亦別具情味。這也是許先生的真我表現。在2017年6月談論淮遠詩文的分享會上,許先生就不由分說,拿出一個又一個的瓷娃娃,放滿一桌,還笑嘻嘻地細說哪一個是淮遠送他的,又哪一個是自己最喜歡的。總之是報紙包報紙報紙包盒又盒中有盒,一層又一層,開完又開……像心事,更像遠年舊事……鄧小樺小姐當主持,氣定神閒,放乎中流任其所之,還不停叮囑他小心輕放,不要摔破。淮遠先生旁觀,微笑。
怕先入為主,許先生為《發射火箭》撰寫的序文我是讀畢全書才敢細看,作者的後記反而是偷步先看了。樊兄在後記說十幾年前出版的散文集《力學/[ ]》在書店給誤置於科學類,而新作《發射火箭》「亦有機會擠身實用科學或技術類」。其實,倘若把《香港官民關係》誤置於「武俠小說類」而能引起當政者或小市民一點點的反思,類似的錯誤分類,看來還是有其正面意義的。
(小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