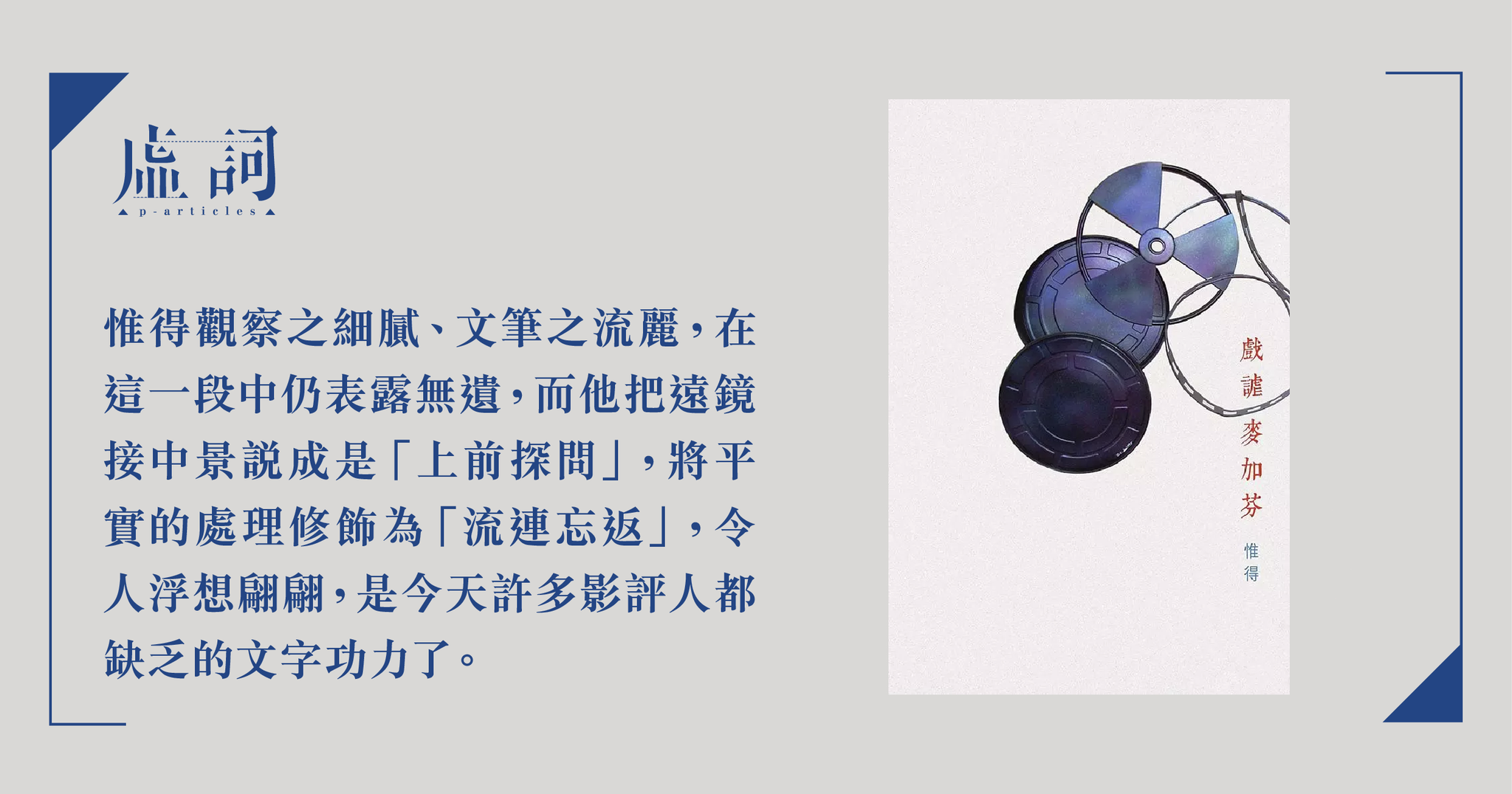讀「神來之筆」,聽「弦外之音」——評惟得《戲謔麥加芬》
影評 | by 陳廣隆 | 2023-08-18
惟得是本地七、八十年代活躍的散文及小說作者,也從事翻譯。原來他最初出現在文壇,據許迪鏘所言是在1974年於《中國學生周報》刊登的「隨筆式影評」[1]。這些影評篇幅不長,但對劇本的寫法、鏡頭的運用、導演的態度都有分析,觀察仔細,也透露了個人品味,後來他甚至準備投身佳藝電視當編劇,只因佳藝旋即結束而不成事 [2],可見他對電影的熱誠。不過,他也許對自己少壯時期的影評不甚滿意,因此這本影評集《戲謔麥加芬》三十八篇文章中,就只收有四篇八十年代的「舊作」,其餘皆是2004年至2016年的新輯。
李焯桃認為惟得文采和識見堪稱「文人影評」之佼佼者,既有傳統文人印象派散文式評論的風致,又不乏西方學院訓練的文學評論修為,能融合各種藝術的觸覺,寫出「寓抒情於評論的美文」[3],無疑是的評。惟得曾在圖書館任事,喜愛閱讀,《戲謔麥加芬》正能呈現作者廣泛的電影閱讀量。他最初的兩篇影評都與荷里活有關,但其觀影範圍自不限於美國影壇——從周詩祿、李晨風到凌子風、胡金銓再到許鞍華、陳坤厚,粵語片、國語片、港產片、台灣電影全都看得入迷;自費里尼(意大利)到杜魯福(法國)、小津安二郎(日本)到基阿魯斯達米(伊朗),再旁及拉烏盧易茲(智利)、曼勞迪奧利菲拉(葡萄牙)與佳麥甸(加拿大)等等導演,東西南北古今中外都有涉獵,從不偏食。
惟得不是只愛流連電影院而已,正如他說「一見鍾情之後,是深切了解的時刻」[4],起初囫圇吞棗地看戲,後來涉獵漸漸廣泛,多讀中外影評,擴闊眼界,但也不會輕易全盤接收,就如《戲謔麥加芬》有一章名為「雲仙和他的朋友」,收有四篇文章,專談導演吉士雲仙,但其實他自言「本來不是正宗雲仙迷,絮絮不休為他辯護,無非想說幾句公道話」[5],所謂公道話,是見《綜藝》(Variety)雜誌曾高捧雲仙的《迷幻牛郎》(Drugstore Cowboy,1989)真摯和獨創,卻又抨擊他的《象》(Elephant,2003)充滿陳腔濫調,惟得認為那是因為影評人「似乎有換上有色眼鏡觀影的嫌疑」[6],於是他縷述詳析《象》的劇情,並參考少有香港影評人提及的雲仙小說《粉紅》(Pink,1997)與他歷年的電影作品,再以亞歷山大蘇古洛夫、佛德烈懷斯曼等大師級導演的鏡頭比對,逐點反駁,非常用心。
惟得熟知不同導演的風格,不必引用甚麼電影理論,三言兩語就能講出其特色。例如他寫基阿魯斯達米「擅用長鏡頭,……我們忙著把他歸類,說是小津安二郎的信徒,適當的時候,其實他也信服艾森斯坦,……改用一組組蒙太奇」[7],相信他必定知道基阿魯斯達米年少時曾往德黑蘭的蘇聯領事館學習俄國蒙太奇理論的歷史。可是惟得分析鏡頭雖細,能說「公道話」,有時候對特別鍾情的作品始終較為寬容,如他愛看任劍輝的粵語戲曲片,評《釵頭鳳》(1957),寫到任劍輝被逼拜堂前的一段戲,就說蔣偉光珍惜其演技,「先是俯瞰鏡頭,唱了兩句,鏡頭接入齊膝中景,彷彿過路人驟聞淒婉歌聲,上前探問究竟。以後鏡頭便停駐不動,流連忘返地看著她把悲聲發放得淋漓盡致,直到最後幾句,任冰兒等著登場,鏡頭才緩緩流轉,依然愛不釋手地把任劍輝納入畫面左方」[8],似乎相當欣賞導演的調度能力。論《桃花仙子》(1958),又指蔣偉光「鏡頭靈活流轉」[9],令桃花仙景的歌舞場面更賞心悅目。可是相對於李晨風等同期的第一流導演,蔣偉光從來不以鏡頭與調度靈活見稱,上文兩處「流轉」,也不是十分複雜或暢滑的鏡頭運動,如「那緩緩流轉」,不過是簡單的推軌鏡頭,拉後兼右移,幅度數米維時數秒(任劍輝在期間續唱了兩句),用意不過是調整構圖,讓任冰兒自後方出場並使兩人平排在畫面,縱使簡潔有效,卻看不出有多匠心獨運。雖然如此,惟得觀察之細膩、文筆之流麗,在這一段中仍表露無遺,而他把遠鏡接中景說成是「上前探問」,將平實的處理修飾為「流連忘返」「愛不釋手」,令人浮想翩翩,可謂妙筆生花,是今天許多影評人都缺乏的文字功力了。
惟得的真正絕活是劇本賞析。例如他討論張愛玲撰寫的電影劇本《小兒女》(1963),就先比較《小兒女》與張愛玲早期小說《茉莉香片》(1943)、《金鎖記》(1943)、《桂花蒸——阿小悲秋》(1944)中的壞女人生母/後母形象的傳承,再以莫泊桑小說《羊脂球》(Boule de Suif,1880)、史丹堡電影《上海快車》(Shanghai Express,1932)、國語片朱石麟《花姑娘》(1951)、粵語片周詩祿《兒心碎母心》(1958)的「聖母光環」,反襯《小兒女》對自我犧牲的母愛的保留態度,說明幾個女角色都是「當聖母的淒楚」、「充滿內疚迷惘」、「始終難以自保」的人物,這才指出影片「說是喜劇收場,其實更似『哀矜而勿喜』」[10],可見他博覽與細讀的功夫。至於他以岸西編劇的《男人四十》(2002)與梅維爾自編自導的《里昂莫焉神父》(Léon Morin, Priest,1961)相提並論,也是少有前人提過的觀察——他比較兩片處理曖昧而犯禁的感情的懸疑性,指出「岸西和導演許鞍華合作賣關子,影片於是響起裊裊餘音。岸西盡得梅維爾的真傳,青出於藍」[11],乃是因為編導兩人能以分鏡與影機運動組織出更耐人尋味的情慾疑案,最後評定岸西比梅維爾「更添上神來之筆」[12],就令李焯桃「拍案叫絕」[13]。惟得敢謂岸西勝過「法國新浪潮教父」的手筆,無論是否認同,也實在是充滿自信的評論。
惟得善讀「神來之筆」,其實他更厲害的是能聽出「弦外之音」。這個「音」可以有三層意思。第一、惟得熟悉不同音樂,貝多芬、孟德遜、馬勒,如數家珍,而且涵蓋東與西,如早期廣東音樂《雨打芭蕉》和路易士.阿姆斯特朗《聖詹姆斯療養院》(St. James Infirmary Blues,1928),他都能聽出電影引用的源頭,可謂「耳聽八方」。除了辨認,還能鑒賞,如他分析陳韻文和湯浩柏導演如何分別在《CID:晨午暮夜》(1976)與《皇上無話兒》(The King's Speech,2010)巧妙運用貝多芬的樂章,論其異同,最後謂貝多芬這一樂章是音樂界的羅生門,「不同的聽眾可以有不同的感受,甚至同一聽眾,在生命另一階段,也可以衍生出不一樣的詮釋,或者這就是不同凡響的定義」[14],為讀者上了一門接受美學入門課。
第二、惟得不單留意音樂,更留神不同聲音。例如他評論《瘋劫》(1979),一開首就說「真多電話場面,還未有手機的年代,已經預言人對社交網絡的瘋狂」[15],指出片中多次以電話鈴聲勾魂奪魄。談《七女性︰汪明荃》(1976),則以汪明荃的呼喚、尖叫,于洋的獨白與唸書聲,欣賞陳韻文寫人物之層次豐富。[16] 論《北斗星︰阿詩》(1976)更仔細地聽到「編劇陳韻文更安排她的對白越來越簡短,寥寥數句,都沒有尾音」[17],藉以寫出角色可悲的疑畏與退縮。連沒有尾音都聽得清清楚楚,難怪他可〈捉《家》《春》《秋》的字蝨〉[18],從三部電影唱的歌曲與唸的舊詩文,批評「中聯的創業作在新詩一欄吃了零蛋」,幸而「其後的製作方針倒在世界名著一欄得到了滿分」[19]。不過,惟得也偶有手民之誤,同篇中他說明《家》刻意讓克明拋書包時弄錯張九齡與張公藝的典故,就將「張公藝」聽/寫成「張公毅」了。[20]
第三、惟得看電影非只為消遣,對政治、民風、教化也有自己的立場和態度。他寫《李後主》(1968),主題是任劍輝的演技,也不忘從「小樓昨夜又東風」和「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兩句提到「這個『東』字輾轉流落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更使人心驚肉跳,……一首感懷身世的詞,為一個時代的政治氣候作註腳,是否李晨風的弦外之音?」[21]談胡金銓,則認為外國影評人析述未周︰「烏亞提起胡金銓當初拍《大醉俠》,正值越戰升級,文化大革命席捲中國,胡金銓往古中國取經,迴避敏感的政治題材。烏亞倒沒聽到《大醉俠》的弦外之音,胡金銓仿傚影片的醉貓裝瘋賣傻,然而心想為民除害卻又難忘恩義的複雜心態,豈容『明哲保身』四字抹殺」。[22] 這些評論都可看到惟得自己的「弦外之音」。
惟得行文溫柔敦厚,觀影雖然不嫌血腥,例如他對吉士雲仙借少年校園殺手故事拍出人性之惡與生命之脆弱的《象》甚為欣賞,但總的來說應不傾向粗野暴力的作品。如他認為史高西斯《華爾街狼人》(The Wolf of Wall Street,2013)「借連珠的粗言穢語諂媚觀眾,說是諷刺搶錢一族,潛意識更像嚮往他們的糜爛生涯」[23],他沒有提出更深入的剖析,也沒說明為何這是「諂媚」,但他似乎忘了史高西斯歷來就善於以市井俚語、粗言穢語寫出角色的暴躁、張狂、執迷,與及街頭秩序的怒火和險惡,不是突然戀上了糜爛。記得李歐梵也曾認為晚期的史高西斯「江郎才盡」、「導演功力不足」[24],筆者並不認同[25],但惟得對道德教化的關注,依然令人尊重。惟得愛用「慈航普渡」一詞,[26]喜平實溫厚,反誇張煽情,未必鄙視官能刺激,也非只重高雅藝術,也許《戲謔麥加芬》沒收入惟得少壯時評論荷里活通俗片的文字,也少談及新近的商業娛樂片,才予人偏向「溫柔敦厚」、「義正詞嚴」、「文人影評」、「細密美文」的感覺。筆者期待惟得再結集影評文字,專談真正的麥加芬手法——希治閣不就是最雅俗共賞的大師嗎?
註:
- 見許迪鏘在惟得小說集《請坐》所寫的〈鞠一個躬——《請坐》序〉。惟得著︰《請坐》,香港,素葉出版社,2014年,頁vi-vii。
- 見許迪鏘在《戲謔麥加芬》所寫的序〈誰是麥加芬〉。惟得著︰《誰是麥加芬》,香港,文化工房,2017年,頁xviii。
- 見李焯桃為此書寫的序。同註2,頁vii-xi。
- 見〈維也納輕吻胡金銓〉,同註2,頁69。
- 見〈借校園描暴力〉,同註2,頁166-167。
- 同上,頁161。
- 見〈齒頰櫻桃〉,同註2,頁154-155。
- 見〈任風弄月劍生輝〉,同註2,頁5。
- 同上,頁12。
- 見〈危樓夢魘——探討《小兒女》與《一曲難忘》角色內心的曲折〉,同註2,頁55。
- 同註9,頁74。
- 同上。
- 同註3,頁x-xi。
- 見〈貝多芬的羅生門〉,同註2,頁132。
- 見〈《瘋劫》的餘韻〉,同註2,頁105。
- 見〈兩個人的心居〉,同註2,頁108-111。
- 見〈阿詩的手指〉,同註2,頁113。
- 同註2,頁29-39。
- 同上,頁39。
- 同上,頁32。
- 同註12,頁19。
- 同註4,頁69。
- 同註12,頁136。
- 見〈神鬼無光——馬田史高西斯憑什麼獲獎?〉,收入李歐梵著︰《人文文本》,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9年,頁181。
- 筆者較認同家明這篇影評的說法︰他謂史高西斯「永遠是說故事的大師傅,他的能量沒隨年紀衰減,作品愈來愈起勁。《華爾街》同時叫人目定口呆,史高西斯這麼多年,電影揭人性及社會陰暗不少,世界從沒像《華爾街》爛得那麼透徹」。見家明〈《華爾街狼人》金錢萬歲!〉,《明報》2014年2月16日。
- 同註2,頁49、5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