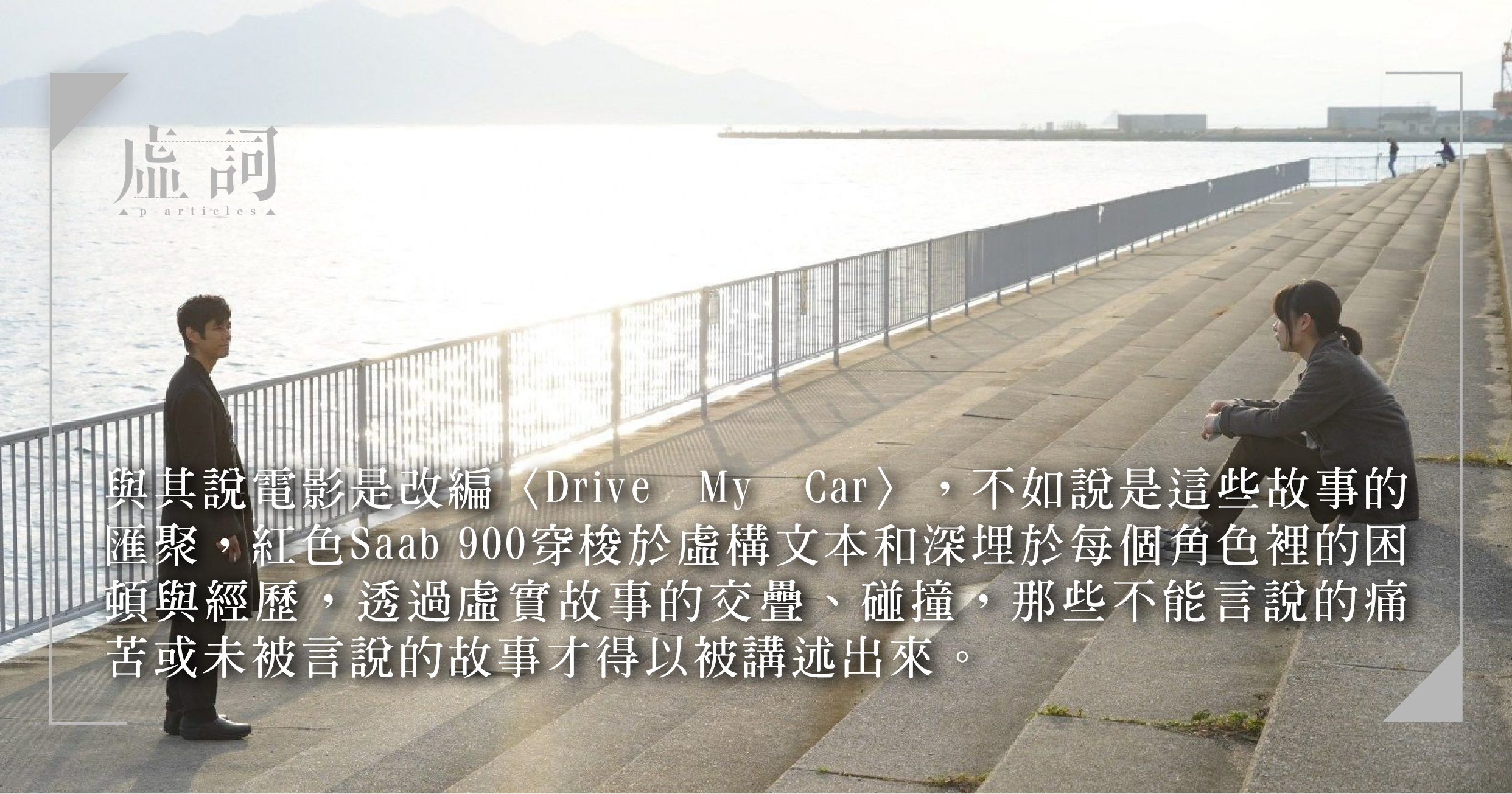比性愛更能讓彼此靠近的──濱口龍介《Drive My Car》
電影是這樣開始的:日照下,床上有一對夫妻,他們裸著身體,一種親密的標誌;然後是shot reverse shot的剪接效果,我們看到躺在床上被日光照得清清楚楚的丈夫家福,以及在逆光鏡頭裡只剩下陰影與輪廓的妻子音。妻子正跟丈夫講述一個故事,一個女高中生偷偷潛入暗戀對象的家裡,留下信物但未有在他床上自慰的故事。可以潛入別人家裡但不可以自慰,是因為電視尺度嗎?丈夫問。因為她知道有可以做和不可以做的事,妻子答。
故事未完,妻子卻早一步過身。在懸念中,電影的故事才真正開始,關於一個失去女人的男人,一個未被講完的故事。
讀過村上春樹的原著小說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會知道女高中生的故事其實是另一篇小說〈雪哈拉莎德〉裡的情節。濱口龍介的電影以〈Drive My Car〉為核心,又穿插著同一本書裡的〈雪哈拉莎德〉和〈木野〉,以至俄國劇作家契訶夫的《凡尼亞舅舅》,幾個故事看似互不相關,卻在電影角色的層面上起了情感的互文作用。與其說電影是改編〈Drive My Car〉,不如說是這些故事的匯聚,紅色Saab 900穿梭於虛構文本和深埋於每個角色裡的困頓與經歷,透過虛實故事的交疊、碰撞,那些不能言說的痛苦或未被言說的故事才得以被講述出來。
可以說,故事或說故事本身,才是電影《Drive My Car》的真正主角。
情色的背面
情色,不是porn,而是erotic。「情色與單純性行為的區分在於其獨立於傳宗接代本能之外的心理探索。」[1] 巴塔耶在《情色論》的前言裡如此形容。
某程度上,這種情色或曰心理探索,是電影《Drive My Car》的一個起點。性生活是家福和妻子音的生活核心,因為在做愛的過程中,妻子會開始講述一些故事(這也是〈雪哈拉莎德〉的情節),然後她會忘記,而家福的責任就是把這些故事記住,在另一天將其重述出來。我們可以想像這個「講述故事-重述故事」的過程是兩人之間的一個微妙平衡,彷彿兩人可以藉此觸碰到彼此內裡,而不僅僅是性愛中的肉體愉悅。透過故事建立起來的內在關係,說起來正正是電影的戲劇主線。
後來我們會知道,這個習慣其實是在兩人喪女之後才出現的,帶有一種創傷後遺的況味。而且,妻子不只跟家福之間有性關係,她跟不少飾演她的劇本的男演員都有所謂的婚外情,他們或者都知道音在做愛時會講述的那些故事。但終究沒有一個人可以真正明瞭她的動機和感受。故事中前生是吸啜著石頭的八目鰻的女高中生彷彿有她的重影(吸啜石頭這個意象本身不也是非常明顯的情愛象徵嗎?一種近乎孤絕的愛。),然而在所謂情色的終點,卻只有更多的不解,彼此沒有靠近多一步。不只故事未被講述完畢,就算已被講述和重述的部分,都只帶來更多的謎團。
在探討情色的主題上,文藝作品跟一般為了感官刺激而創作的色情作品的分別,往往在於前者較常探索情色的不可能性。看似標誌著極致親密、水乳交融的性愛,到頭來就如電影的開頭一樣,只能看見另一個人的陰影與輪廓,更甚變成生死相隔。卡梅.答悟得在《吞吃女人的畫家》裡形容得貼切:「性是薜西弗斯真正的石頭。」[2] 如果缺乏一種真正的連結,再親密的身體接觸,都不能拉近那道不容僭越、名為他者的界線。
言語的重量
綜觀濱口龍介的電影,有一種東西比起性愛更能讓人彼此靠近,那就是言語。或者倒轉來說,除了言語,別無他法。
舉例來說,前作《偶然與想像》的第一個故事〈魔法〉,兩個女子在車上談到一種沒有dirty talk、沒有身體接觸卻可以觸及彼此內裡的對話,不知道自己偶遇閨蜜前男友的芽衣子坦言「沒想過聊天竟然可以如此情色(erotic)」;又譬如第二個故事〈門常開〉,真正讓奈緒與教授作家靠近的不是她的色誘或文學上的性愛描寫,而是教授告訴她,不要因為別人的看法而改變自己,一句觸及她內裡困惑的說話。那到底不是一種身體上的裸露,而是內在自我向他人裸露,而後者相比前者更為赤裸。
《Drive My Car》明顯承接了這個觀點。無論是電影裡面的虛構文本(《凡尼亞舅舅》和妻子音的口述故事),抑或深埋在每個角色裡的創傷和經歷(而這些經歷又時而跟虛構文本重疊在一起),最終都需要透過言語的形式表達出來,唯有說出口的話方能讓彼此溝通,彼此靠近。然而,《Drive My Car》跟前作不同之處,在於創傷這個新的角度。熟悉創傷後遺的都知道,任何創傷和受苦經驗都是人們無法輕易說出口的事情,創傷是一種失去、一種缺席,受苦是生活在理所當然的彼岸,是人被拋擲到世上如此不由自主的荒謬。即使當事人嘗試說出口,或都需要一個婉轉的方法以圖迴避直接觸及深埋在記憶裡的創傷經歷,免得身體再次遭到創傷的襲擊。
創傷這個故事角度,為電影額外增添了一個言語的意義得被轉譯出來的維度。在創傷的巨大陰影下,《Drive My Car》要講述的恰好是直接交流的相反,各種無法對自己或對他人坦誠的生存狀態。就像家福雖然有能力記住妻子在做愛時講述出來的故事,卻無法解讀箇中含意,亦無法面對自己在妻子外遇這事情上的複雜感受。電影裡,言語再不是那種情色的溫柔接觸和互相撫慰,而是背負著言語背後那些無法輕易表達出來的龐大黑洞,人與言語以至自我之間的距離,或一種哀痛之難。
在戲劇裡相遇,在戲劇裡溝通
電影《Drive My Car》對於言語的省思與解答,最明顯的部分當屬家福的跨國語言劇場作品,以及啞女演員允兒。兩者在電影裡的作用,似乎都是有意表達言語本身並非一種純粹的工具,而是一個需要時刻更新、彼此碰撞才能走過的過程。
家福的跨國語言劇場作品,本身就是刻意強化言語與言語之間的距離的一次操演。透過由不同國家、操不同語言的演員飾演劇作裡的角色,然後一次又一次刻意放慢的圍讀劇本環節,這個過程本身不全然是為了讓演員聽懂對方說出口的言語所要表達的意思(如果只需懂得字面的意思,看文字翻譯就夠了),而是留意在這些「意思」周圍,構成「言說」這個行為的各種細節。允兒在這個演練過程裡的參與,自然是最具象徵意義的部分,就像她後來在餐桌上跟家福說,一個患啞的人早早習慣別人無法明白自己,必須通過言語之外的元素來觀察和溝通的生活。於此,所謂言語就不限於其字面意義,而是一種通過肉身的在場來完成的表達行為。
或者也可以說,不斷的圍讀和排演,也即是家福必須通過在車上反覆唸讀以熟悉劇本的這個習慣,本身即是一個放緩到極致的理解過程。其目的其實不在於熟讀劇本,而是像後來家福自己所說,讓劇本牽引出演員的內在自我,通過這種沉浸般的理解,讓角色從演員的內裡孕育出來。換句話說,真正在舞台上交流的不(只)是演員的戲劇表演,而是他們彼此內裡的經歷、情感和故事所牽引出來的,通過角色傳遞的真實;某程度上,戲劇角色乃至劇本自身都只是一個容器,人通過自我經歷與虛構文本的重疊所呼喚出來的共鳴,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這些對言語的省思與解答,便是濱口龍介通過電影《Drive My Car》所要傳遞出來的,如何在創傷裡互相理解的方法學。與其說電影裡的角色是通過言語來溝通,不如說他們是通過故事來溝通。因為創傷使人無法直接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人們就通過或虛或實的一個個文本和故事,把自己表達出來。而這種表達方式的核心,除了需要對文本有所認識之外,還需要有打開自己的勇氣,在溝通和理解之前先觸碰自己內裡的幽暗,先抵達自己才能抵達別人的心──這正正是家福在重述妻子講述的故事時所欠缺的元素,一種更根本的內在連結,透過交換透徹的心來完成的溝通。因為他沒法面對得悉妻子外遇帶給他的苦困,表面的穩定卻最終換成兩人之間的隔音玻璃。
故事接力,和「誤讀」的必要
濱口龍介對於不同故事和角色背景的挪用與併貼,蠻符合班雅明在文章〈譯者的任務〉裡提到的,翻譯作品對原著的存續和開展;重點往往不在轉譯後的文本在多大程度上把原著搬字過紙,而是如何通過語言的更新,把原著的生命乃至語言本身延伸下去。「翻譯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再為了原著文本而存在,而單單為了語言而存在。」[3] 班雅明在文章裡說。
我們甚至可以說,電影《Drive My Car》本身就是一個後設地把這個轉譯過程搬演出來的示範。這一方面是指電影對小說原著乃至《凡尼亞舅舅》劇本的改編和挪用(甚至可以說是騎劫),另一方面也是指電影角色如何重述和轉述另一個角色的說話,而在語言的運用中,必然存在一個過程,或一個他者的存在;說話不是為了結束對話,而是為了彰顯溝通必須是一個困難的過程,但往往在這趟或者沒有終點的旅途中,人才真正懂得互相傾聽、互相了解,這才活出了言語的生命力。如此我們又回到行車之旅的象徵意義裡,真正讓故事和對話發生的不是旅程的起點或終點,而是那個過程。
而未完的故事,或已逝之人的故事,又有沒有講下去的可能?在《Drive My Car》的中後段,高槻在車上跟家福談起音的那個女高中生的故事,甚至講出了家福所不知道的後續發展。其實我們沒辦法證實高槻所說的是否真實,那都可能是他杜撰出來的,但就如美沙紀所說,至少他說出了他所相信的真實──那是一種基於罪疚、渴望被別人發現的真實。故事的延續,在於那一刻高槻體會到音從前的感受,他突然明白了;那可能是一種「誤讀」,但又是一種基於情感共鳴,在別人的故事裡辨認出自己的感受的,必要的「誤讀」。或者也可以說,所有故事本身都是未完的故事,只有藉由來者一次又一次的閱讀誤讀,它的生命力才得以再被喚起,重新確立一種故事的互動關係。
電影結尾,美沙紀駕駛象徵家福的故事的紅色Saab 900再次開上公路,一個旅程的結束又是另一個旅程的開始。《凡尼亞舅舅》裡由桑妮亞唸出的對白:「我們要繼續活下去。」也是所有故事的最後一個互文。曾經坦誠相對,然後各自上路,一直走完各自的人生。班雅明又在〈譯者的任務〉裡說:「在這種純粹語言裡,所有的訊息、意圖和含意,最終都會在同一個層面相遇,而且注定要逐漸消失。」[4] 大概沒有比這句更情色的句子了。
[1] 賴守正譯,喬治.巴代伊(Georges Bataille)著:《情色論》。新北市:聯經出版,2012年。頁67。
[2] 陳文瑤譯,卡梅.答悟得(Kamel Daoud)著:《吞吃女人的畫家》。高雄市:無境文化,2019年。頁147。
[3] 莊仲黎譯,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著:〈譯者的任務〉,《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班雅明精選集》。台北:商周出版,2019年。頁211。
[4] 同上。頁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