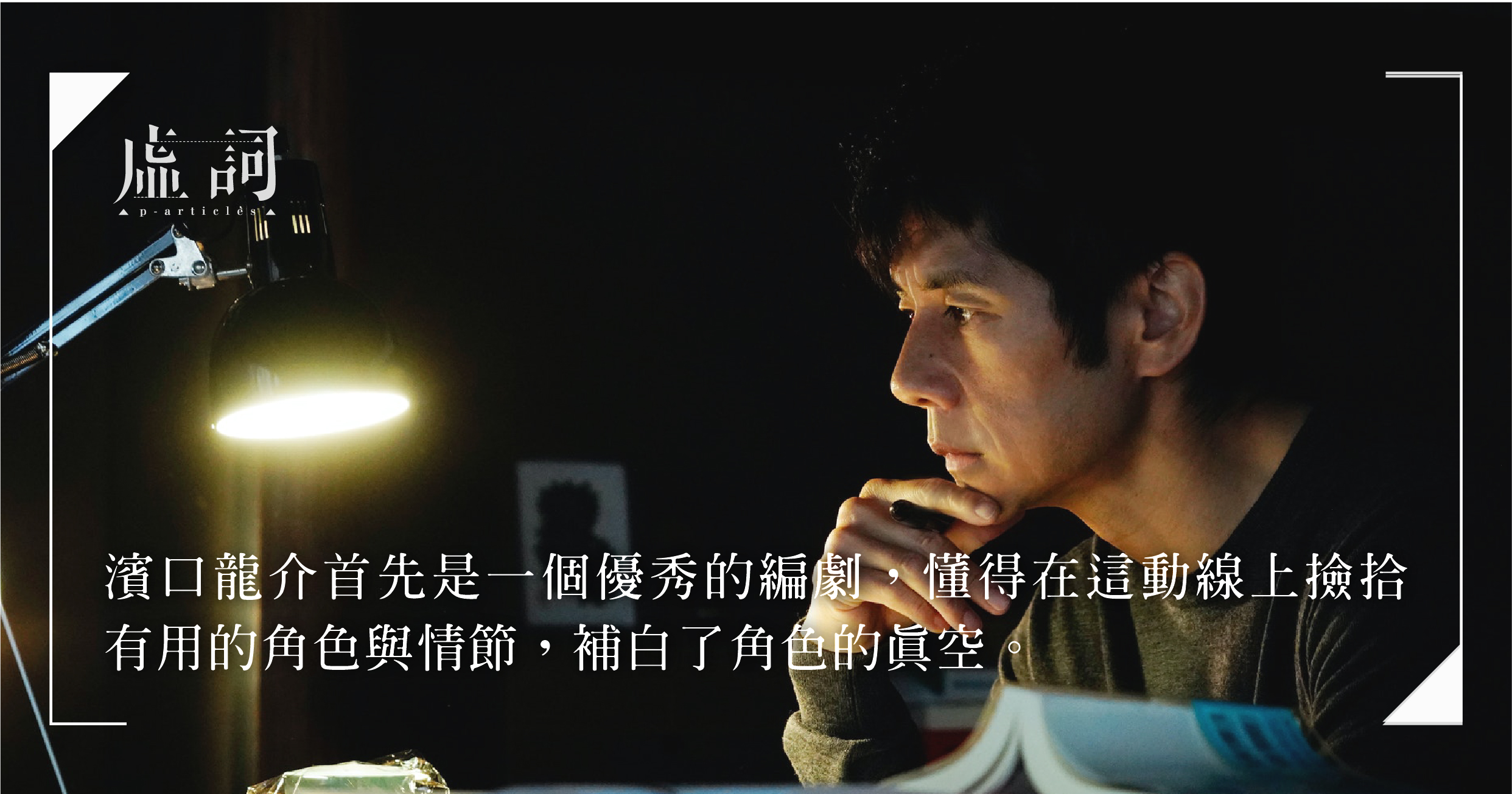或在聽風的歌——靜讀電影版《Drive My Car》
影評 | by 化蛤堂的寒露 | 2022-03-29
村上春樹小說的改編電影,應該有些甚麼?入坐之前一直在想這件事。它必須要有一個瀟湘精瘦的男主角,一個人跟世間格格不入;彷彿一切如常的城市,入夜後陌然掛上異色。天氣通常很冷,那樣人與人的隔膜會明顯一些; 如果暖的話,大概會去看海,這是《聽風的歌》以來的調調。最少得去酒吧的吧枱前坐坐,視付年紀給角色喝喝啤酒或威士忌,然後一幕幕播著文本列好了的歌單。
把這些統統拍出來的話,怎麼說都比較像《重慶森林》。
問怎樣才是最好的文本改編電影,或者有生之年都不會得到答案。而文本改編而成的經典音樂,卻早有公論。好在柳應廷和YOASOBI或多或少都有在大家的Playlist佔一席位,翻鬆了這一片的土壤。
舒伯特公認最懂得改編歌德的詩。葛麗卿一個人在屋裡心如鹿撞,記掛著喝了魔法藥水而變得年青俊朗的浮士德。李斯特和華格納都寫《浮士德》,李斯特的葛麗卿心跳如躍動於琴鍵,華格納的絢爛時高潮迭起。但舒伯特只寫了三個聲部,高音部留給女聲演唱,另外兩部用鋼琴譜寫紡車的腳踏聲和紗線一圈圈輪轉的聲音。紗線的轉動隨著小女的心情或高或低,直到她想起那偷偷一吻,紡車驟然停轉。文本裡面其實沒有半句提及,紡車的動靜。然而舒伯特這一筆到底是補足,抑或是添足,毋庸置疑。
濱口龍介導演下的《Drive My Car》並沒有帶給大家那預想中的歌單,縱使村上老爺分明點唱了一堆中古的美國搖滾,Beach Boys、Rascals、Creedance Clearwater Revive(CCR)、Temptation。也正因為這歌單,加上對駕駛手動排檔汽車的碎碎唸,讓讀者認定這男主角是村上春樹本人的化身。只是濱口龍介並沒有讓《Drive My Car》拍成一齣這樣的電影,他讓一般觀眾都期望插播音樂空間都留白。因為家福需要這種沉默,這也是家福和美沙紀的必要的溝通方式。但這種沉默並不是無聲,不論是穿梭大橋還是走在小島的彎路,引擎轉子的伴奏一直流暢而平滑。
馬力高的歐洲中古車,保養良好手動排檔,神秘而駕駛利索的女性司機。
手動排檔的汽車運轉起來到底怎樣?如今幾乎是電動車的世界了,或者大家都不在意。有機會叫貨車的話,可以留意一下,那動靜大得不容易忽視過去。離合器鬆開,齒輪失速變調,波桿咔喳地搖到下一檔,離合器重新咬合,引擎的轉動一下子又快了上去。重複。主角家福的耳朵敏銳又敏感,即便只是換了一套新的雨刷,他都能抱怨摩擦的聲音太過堅硬。所以他不能信任其他人的駕駛,尤其是舉措不定的司機,而這種又以女性為多。村上春樹不介意寫這種赤裸的偏見,他深信一個人跟一個人之間就是有種隔膜或者偏見或見不解,是源於比價值觀道德觀更底層的地方,比如話生理上的反應,像吃榴連、芫荽、臭豆腐、Sauvignon Blanc或者獵奇的性愛。區隔著我們的是卡夫卡式的、命定的、無解的疏離,或者正因如此我們的男主角必須再一次叫卡夫卡(家福/Kafuku)。
聰明的導演會知道,改編的電影和村上春樹的小說本身是兩件事。小說讀者一般都有健康的社交距離,不像電影的觀眾一兩百人一齊看同一段戲,聽同一句話。如果原原本本讓家福在鏡頭前獨白自己對女人駕駛的偏見,即使是西島秀俊恐怕都招架不住。村上的小說世界,是以他的作品為總和的延長線,作者總是一而再再而三去暗示,男人和女人,作者和讀者,中間不過都是理解和被理解的比喻。沒有女人的男人們,in short,可以是沒有讀者的作者,也可以是沒被理解的人們。而人類大半的後悔與遺憾,在村上而言,或許都跟這種「理解落差」息息相關。
村上春樹寫作的動線有相當的連貫性,不同故事的角色之間,總是有不能言喻的相似。讀完《Drive My Car》去讀《刺殺騎士團長》的話,你會隱隱覺得主角畫家的老友雨田會有一幕忍不住吐露自己跟主角的妻子有染。(我承認這是精神污染)然而《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不可能觸立存在於村上小說的動線上。尤其在《1Q84》之後明顯地將書寫的方向由經典文本而起的重構,轉而投入古典音樂的探索,Drive My Car 的故事正好夾在這個時期的中間(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 (巡禮之年 - 李斯特)和 刺殺騎士團長 (唐璜 - 莫札特) 。村上老爺在探尋文本的音樂性的路上,寫下了這樣的一篇小品。濱口龍介首先是一個優秀的編劇,懂得在這動線上撿拾有用的角色與情節,補白了角色的真空。一次無日無夜的北海道公路旅行,一個女學生潛入熟人家中的冒險,一段無稽的化身成八目鰻的夢,在在都能看到同時期兩本長篇小說的影子。只有這樣的改編,才能讓本來有如草稿的短篇故事,豐富成一段公路旅程。
如果這輛SAAB 900一直在東京市內繞圈子的話,大家都只會裹足不前。
不論是文本小說,還是電影劇本裡面,契訶夫的經典劇作《Uncle Vanya》都有著不可輕視的地位。Curtains were blue,我們不會知道這劇作在村上心目中的意義,最少我們可以肯定在唐璜之前,作家的目光早就開始走向劇作。而有趣的是,《Uncle Vanya》之所以成就經典,是契訶夫事隔十多年後從新改寫自己的劇目,原版叫《Goblin》(或《The Wood Demon》)。幸好村上春樹沒有真的去重寫《海邊的卡夫卡》,他很快就放棄斧鑿這個故事,把這篇草稿輕輕放下。他結果將家福這個男人一分為三,讓三個聲部互相模仿對位和追逐,寫成夾雜著豐富Canon 和Fugue技巧的長篇變奏。 (我明白大家會抱怨推論不足,假如真的有讀者看到這裡的話,我們找個機會再寫。)
電影裡面的《Uncle Vanya》肢離破碎,不僅是情節出現的次序跳躍,擔任角色的演員也是轉了又轉,時而是演出,時而是排練,更多是家福和錄音機條件反射一般的對答。濱口龍介不僅將一齣戲劇完全地消化到電影裡面,更將外語劇場的本質交融到小說作品的主旨,容讓現實中不同國籍、年齡、語言的演員一同參演,平實展現出人與人之間固有的不解,詰問世間有冇超越語言的解讀方法。
這一齣電影到底是村上春樹的小說改編,抑或是濱口龍介的電影呢?Better be bo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