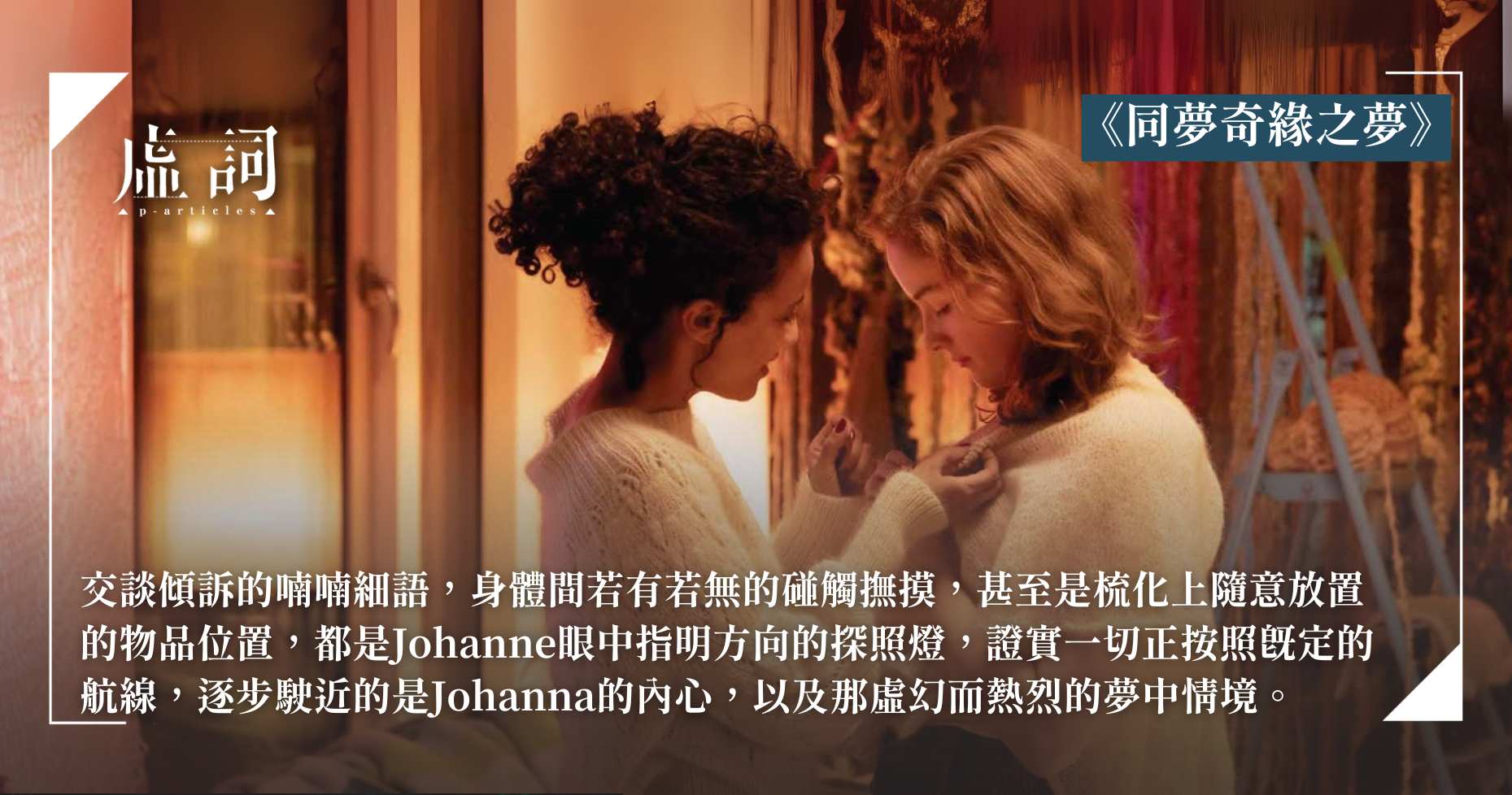〈黛玉笑了〉:捻花而笑的林黛玉
其他 | by 余永曇 | 2025-07-03
余永曇傳來〈黛玉笑了〉詞評,詞人周耀輝將《紅樓夢》中林黛玉那多愁善感、葬花哀悼的傳統形象,重新塑造為捻花微笑、豁達開竅的現代女性。〈黛〉中的黛玉從感嘆命運無常,轉而以微笑面對離合,展現「敢愛敢分」的現代愛情觀。由「葬花」的細膩哀愁,到「捻花」的瀟灑釋懷,映射出當代情感哲學。 (閱讀更多)
《不赦之罪》與「重蟹」——關於重量、罪愆與上帝
雙雙傳來《不赦之罪》影評,他以不可靠敘事者的視角切入,剖析梁牧師對女兒之死與陳梓樂「不赦之罪」的執著糾葛。他將此與基督教反墮胎教義、告解儀式,以及李滄東《密陽》中「原諒」的掙扎相對照,並借《化物語》的「重蟹」意象,揭示人們試圖將罪愆與過失交託神靈、追求「卸下重量」的心態。雙雙認為,真正的贖罪不在於獲取赦免,而在於勇敢承擔、持續背負,探問在無法卸下的重擔前,神的凝視如何賦予有罪者前行的力量。 (閱讀更多)
「怪異」背後的意義:讀杜正勝《物怪故事解:中國亙古流衍的心態》
書評 | by 邱常婷 | 2025-07-01
邱常婷讀杜正勝《物怪故事解:中國亙古流衍的心態》,指出物怪是「非常」的存在,源於人類對未知的恐懼與想像,根植於集體無意識或文化積澱的「常」被打破。這些看似怪誕的故事,實則承載著深層的文化密碼、社會慾望與歷史脈絡,是古人理解世界、傳遞知識的方法,甚至成為上位者政治操控的媒介。 (閱讀更多)
汽笛再響,迷霧中仍有我:鴻鴻讀陳滅《離亂經》
鴻鴻讀畢香港詩人陳滅《離亂經》詩集,認為陳滅有如當代的吟遊詩人,唱著失落的情歌。陳滅以中國詩詞修辭與西方電影技巧交錯,呈現一種華洋混雜的現代感,這本是香港城市及香港詩的本色,卻在新時代的碾壓下,成為身分的證明。鴻鴻指出陳滅以小寫的我單挑大寫的香港,因而許多句子、許多意象,都爍金為刃、凝土為器、氣湧成歌。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