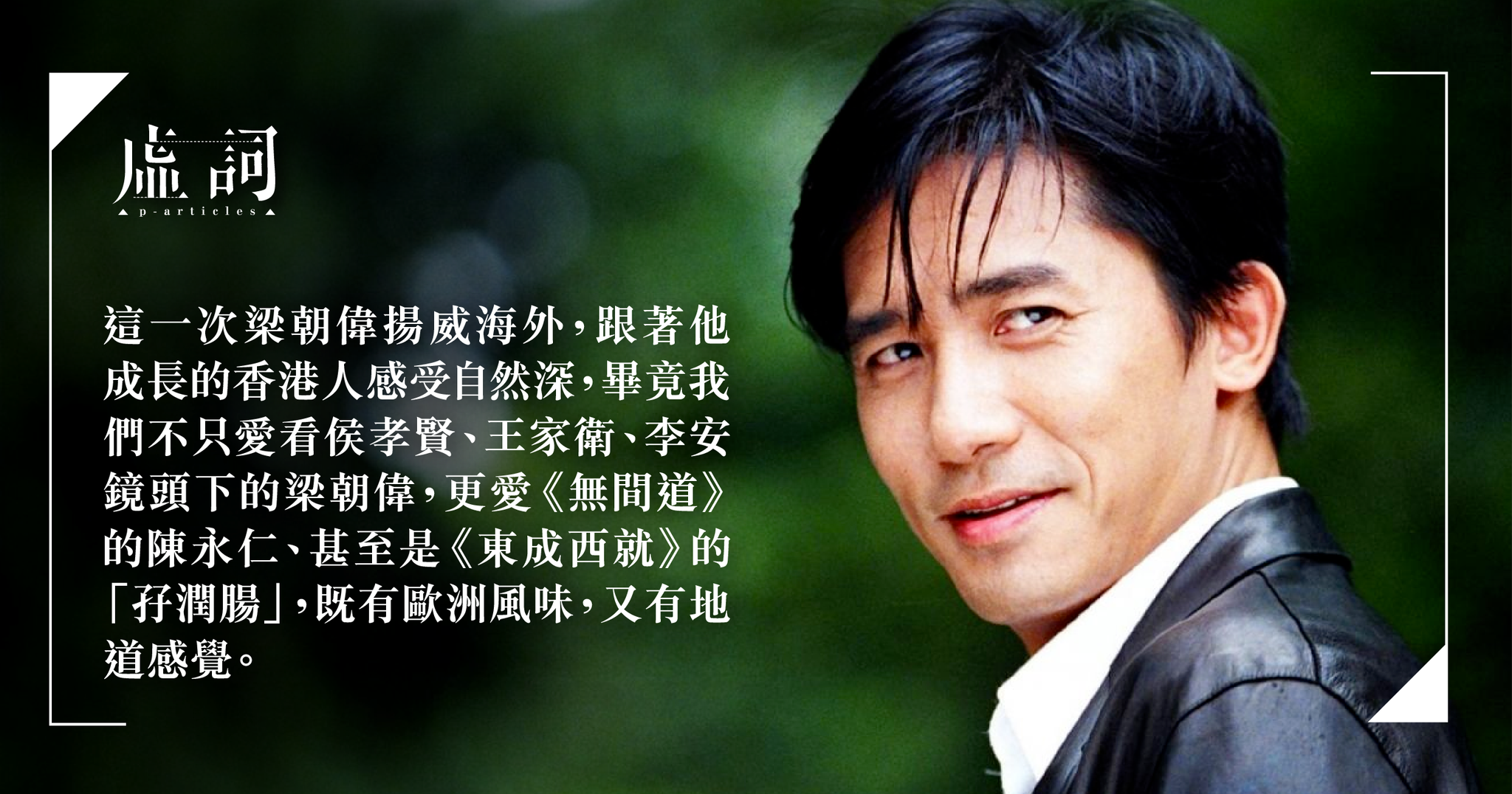【無形・致我們終將遠去的校園】 有人坐在我對面——校長室素描
為了謹慎一點,我們不妨將推論過程縮短﹕看看校長室,就可以知道這是一個怎樣的校長。這大概應該沒有甚麼人反對,就像我們走進一間房子,看看「歐洲風」、「韓國風」、遷就孩子、利便寵物等的家居設計與用心方向,推算房子主人心儀與關注何在,合情更合理。如果你有足夠的緣份,人生中看過許多不同的校長室,你又真會發覺中間有很大的不同,至於「同」和「異」,往往辯證地互相發展滲入。書桌連「大班椅」常居於當中要塞,然後電腦、打印機、文件櫃、書櫃、電話,總有空間放著出席某某典禮、交流訪問的嘉賓留念銀碟,哪一個都差不多……不過校長的氣派與心事,在裝璜佈置中又透露一二,例如數十尺的私人洗手間、來一組英式設計的古典吊燈、一套三件的歐洲皮沙發配意大利磚木紋地板,想像圍坐時談笑風生,或好茶慢煮,或几淨無塵,哪一個都不一樣。 (閱讀更多)
【虛詞・致我們終將遠去的校園】更衣室
家在街市賣水果,她手心沾染果皮的鮮,或者是因霧氣而生的餲罨,不過,相比起其他檔口,已經無甚異味。「嘖嘖嘖嘖,已經咁大個女。」有些中年男客,每次見她到攤檔幫忙,都重複同一句話,然後請她親自挑選水果,全程盯著她的臉,又移目光至胸部。也許是她敏感多心,可是,總相信即使自己將一個爛橙放進去,以後他們還是會光顧。 (閱讀更多)
【無形・文學館在他方】逛日本各地文學館的旨趣與追想
長年浸淫於日本文學的我,不覺中,或因工作,或純粹是個人偏好,赴日時,腳步總不由得朝當地周邊的文學館而去。從南到輕井澤造訪各地的文學館如下:九州小倉的松本清張紀念館、同在小倉,被列為史蹟的森鷗外故居、和歌山縣的佐藤春夫紀念館、南方熊楠紀念館、奈良的志賀直哉故居、神戶文學館、茨木市川端康成文學館、追手門學院大學宮本輝Muesum、鎌倉文學館、位於橫濱的神奈川近代文學館、金澤文藝館,以及以東京為最多去處的文學館,例如世田谷文學館、三鷹的太宰治文學沙龍、山本有三紀念館、星與森與繪本之家、新宿早稻田的漱石山房紀念館及中井的林芙美子紀念館、文京區千駄木森鷗外紀念館、田端文市紀念館、日本近代文學館、池袋舊江戶川亂步邸書庫、講談社不對外開放的書庫、日本推理文學資料館、市谷之社書與活字館,輕井澤高原文庫、繪本之森美術館等。 (閱讀更多)
【佬訊專欄】竊書不能算偷,唔還書就是狗
「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猶記得因為偷書而被打斷了腿的孔乙己,是出自魯迅筆下,而佬訊竟真被朋友竊了書,他甚至否認借書的事實,令佬訊得以用一本書看透了一個人。但他沒打算放棄追問,決定和朋友來個鬥長命的遊戲,對方扮忘記,他也可以扮忘記。 (閱讀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