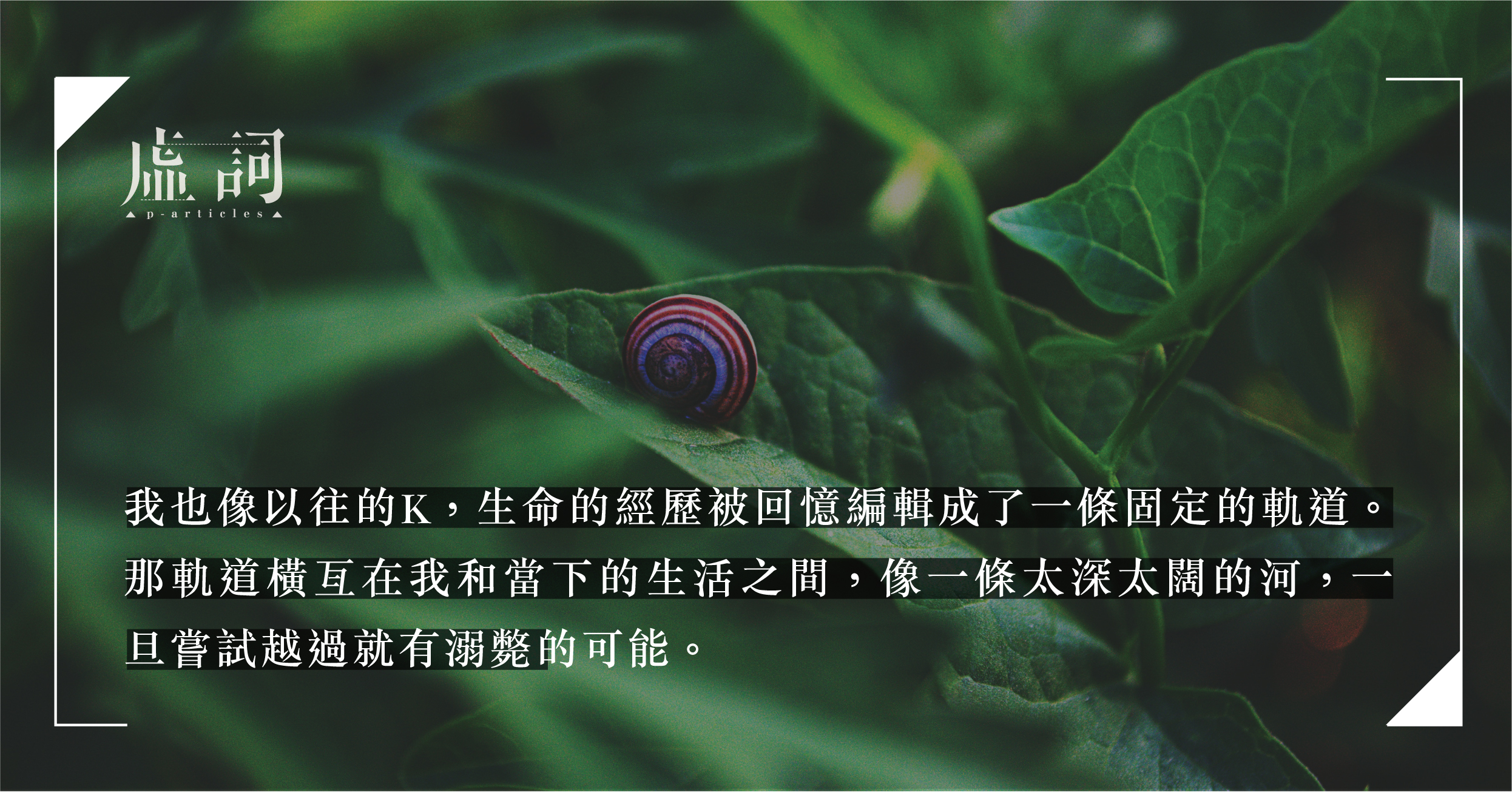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敍事漩渦
我總是記得那些陽光滿溢但乏善足陳的下午,晴朗對於虛空的生命無補於事。K如果不看書,就會拉著我,要我坐在她面前,聽她訴說那些淤塞在她生命裡難以釋懷的事。K的故事開展於我出生之前,至於我出生之後,她的日子似乎只是在沙漏中不斷溜走的砂,過活卻忘了要活著。我不是喜歡而是必須聽她說話,而且學會了,聆聽要用上的不只是耳朵,還有,用眼睛注視她表情的起伏,用鼻子辨析空氣的變化,用皮膚上的每一個毛細孔感受她情緒的光暗。K並不具備任何獨特的敍事技巧或才能,她只是有一團密度很高的憂鬱。童年至青春期,許多個這樣的下午至黃昏,我無法在她跟前離去,並不是因為她每次都在重複相近的經歷只是巧妙地變更細節,而是那團憂鬱既濕又重,一直壓著我,使我難以動身,慢慢地成為了我身體裡的一部份。
當人的生命裡開展了經歷,經歷成為了回憶,回憶成了一種敍事的模式,執念生成了重複的軌道,皮膚上才會開始爬了頑固的皺紋,皺紋很像後天的掌紋。「習慣成為性格,性格形成命運。」有一本書這樣說,我迷信了這樣的句子。
後來,我活到了K生育我的年紀。每個清晨,我的意識離開了一堆夢之後並不願醒來,為了迴避回憶角落裡的愈鑽愈深的黑暗。我也像以往的K,生命的經歷被回憶編輯成了一條固定的軌道。那軌道橫亙在我和當下的生活之間,像一條太深太闊的河,一旦嘗試越過就有溺斃的可能。
每個人都是自己生命的敍事者。K在反覆的敍述之中漸漸無比堅定地相信,她那經歷了半生流徙的父親,晚年被長子背叛,親人之間為了利益而相互離棄就是命運的主軸,所以,她所先後遇到的兩個人,她以為可以倚靠,終於也因為不同的原因而丟下她。
(但她沒有說,丟棄原是一種互相促成的結果)
我盡量保持沉默,但我在暗裡每天都對自己訴說,八年前,當我離開了一個人和一所房子,也同時失去了一隻手或一隻腳,半個心臟或一邊腎臟。每天的每個小時,我都對自己重複敍述一種缺失。身體裡彷彿有一個很大的,無論被任何的人或事物穿過也不會生出任何感受的洞。
是甚麼原因,我相信了這種敍事?某個我不願起床的灰色上午,我看著貓又在重複早上的巡邏路線圖:床上、窗台、書桌、客廳的窗台、廚房窗子,最後是淋浴間的去水道。貓以氣味作為記號,劃出了屬於自己的範圍和邊界,作為每天的作息分野,間接設定了自己一生的際遇。我發現自己跟貓如此相似,貓使用的是氣味,我動用了回憶。
是甚麼原因,我相信了這種敍事?我記得,童年時期那個生命張開著充滿可能性的空白,像水一樣流動的自己,那麼渴望被將要發生的故事填滿,成為一個具有固定形狀的實實在在的成人。可是,當經歷的軌道一圈一圈像漩渦那樣囚禁著我,我再也無法自漩渦的中央逃脫。
為了得到一種暫時的中斷和靜止,我參加各類的打坐、靜心、冥想和療癒活動,在閉上了眼睛,只有一呼和一吸的時候,心慢慢地靜下來,於是,我慢慢地感到一種愈來愈巨大的恐懼——要是拋下了這樣的敍事,我還剩下甚麼?或許只有一種甚麼也沒有的沒有盡頭的灰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