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飛機
散文 | by 陳俊熹 | 2023-02-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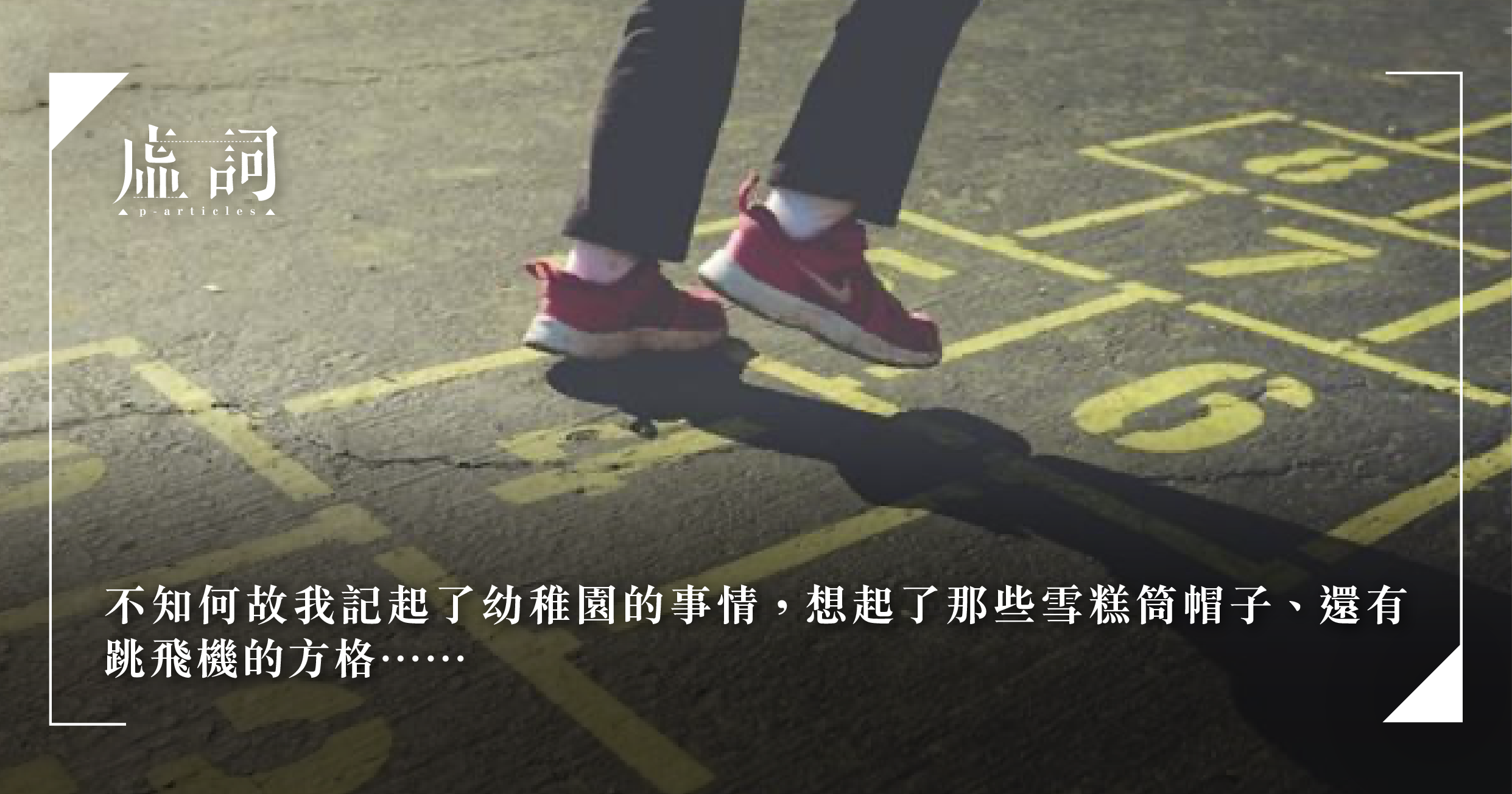
330321838_724565905702357_3453409611452438967_n.png
在畢業前最後一次生日會上,老師忽然跟我們說起,小學是沒有生日會的。
我小時候所就讀的幼稚園每兩個月便會舉行一次生日會,為那兩個月生日的小朋友慶祝。那天會少上兩節課,大家跟着老師唱生日歌、影大合照、吃零食。幼稚園的色調本來就很繽紛,生日會更甚,天花掛滿紅紅綠綠的彩帶,老師會和我們一起戴雪糕筒帽子。我很喜歡這樣的生日會。當老師告訴我小學沒有生日會時,本來對小學無甚概念的我馬上害怕起來,沒有生日會的校園生活一定很恐怖,向來絕少哭泣的我不知為何哭了出來,而且無法止息。另一個老師為了安撫我,於是帶我到樓下的花圃去跳飛機。我在方格子裏邊跳,老師在旁邊跳。老師口中數着一、二、三、四……又讓我跟着她一起數。很神奇,口中一、二、三、四的數着,哭泣聲就漸漸地、自然地止住了。老師牽着我的手,我們一起回課室。
這件事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擅自認定了小學是灰色的。有段時間我誤將元朗工業邨一座外牆灰白的工廠當成小學,每次經過都拉着媽媽的手快步離開。後來才知道不是。
我問父親關於他以前上小學的事。他假意推搪說四十多年前事作不得準,其實心裏根本很想說。他以前讀基督教小學,早會有類似禱告的儀式,大家都要垂首闔眼,聆聽禱文。還是小孩子的父親會張開眼睛,偷看其它人有沒有閉眼。有時會和其它頑皮的傢伙對上視線,然後亂打眼色、露出古怪的鬼臉。真有趣,我將遊移的目光想像成小魚、在死水中撥起漣漪。我忽然覺得小學沒有原先那麼恐怖。在灰黯沉寂的世界中,似乎只要能與這些冉冉而動的有靈的眼睛相接,我就能堅強地活下去。
如今回想起來,小學教過我的老師大多都不太正常,尤其是小一班主任。小學不像幼稚園般可以常常活動,多是靜靜地坐着聽書。我總是在座位上動來動去,我不想被人注意到,但我不做些小動作就會很難受,我儘量不讓人察覺、不發出聲音,但老師們一看見我這樣就會用難聽的說話罵我,認為我有心擾亂秩序。我覺得他們都是壞人。老師向班主任投訴我的課堂表現,於是我成為了她「重點整治」的對象。只要坐得稍有不端或是挪動了一下,她便懲罰我,要我抄書、留堂、罰企。她又把我帶到別的班房讓其他同學嘲笑我:
「嗱,大家識唔識得將雙手放喺檯面唔郁啊?」
他們都說識得。
「但呢個人唔識喎,一唔郁嚟郁去就身痕,佢奇唔奇怪啊?」
他們都說奇怪。
接着便是一陣笑聲。我不明白他們為甚麼會笑得那麼高興,我不知道有甚麼好笑,於是我小息時很認真地跑去問他們,他們想了很久,就是說不上來,最後只歪着頭說不知道。他坦言那的確不是有趣的事,只是直覺感受到老師想他們笑,於是順着氣氛笑出來。有時候沉默反而有聲,從眾呼喊是為了讓自己的聲音隱匿在時代的主旋律中。我從此學識了,要以呼聲回應沉默,要以沉默回應呼聲。
後來我揣摩出一種發洩好動癖性的方法,我在櫃桶中畫下跳飛機的格子,然後墊上一些透明的文件套作緩衝吸音之用。每當我想郁動,或是老師將其他班的傢伙帶來遊街示眾的時候,我便以手指跳飛機。這讓我感到很安心。不論老師施予何種限制,我都有六個可以自由跳躍的格子。
不過這種自由很快也被禠奪了。
那時學校舉行了名為環保週的活動,只要帶手帕回校就能得到貼紙。我很想得到貼紙,所以乖乖準備了手帕,攝在短褲後袋。但我就是無法克服好動的怪癖,午會時我忍不住在櫃桶中玩起了跳飛機的遊戲,被班主任發現了,她把我叫出來:
「其實你係咪有病?係咪唔識控制自己對手?」
「我冇病,但我控制唔到對手。」
她拍檯,嚇得我退後了一步。她認為我在駁嘴,叫我行前兩步,捉起我雙手,隨手拿來一卷封箱膠紙在我手腕處纏了三四圈,然後將我擱在原地、叫有帶手帕的同學出來排隊拿紙貼。我有帶手帕,但雙手被膠紙縛着無法伸到後袋。看見我掙扎着想將手帕拿出來的樣子,有個女孩想幫我。
「唔好幫佢,等佢自己嚟。」
她縮開手,回頭悄聲跟我說,對不起,我抽一抽鼻子,向她點頭。班主任注意到了,她刻意大聲說:
「唔洗同佢對講對唔住,佢自己攞嚟,佢係抵死,你哋唔好黐埋佢到。」
我睜大雙眼瞪着眼前這個被稱作老師的人,我無法相信為人師表者竟會敵視一個小女孩最真摯無欺的善意,她翦斷了人類間最質樸美善的連結,她是大惡人,我本能地感受到充溢頭顱的怒意和仇恨,我要殺死她。她用膠紙將我雙手扣起,於是我用頭鎚撞她,我像瘋狗一樣撲向教師桌。事情變得很嚴重,我被兩個大人制服。訓導聽完班主任的話之後將我拖到樓下教員室外的走廊。他擰起我的衣領:
「你知唔知自己做緊咩?」他明知故問,我沒有說話。
「問你啊,係咪聾咗啊?定啞咗啊?頭先好惡㗎嘛你,成隻顛狗咁㗎嘛,出聲啦。」他用另一隻手拍我的臉,又搖我的衣領,好像要把昏迷的人拍醒,不過,我清醒得很。
他以諷刺、喝罵以及可怕的沉默來懲罰我,又逼我認錯、朗讀出不是罪名的罪名。我一句話都沒有說。如此耗費了不知多少時間他才停止了教訓。他很小心地將膠紙剪開、撕下,我手上只留下淺淺的、易癒的紅痕,我誤以為這是他的温柔。下午的課全都沒上,見了社工(那時我們有種奇怪的觀念:不正常的傢伙都要見社工,見社工的傢伙都不正常),又見了副校,他以一種温和的口吻對我說教,說了些「無論甚麼情況都不能用暴力解決問題」、「老師其實只是為你好」、「你以後會明白她一片苦心」之類的話,最後又說破例不記過,只要午休罰企三個月。他們軟硬兼施,甚麼都做了,唯獨沒有通報家長。我亦沒有提起這件事。
那天感覺漫長之極,已經很累了,回到家只想攤在梳化午睡。正義、公平等等,似乎變得不怎麼要緊。比起喧囂揚厲的大義,此刻安靜較有利於癒合。六時的倦日是夏天僅有的温柔,樓下的車聲很遙遠,我在寧靜中小睡。不知何故我記起了幼稚園的事情,想起了那些雪糕筒帽子、還有跳飛機的方格……我今天的表現比那時候堅強得多了,在班主任面前沒有哭,在訓導面前沒有哭,在班副校長面前也沒有哭。這些事情我都獨力擔荷了。我這麼了不起,最後卻還是沒拿到貼紙呢,我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