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的我
散文 | by 麥嘉悅 | 2022-01-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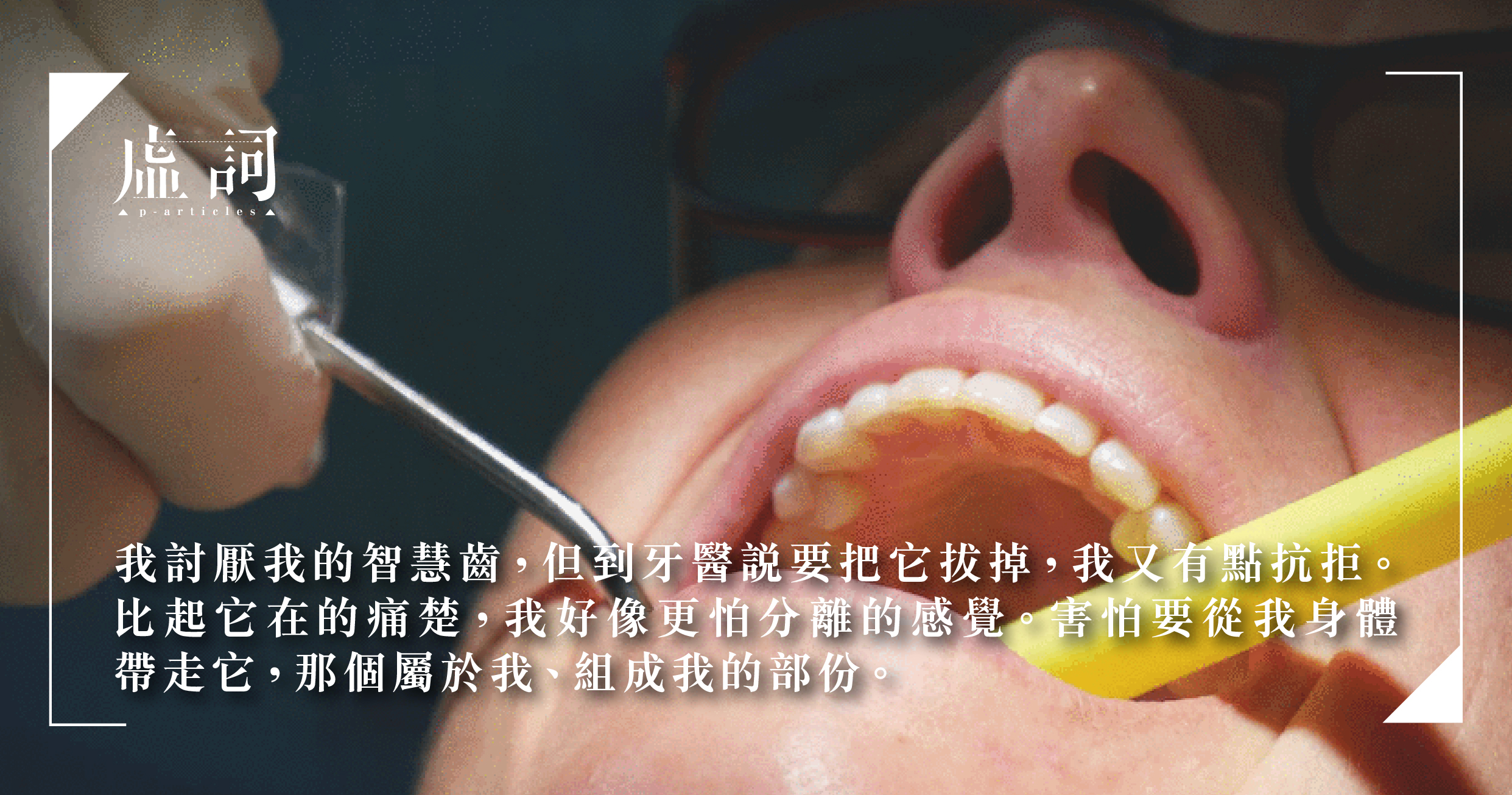
271528311_1080708302706836_2610136477003817282_n.jpg
最近潛伏多年的智慧齒打算要冒出頭。
「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絕對是用來形容智慧齒的,像是將每月的經痛轉移到口腔發生,而且是每日進行。
我討厭我的智慧齒,但到牙醫說要把它拔掉,我又有點抗拒。比起它在的痛楚,我好像更怕分離的感覺。害怕要從我身體帶走它,那個屬於我、組成我的部份。離別的感覺太難受,卻又不得不揮手道別。
感覺拔牙是在逼迫我預習面對死亡。
預先綵排旁人定會離我而去的結果,像是不得不拔的智慧齒。或許,神在構造人體時,早已悄悄安排我們演練擁有又失去的過程,免得日後如期而至的死亡,會對人打擊太大,如骨牌一般,一個接一個的倒下。
隨年歲漸長而萌牙的乳齒,然後又在不知不覺間,逐一脫落,無一悻免。我習慣把每一隻小小的牙齒都留著,存放過去的自己,一塊殘缺的碎片,一具逝去的屍體。人因為不捨,會想盡辦法去逃避死亡。牙齒離開了身體,但我要留它在我身旁。人為甚麼要安放祖先的骨灰,怎麼不隨便撒撒?就是想有一個痕跡,要不然,慢慢就沒有人會記得你,得留下甚麼。
空洞的牙肉是無名碑,紀念存在過的牙齒。頭幾天都是瘋狂用舌頭去確認,看看是否真的不在,只少了一兩顆牙,口腔卻像拓寬成豪宅,有點寂寞。不過沒有了智慧齒會癒合,恆齒又會馬上填補空缺,無論是我還是口腔,都會習慣了沒有它的存在,只有疼痛的記憶是深刻,但亦逃不過逐漸模糊的結尾。
大抵人都有點犯賤,犯賤的喜歡被虐,太過順遂的活著,便不覺得自己活著,痛楚也不是甚麼壞事,比起再也不會痛,要好太多。
還有,我打算染頭髮。
打算在二十歲時迎接遲來的叛逆期。
不想再聽到別人對我的印象停留在乖巧的層面。
我卻停留染頭髮等於壞孩子的封建時代。
髮色新潮。
思想古舊。
說起頭髮,想起了以前被媽媽抓去剪短髮的時候。
每一次我都蹲在地下,哭著拾回被迫離我而去的頭髮,哀悼死掉的它們,然後又因為不捨,所以裝到空的糖盒,偷偷藏著。有時收拾東西,又會再遇上糖盒,打開後拿起髮束揉揉,很幼細滑嫩,手感上與自己現在頭髮上的沒甚麼分別,但它也不會再長了。感覺有點噁心,像是下蠱需要的道具,明明是自己的頭髮,看著倒帶丁點邪門的味道。後來我長大了,媽媽也沒再將我捕獲,我也任由頭髮隨便長。本以為頭髮就會一直長下去,但我跑去一口氣剪掉了,更是一次比一次剪得短。
第一次剪短是在放榜前幾天,由及腰爬到胸前。
第二次是放榜後,它到了耳旁。
最近一次是十月份,還不適應新生活的時候,頭髮又回到放榜前。
不說都說頭髮是三千煩惱絲嗎?每剪一次就覺得有些問題像是已解決,感覺自己思想也浪漫。剪頭髮會上癮,按生活困難程度而定長短。解決不了,那就多剪些;只是心有點煩,那就酌量意思一下。
也許是一個自殘的替代方案,有勇氣去捨棄,但沒有勇氣傷害自己。以前頭髮就是命根,容不得別人動手動腳,雖說反抗不了被剪的命運。現在卻是可有可無的,發生甚麼事便可立馬拋棄。
雖然沒有流血,但有最明顯的外傷。每次剪頭髮,都是在內心偷偷傷害自己的過程,還要留下每個人都看得出,十分張揚的證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