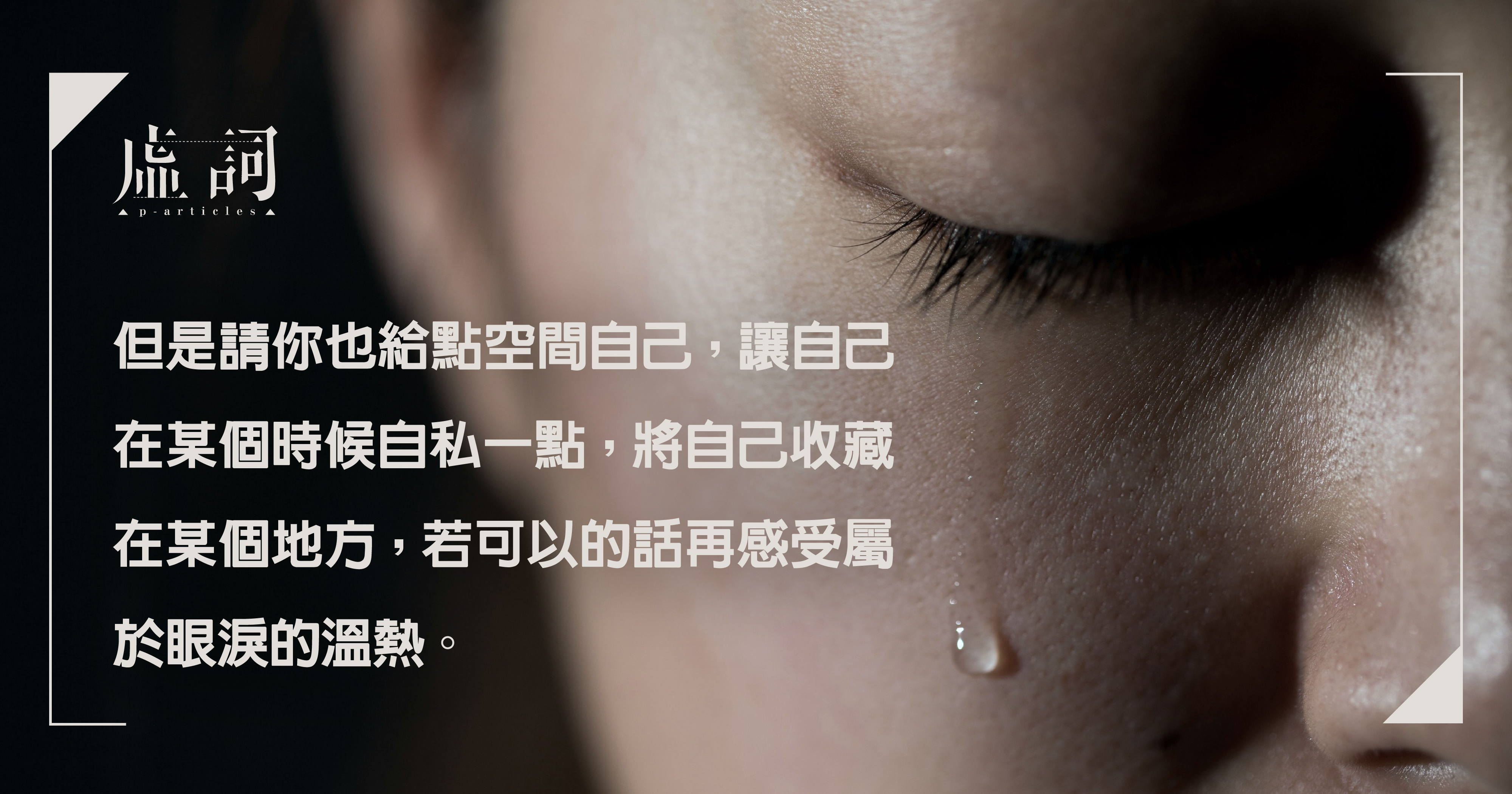【虛詞.見字__】見字,請你哭一場
見字,請你哭一場。
你,多久沒有哭過了?
曾經在社交媒體有過討論,究竟看《狂舞派3》哭的死去活來的我究竟是不是正常,然後得到了「如果沒法哭出來」才是不正常吧的說法。然後,那位朋友在這句話後面加了個扶額的符號,暗示了他也是自己口中不正常的一員。這對我來說是難以理解的。為什麼會哭不出呢?明明我們能夠從電影中看到現實的影子。我們是多麼的絕望而痛苦,而看電影是其中一個不錯的發洩出口。我又問了其他的人,他說,因為太過絕望,眼淚已流盡,就再沒有令他流淚的事情。
在這個城市的所有人無疑是絕望的。曾經,我們以為能夠和平地走到馬路,在夏日的陽光下呼叫口號。曾經,我們以為團結的力量可以令政權聽到我們的聲音,聽到我們的吶喊。他們也許會知道做某些事情對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益處,也許會認清我們為什麼反對。我們還記得二零零三年的時候,那些權貴和官僚看到了數百萬人擠滿的街道,他們願意後退一步,彷彿我們得到了某種勝利。
這次在開始的時候我們或許也有同樣的想像,但隨著時間的推進我們很清楚那只是幻想。我們以為十幾萬是不足夠的,所以百萬人走出來,又到二百萬加一個人,卻只換來了一句「壽終正寢」。
又可能是我們看到活生生的生命變成了墓碑上的文字,可能是某些人的死不悔改,於是又沒有嘗試去忘記。但是當中我們放棄了什麼,又得到了什麼,在這個時候其實說不清楚,更是深化了這種絕望。我們可能最後會失敗,而失敗的結局就是我們所愛的這個地方,和愛這個地方的所有人,都不會存在:這與種族滅絕不相同——種族滅絕的倖存者在遙遠的他方或許有能力,甚至有責任去記著發生過的事情。但是我們是被殖民,我們的文化只能夠融入侵略者的所謂文明裡面,我們的身份也只能夠被吞併。
我們是絕望的,看不到出路般盲目地走向一個未知。這也許就是我的朋友沒法哭的原因:在這樣的苦難之中,已經無力再哭了。或許就是無力到連流淚都無法做到。
或許有另一種說法。我們好像不應該在這個時候痛哭,彷彿應該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很多時候會有人說,哭解決不了問題,比起浪費時間去痛哭流涕,不是應該做更重要的事情嗎?我們聽到她在電視上,那鱷魚的嘲笑。紙巾接住了她的眼淚,承載了那份虛偽。我們就算如何悲傷也於事無補,倒不如做其他事情,寫畫文宣,走上街頭。就連抗爭也充滿了這個城市的味道,我們需要快與效率。
我們好像是自然地壓抑著我們的情緒,或者是負面情緒,將當中有用的憤怒和勇氣提煉出來,為我們的行動去服務。憤怒可以令我們可以有反抗的動力,勇敢令我們能夠走上前,但悲傷好像只會讓我們繼續沉溺在自己的情緒世界中,並沒有任何推動力。簡單來說,即使我們在談論感性,也是用理性去判斷有哪些情感比較可取。
所以,我們貶低了悲傷。
到這個時候,我總是忍不住去問,我們可以自私一點嗎?即使對未來彷彿沒有幫助,但是人需要屬於自己的空間。我們可以找個時間給自己,看看那些沉重的書,看看無權力的我們可以做什麼,看看其他同路人在這場運動的記錄,看看那些不想再看的紀錄片和電影。有時好好的哭一場,然後重新回到自己的崗位,讓我們的呼吸得到空隙。而當我們擁抱悲傷,我們或許會更加強大:因為我們更加能夠理解自己,讓無力和絕望減少一點。
或許能夠在動植物公園看樹與花,還有天空的雲層;或許能夠在海旁看浪與橋,還有遠方的倒影;或許能夠在家的一隅看詩看文,還有來自他國的小說。 讓我們打開葉慈的詩集,說說那最美好的時代。也讓我們看看卡繆的反抗者,吶喊著要麼全有要麼全無。讓我們看看台灣的故事,讓我們為了民主化的血腥而哀悼,為現在還算美好的未來帶來些微信心。讓我們看十年、看地厚天高、看黃之鋒的紀錄片,讓我們看看曾經走過來的歲月,讓我們記住這一切的情感,憤怒,無助,以及悲哀。讓我們相隔屏幕,相隔文字與紙本哭泣,然後又用墨水承載自己的眼淚,傳到很近又很遠的大家心上。
我很清楚有人現在是沒法哭泣,就像我的朋友那樣。但是請你也給點空間自己,讓自己在某個時候自私一點,將自己收藏在某個地方,若可以的話再感受屬於眼淚的溫熱。
見字,請你哭一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