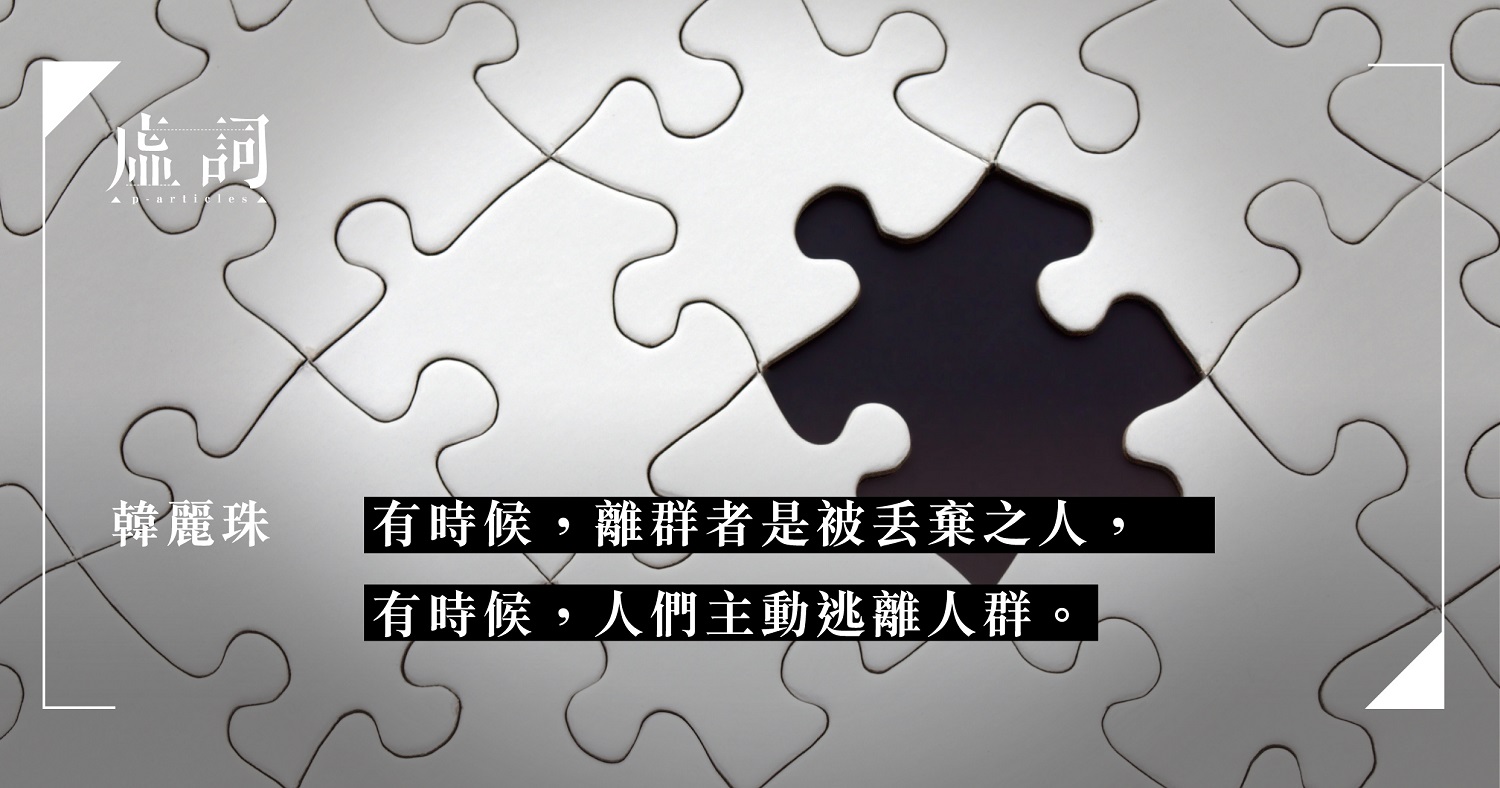【韓麗珠專欄︰越界的誡】不笑防空洞
踏入青春期之前的一年,我遇到了一種狀況,然後作出了一個決定。那時候,我決定,以後都不再笑。
當然,在以後的日子,我還是會笑,例如,禮貌的微笑、大夥兒說笑話時跟著大家的節奏一起笑、為了使對方高興而把自己的嘴巴掀動成一種友善的弧度,甚至,為了逃避某種「你常常黑臉」的譴責而不自覺地堆起了笑容,也有,忍不住笑個不停的時刻。
但,從決定戒掉笑的那天開始,我可以清晰地感到,內心和臉面之間的某道重要的橋樑,已永久地中斷。我需要這樣的斷裂,來紓緩失去對人類世界信任的衝擊,只有這樣,我才可以從孩子過渡而成為少女,然後是大人,沒有人能走進來,我再也無法走出去。我可以通過不笑,把自己收藏在安全的角落裡,像戰爭時期的防空洞。
沒有任何原因(起碼,我無法偵測到是何種原因),課室內的人圍成了一個圓圈,我被趕到圈外去,無論同學或老師,看著我的眼神都帶著冷漠和嘲弄。他們有時看見我走近,便會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我無法得知對話的內容,但不友善的氣氛,是異常渾濁的空氣,令我時常感到窒息。後來,我逐漸學會了,無論走到哪裡,在一個群體之中,總是有一個,或幾個人,會被攆到圈子以外,圈內的人成了緊密的人鏈,被排拒的人,無法再回到那裡去。有時候,被趕出圈子的人是我,有時候,被趕出去的是另一個人,有時候,離群者是被丟棄之人,有時候,人們主動逃離人群。
很快,我學會了和群體保持距離。如果必得有個人被攆出去,我不太介意那個是我,如果必須選擇,我會主動離開人群。
在人體所有的器官之中,只有嘴巴可以張開或閉上,可以吐出好話或髒話,嘴角可以往上揚或向下彎,意義截然不同。關閉是一種懲罰,責備我疏忽了對自己的保護。我要把內心藏在身體的深處,再也不要通過嘴巴把脆弱的心隨意泄露。可能那時候,我就妄想著要把自己改變成,虛偽的,冷酷的,強壯的,剛強的成年人。不過,也是在多年以後,我才知道,虛偽的技藝,並不在於真誠的關閉,而是假裝的親切,不是外露的黑臉,而是任何時候都可掏出一副能應對不同場合的笑臉。要是想把自己藏在安全而沒有人找到的角落,應該要培養的是百變笑臉,而不是不笑的決斷。但我知道這一點時,已經太遲,我已經練習了過多誠實的技巧,而且,已經老大。
那天,我讀到一段關於新疆的新聞,人們將會因為臉露不滿、不屑或過於倔強的神情,而被政府懲罰。令我驚訝的,並不是在法律上,對於面目的規管,不久後將會在現實中出現,而是,我突然覺悟,原來以往多年,我所做的並不是關閉,而是一種揭露──揭露了因為憤怨而把臉面的門狠狠地關上這件事。這樣,不但把無禮的干擾引進來,甚至可能會,惹來無理的規訓。我所做的和我所想要達到的是相反的方向。
我惟一能慶幸的是時間令人變得柔軟,不再妄想通過戒律改變自己,而順應著戒律的失敗或遺忘,而完全接受自己的生而有之的個性而帶來的不可迴避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