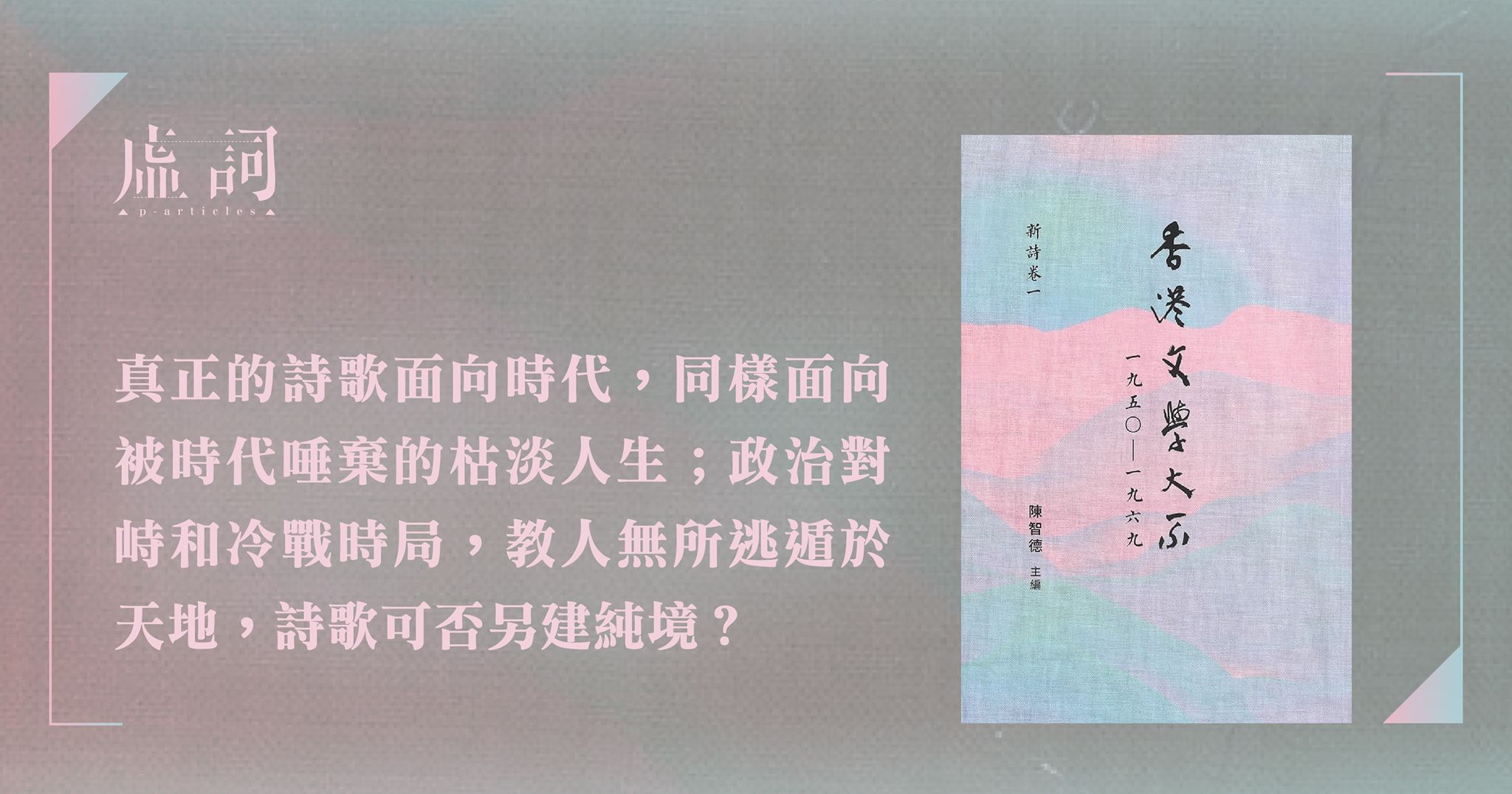追尋藏匿的香港詩境──《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一》導言選錄
一九五○年代是變動、轉折、離散的時代,一方奮進,另一方失落,在明顯可見的二元對立以外,實在糾纏更多莫名的苦思、掙扎、失語、幻滅、覺醒。真正的詩歌面向時代,同樣面向被時代唾棄的枯淡人生;政治對峙和冷戰時局,教人無所逃遁於天地,詩歌可否另建純境?詩歌以精煉、超越的語言截取片刻即逝瞬間,轉化時代精神,尋求超越的理念;那「分行散文」似的現代句子備受冷嘲、無視,長期被藏匿於幽深岩洞,脆弱欲裂的舊刊紙頁,在凝視裡成灰,但只要對文藝、對人文精神有感,便總忘不了一個一個象徵探索時代的名字。
他們當中,不少人同時寫小說、散文以至評論,在講述跌宕起伏故事的小說、書寫紀事抒情的散文以外,仍留下明知沒有多少讀者的、換不到幾許稿費的新詩,他們好像以澹泊之身、漠視虛榮和慣於寂寥的心志,凝視奮進或失落的人群,不願驚擾世界地,暗自苦思、掙扎,留下不易消化的文學聲音,一字一句,一行一語,俱是未被解讀的時代精神,一種藏匿的詩境。
本導言原分「轉折中的流動」、「藏匿的詩境」、「一九五○年代的時代精神」、「『詩選』與歷史意識」四節共一萬八千字,現精輯選錄首三節部份焦點內容,為讀者作引介。
一、轉折中的流動
相對於戰後左翼作家暫居香港數年後北返,五○年代的南來文人留港時間更長;戰後左翼作家以詩歌呼應其時中國內地左翼文論及文藝作為鬥爭的需要,以至部份作品呼籲香港人民離港北上參與鬥爭或建設,五○年代的南來文人則抱持更多個人角度的感懷,對中國內地思潮表達不同立場、不同態度的呼應,也表達出更多香港視角,又另有在政治意識形態的表述、配合以外,流露個人以至集體的失落、不安,呼應戰後長期的離散、播遷。
一九五○年十一月,何達承接他寫於一九四九年的〈我的感情激動了〉一詩的昂揚語調,再寫出長詩〈從早晨到早晨〉,從一個日常的、電車如常開出的早晨,引向一個從「抗美援朝」角度報道韓戰的報紙出版的早晨,何達由此實現出一種香港文學「流動」的其中一種面向。
四、五○年代之交,是轉折、變動的時代,也是意識形態分歧的時代,有歌頌新生,也有哀痛斷裂;有北上和留守的人民迎接解放,也有大量人民告別家園和親人,流徙往台灣或香港。因著離散、播遷及其連帶的文化差異經驗,五○年代初期詩人對時間的感受可說是特別敏感而分歧,除了何達〈從早晨到早晨〉、鄭辛雄〈送工友回國支前〉等詩所讚頌的時間,另有徐訏〈記憶裡的過去〉、〈時間的去處〉、力匡〈燕語〉等詩講述出另一種時間:哀懷過去的經驗斷裂、不信任現在,卻同樣把虛渺的希望寄託於未來。
何達〈從早晨到早晨〉一詩所呈現的熱情當然具一定代表性,但同時亦有另一種意識傾向的寫作,強調經驗和文化的斷裂,當中的情感意念傾向,同樣應予尊重和正視,例如徐訏寫於一九五三年的〈原野的理想〉一詩,以黯淡、消沉的語言,視香港為磨滅理想的所在。對徐訏那一輩來自上海的中年作家來說,其難以認同香港的心情是可以理解,而且是很普遍的,他們的作品一部份表達了對於異域的疏離,另一部份表達了對故國山河的懷戀,但當中的懷鄉書寫也經常結合了對於異域的疏離,成為一種複雜的情結。時代後退,即使緬懷過去、渴欲回鄉,亦只能咬緊牙關,繼續在轉折中流動,一整代人就這樣在流動中不由自主,留下或顯或隱的詩境。
二、藏匿的詩境
左右翼意識形態對峙、冷戰思維的影響,可說是了解一九五○年代的時代精神的基本要點,此處無庸贅言,劉以鬯〈五十年代初期的香港文學〉一文在政治因素以外,詳述五○年代作家在商業和政治夾縫中,不得不寫違背本身文學理念的通俗或政治傾向文字,標示五○年代香港文學「掙扎的特性」。
相較於徐訏、力匡和何達,楊際光的詩較少回憶過去生活或直接批判現實,而是另行建造一個在觀念上存在的「純境」,〈綠色的跡印〉、〈水邊〉、〈海濱〉等詩都是他心中那「純境」的反映,從中得到「精神藏匿」,但那「純境」不表示一種隔絕的美,卻仍有內在壓抑、矛盾與掙扎。楊際光要用詩將現實隔絕,但不表示他的詩與現實無關,即使楊際光未直接「反映」現實,他的詩也可看為對五○年代香港現實環境的回應,再看〈摑腐朽者〉、〈暴風午晝〉,對外在世界的狂亂,尤其紛擾世態對純粹事物的破壞,表達了一種沉潛的憤怒。
「純境」不表示隔絕或逃避,反而是認清世態的紛擾、政治的混濁,試圖回到現代文學語言的最深層,近乎以「潛流」的方式越過浮淺的表象,再看夏侯無忌〈夜曲〉、林以亮〈噴泉〉、李素〈落葉〉等詩,都試圖超越政治和現實世界的表象,重建詩歌的純境,卻又因這些詩歌發表在現實政治上並無出路的香港,以至報刊中不顯眼的角落,它們總以近乎「透明」的姿態存在,某程度上仍作為少數掌握詩藝和欣賞方法者的藏匿處,卻又以內省、超脫的方式突破現實困局,逆反時代的專橫,實現了一種超世的文學。
另有部份例如徐訏〈冷戰中的小熱門〉、楊際光〈摑腐朽者〉、力匡〈這世界是一個大謊〉等詩作自詩人本身擅長的抒情性突破出,表達對政治或現實的批判、諷喻,但這些詩當中的政治性並不在於抗共或反共,他們不是為了反對或支持任何特定的政治主張,卻是無法在混濁的世態中保持閒適,徐訏〈歲尾〉批評政治做成的扭曲,當中的憤慨是不分「左」或「右」的,〈冷戰中的小熱門〉譏諷受政治扭曲的文壇亂象,這些詩都從不同角度和現實中取材,寫成特定時空的香港當中不受重視的世態圖。
時代低迷,作家或對世態特別敏感的詩人尤感壓抑,他們尋求純美詩境,另建獨立的理念世界,楊際光的「純境」是一境,徐訏的〈歲尾〉、〈在夜裡〉是一境,燕歸來的「大雪阻隔了倦鳥歸家」,也是一境。在「左」「右」意識形態對立、禁忌處處、矛盾壓抑的時局中,楊際光、徐訏、燕歸來等五○年代詩人尋求一處文藝的也是精神的淨土,以詩境造之,復以詩境維護,成就得來不易的,卻又是難以被理解的、長期湮沒無聞的「藏匿的詩境」。
三、一九五○年代的時代精神
五○年代初至中期的香港新詩,瀰漫一片新月派格律化詩體的色彩,其中力匡的新詩以四句一節,隔句押韻的形式,內容更多以抒發鄉愁和針對「此地」的不滿,對五○年代初至中期的青年學生有不少影響,時人即有「力匡體」之稱,引起林以亮的擔憂,也擔心斷絕了三四○年代以來中國現代派傳統的詩壇陷於浮淺,他以「梁文星」之名甚至以他本人常用的「余懷」之名重發吳興華舊作,以及重刊自己的四○年代舊作,其用意相信在於擔心詩壇浮淺,不忍見既有的現代派傳統斷裂。林以亮近乎以一人之力,試圖對五○年代初至中期普遍瀰漫的帶五四初期至新月派時期的浪漫感傷筆調作出調整,在「力匡體」和散文化自由詩體以外,提出另一種可能性,只是林以亮這種調整的聲音,隨著《人人文學》停刊已近乎煙消雲散,備受忽視也缺乏承接,比馬朗創辦《文藝新潮》留下的影響更小,可說是五○年代香港新詩發展上一種很遺憾的斷裂。
在「力匡體」的影響與林以亮的調整之間,五○年代的香港新詩在格律體形式以外,在一些自由體詩歌中也看到對於三○年代現代派的承接,此外,四○年代就讀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的何達,受業於聞一多,同時感召於戰後初期參與全國學聯「一二‧一運動」時所領受的進步左翼理念,一九四八年來港後所寫的詩歌有表達進步左翼理念的〈我的感情激動了〉、〈從早晨到早晨〉、〈簽名──記一個知識份子的話〉,也有反映香港社會現實的〈窮孩子〉、〈在醫院裡〉、〈失業〉等詩,以至有一九五八年為聲援非洲人民的民族獨立運動而寫的〈難道我的血裡有非洲的血統〉一詩,除了既有的寫實主義,也可追溯到五○年代中後期以前,香港左派文藝刊物大量譯介蘇聯詩歌和智利詩人聶魯達的政治頌歌所做成的影響,何達〈難道我的血裡有非洲的血統?〉、鄭辛雄〈自由神下的控訴──讀《黑人詩選》〉、舒巷城〈雷諾爾回到美國後〉、李怡〈檯鐘的話──為蘇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而作〉都是這時期的代表作;今日重讀之,雖略感詩中的政治理念過於昂揚、過於自信,卻是在一九六○年中蘇交惡之前的特殊時空裡,留下一種既超越又絕世的,追求與弱勢社群同一呼息、普世共通的左翼美學。
一九五○年代中後期,戰後在香港受教育的青年詩人在《星島日報.學生園地》、《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人人文學》、《海瀾》、《文壇》、《文藝新潮》、《大學生活》、《文匯報.文藝》等刊物成長,多數先在相關刊物鼓勵青年學生投稿的版面刊登詩作,得到主持版面的編輯、作家鼓勵,而青年詩人亦在五○年代中期開始自辦文社,互相砥礪,逐漸寫出更成熟作品,例如王無邪〈一九五七年春:香港〉、崑南〈布爾喬亞之歌〉、葉維廉〈我們只期待月落的時分〉、張愛倫(西西)〈廢船〉、〈造訪〉、麥席珍〈鳥之悲歌〉、馬角(馬覺)〈香港島〉等作,足以升華情感、反映時代,留下五○年代末期,一種消頹、無助的城市面相,彷彿一個一個被冷戰時代藏匿的青年,勉力以明知不被理解的分行現代句子,記下苦思、掙扎、失語、幻滅、覺醒。
以上節錄,全文見陳智德主編《香港文學大系1950-1969.新詩卷一》(香港:商務印書館,202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