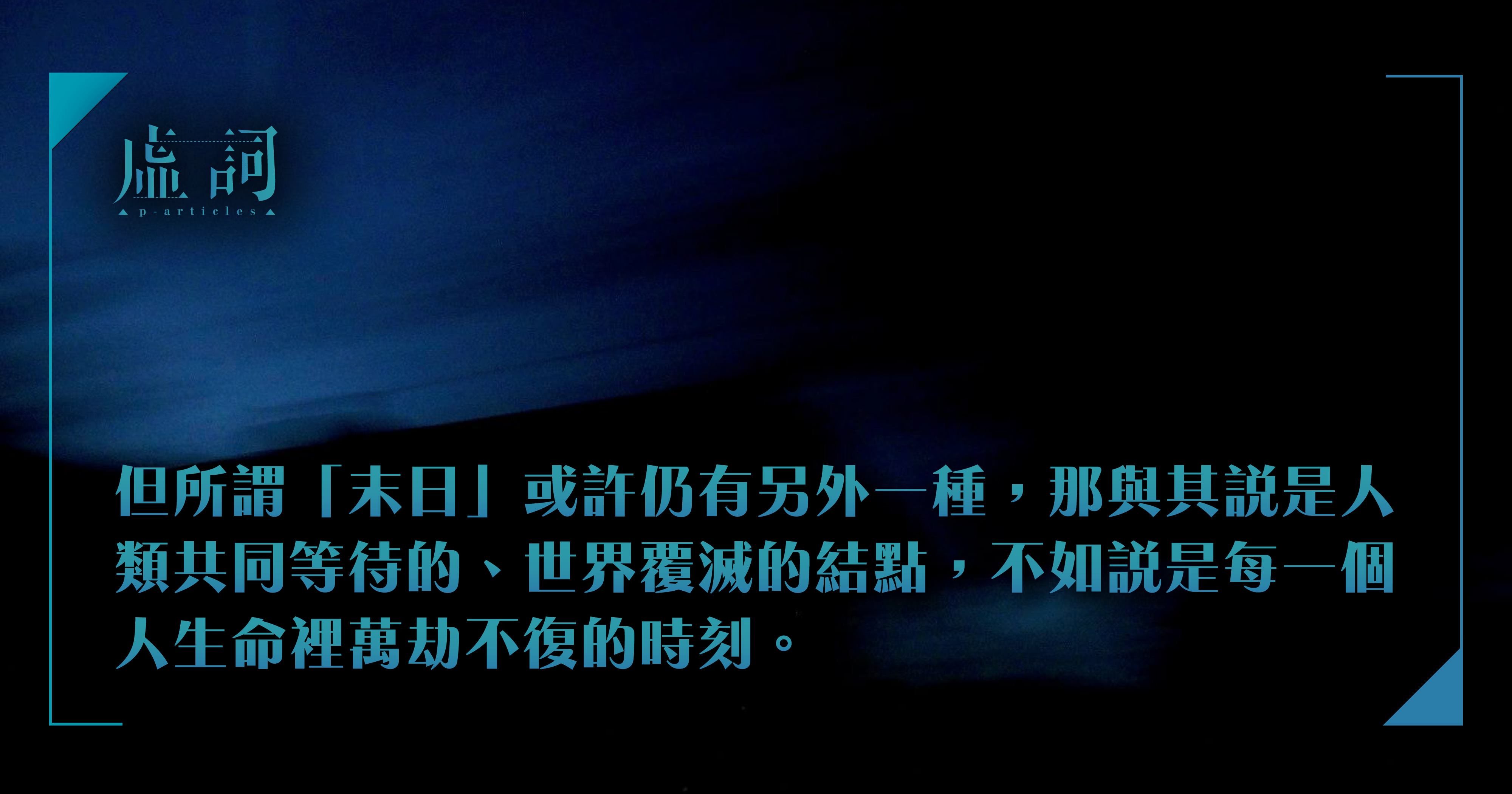【虛詞.說好的世界末日呢?】世界末日:外在的消亡還是抽離的覆滅?
我們對「世界末日」最初的記憶,是來自先知的預言,還是2012年的那場謠言?是盼望中未知的焦急與生出的敬畏,還是「推至眼前」時的恐慌與未定驚魂?
宗教關於末世的描述,常常指向一個未來的時間:彌賽亞再次降臨,世界達至最終時刻(final climax),迎來審判;但這是滅世的時刻,更是救贖的時刻,是「將來世代」的開啟——苦難與邪惡都將消除殆盡,原罪得到淨化,進入神的國度,獲得永生。基督教中,末世是隨時隨地可能發生的個體信仰時刻——耶穌再臨,審判開啟,救贖被看作個體內在的精神性事件。而猶太教與之差別恰恰在於,救贖是一種關於世界與民族的歷史公共性事件。《古蘭經》裡,「信末日」也作為五大信條之一記載其中,成為信徒每日吟誦的禱文。當那日被推向未知的未來,成為感受上帝力量的天啟時刻,這或許又恰恰契合了「盼望」的主題,令「世界末日」這個看起來關乎盡頭的語詞顯得不那麼悲觀、恐慌。那麼,這一時刻何時到來?便也成了終極的提問與等待。
基於將末日視作世界與民族救贖的特徵,馬克思主義勾繪的「無階級社會」曾因其普遍救贖與對資本主義秩序「摧毀滅世」的性格,被班雅明、布洛赫(Ernst Bloch)等人闡釋為世俗的歷史救贖:時間在那一刻徹底終結——此前成為「前歷史」,人類隨後才真正進入「歷史」。只是,在大多數情況下,無論從個體維度還是歷史維度,乃至自然科學的遐想與研究,我們常常以為世界末日是外在的災難時刻,是達至時間的終末、是地球陷入熱寂之時……也因此,我們才彷若「被動」等待,才會發出「末日何時來臨?」的疑問,才焦慮地「惦念」。
但所謂「末日」或許仍有另外一種,那與其說是人類共同等待的、世界覆滅的結點,不如說是每一個人生命裡萬劫不復的時刻;它不似災難片中那個被超級英雄拯救或無力拯救的外部世界,不似小行星擦肩之後再彈回的星球撞擊——世界此後悲情地消亡,它亦可以是主體自願從世界之中抽離的絕望時刻,如星光在夜空裡暗淡、泯滅之際——世界仍在,但只對於他者而言。
就像幾個月以來,那些在暴風雨裡「自覺」隕落的生命,對其而言,哪還等得到神聖文字指向的終結、審判與救贖,甚至再也來不及釐清與思辨「彌賽亞時間」與「末日時間」為何……他們莫不是早已嚴酷地判決了自己那絕望的光景,在這倦怠、冷酷甚至暴虐的社會迎來自己的世界末日。在有限生命的離別之際,他們有幸恍然一瞥「隨時到來」的彌賽亞或超級英雄飛躍而出的幻影嗎?只是,這樣的時刻似乎比先知的預言,更加偶然難料。這難以敬畏,也難以呵責;或許唯有在所有心痛過後,無力地輕聲講句:
我會牽著你手 保護你到最後
直到人類滅亡……
但此刻,也想起《茉莉人生》(Persepolis)裡母親的那句:
“You only have one life. It’s your duty to live it well.”(「唯有此生,你須好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