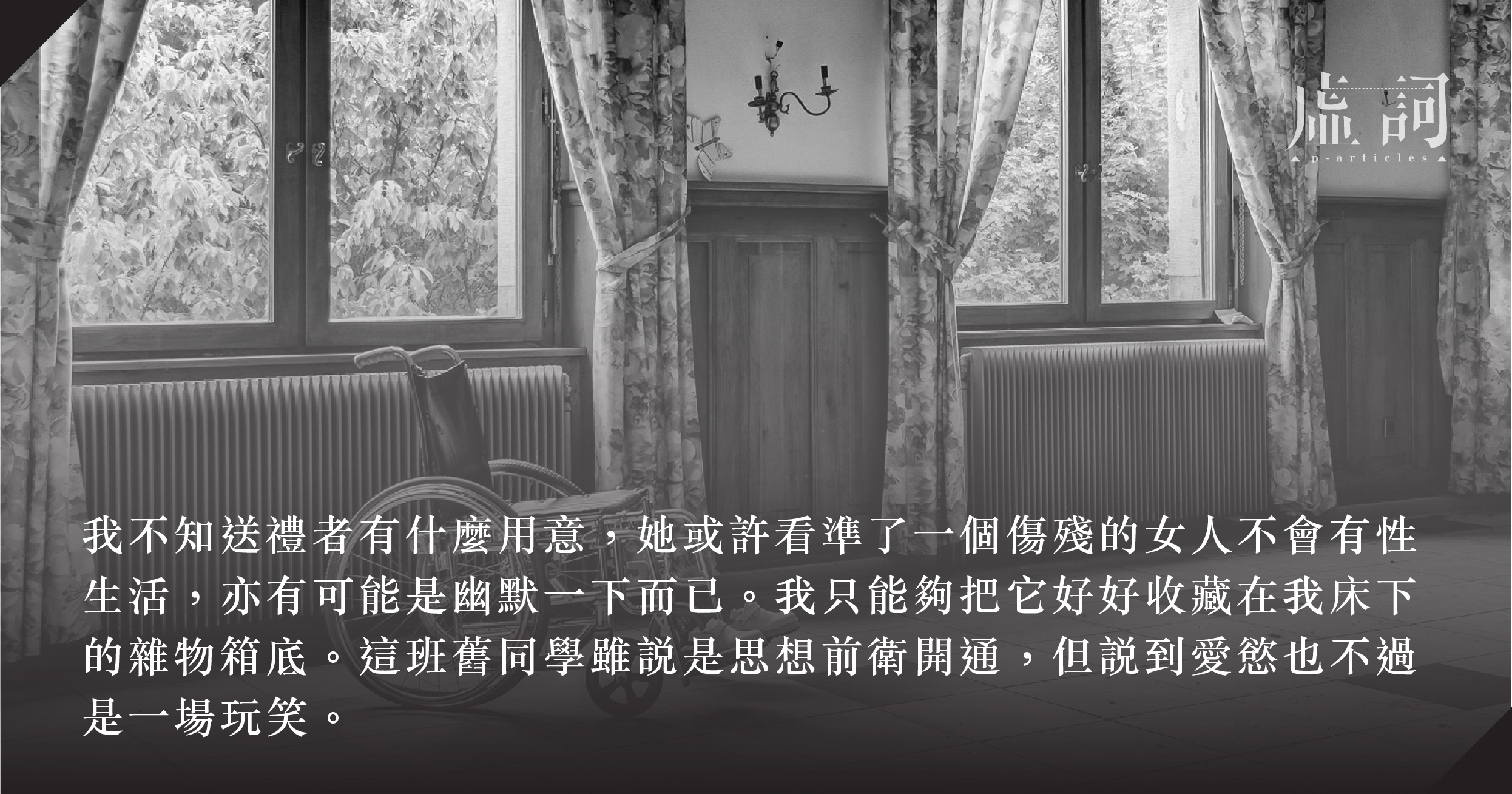輪椅上的聖母
一.
「感覺就像被火燒一樣,猶如在針氈上。這一刻,你會變成了一個氣球,身體不斷地膨脹。那一刻,你又成了一道通了電的管子,一浪接一浪的電流脈衝強而有力地在你體內亂撞。說準一點,身體裏的各個器官都有了各自的意識,都要來造反的,都要來討債的。漸漸你會發現,你失去的不只是身體的控制權,還有你自小培養的理智和人格。一切一切都在眨眼間變得毫不重要......」
他坐在我的面前,正正經經地坐著。
「之後呢?之後又會如何?」我問道。
「之後的晚上我會在床上,在褲子裏撒一泡尿,比平常來得還要腥臭的尿......」他如實回答。
雖然他說話的神情看似十分冷靜,可是言語間倒帶有一點愁緒。他穿著一套端莊純白色恤衫校服,胸口前繡著印有學校標誌的襟章。下身穿著一條灰色長西褲。西褲上沒有他所說的尿漬,而是他的一雙手。我心想他一定是買錯了校服的尺碼。他手臂上的紋理,透過白色的恤衫,若隱若現。也許是因為衣不稱身的關係,他恤衫上左邊的袖口鈕不見了。另一邊的袖口鈕仍在,好好約束住青筋暴現的右手。
「以往,這情況每隔一個月便會出現一次。可是,我現在的情況越來越嚴重。身體越來越不受控制。我快要忍不住了......姑娘,你叫我如何是好?」
他毫無忌諱地帶著問題來找我,表示他對我的信任。本來我應該為此感到慶幸。然而,這一刻的我只可以啞口無言地面對他,茫然地望著他的雙手。他的雙手開始讓我著了迷。他的手掌闊大,可以輕易地同時蓋著另外一個人的口和鼻,控制別人於股掌之間。他每一根的手指又粗又長,像是個同步掌控著五枝鼓棍的爵士樂鼓手。我想,要不是他的缺憾,成為學界中享負盛名的運動健將必然是他的命運。
根據我的經驗,如果手上的個案涉及性而案主是異性的話,最恰當的處理方法就是將個案轉介給異性的同事。就現在的處境來說,這方法是不可行的。機構派來的社工只有我一人。這裏根本沒有男同事可以跟進這個個案。要是我向學校的男老師求助,他們也會以種種的理由來推搪。畢竟這不是他們的份內事。
經過一番考慮,我只能夠這般回應:「我明白,你現在的狀況使你感到很徬徨和焦急。不過,這是十分正常的事。這是成長的必經階段。其實也沒有大不了......」
他像一瓶盛滿了咳藥水的杯子,沉默而且苦惱。他的左手搭著右手上。
「偉賢,如果情況持續的話,我歡迎你再來向我傾訴......」
其實我是有點不肯定的,然而,我要裝著若無其事,慎防我那份疑惑不經意間慘入在言語裡,給他察覺到半點端倪。
我們這次的面談就此結束了。
「我送你回去班房,好嗎?」
我面上掛著一副客氣的笑容,縱使他不能看見,但我相信他是聽得出來的。
他輕鬆地搖了搖頭,說:「學校的路,我都蠻熟了。」說著說著,他把對摺的盲人手杖逐節撐開。他又說:「因為我,要你想去下來,我更不好意思。」
這時候,我的輪椅傳出格格的響聲,彷彿在表示同意。
「下次再說吧,麥姑娘。」
他別過頭去,拿著盲人手杖剔剔撻撻的沿著學校的走廊走去。我在輔導室門前目送他離開,思緒到如絲般的纏。人人都說這年代的青少年大多數都很早熟。性教育課還未上,同學們早已在網上見識了不少。跟偉賢同齡的男孩子,要是遇到相同的困擾也可以自己解決。然而,偉賢天生是個瞎子,一生看不到東西。他的腦海根本對女性的胴體一點印象也沒有。茫然間,最原始的本能在一個年輕無邪的軀體內紮根萌芽。這種突如其來的覺醒打亂了一個小伙子對成長的憧憬。他所說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我都明白。儘管他在走廊的末端消失了,他的說話卻在我腦海裏結繭,堆砌出無數的畫面。
二.
每個星期,我有三天需要到所屬的學校工作。其餘的日子,我便要留在中心裏完成堆積如山的文書工作。我趁著今天要回到中心工作,打算好好跟上司交代那個男生的個案。可是,他的回應也不出我所料。
「由此來看,他的個案沒有大問題,也沒有潛在危機,不需要迫切的介入。有時候,我們也需要給他空間和時間成長......」
說到底,這也不過是人手調配的問題。他說完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說話,情況依舊。這男生的個案還是由我處理。
話末,我的上司順帶一提,說:「你看了那張海報沒有?」
我一臉疑惑地搖頭。
接著,他掛上一副招牌的笑容說:「你的海報已經完成了,都掛在機構大樓的外頭,一定能夠替我們的社區帶來正面的影響!」
大學畢業前,曾經有一位督導私下勸告過我。
「你我都要面對現實。香港是金錢掛帥的社會。社福界也不過是一盤生意。小機構的中心未必有傷健的設施,要他們聘請你也有些難度。另一邊廂,大機構要靠宣傳,擴大他們的服務範疇。你就是他們最好的宣傳工具!」
這位督導口中的社福界和教育界都是黑暗的。他勸告我的時候,他已經半步入退休狀態。至今,我還沒有忘記他的話。
下班的時候,我刻意去留意掛在中心外牆的海報。海報之大蓋過三四層的窗子。我的輪椅佔了海報的四份之三的位置。記得拍攝當日,中心的負責人花了很長的時間跟燈光師爭論。他向燈光師下達了一個指令,把我臉上的光調得脫俗而且親切。那時候,我也替那位燈光師煩惱。到底如何可以將兩者矛盾的東西放在同一張臉上呢?在他們爭論期間,我,在鎂光燈下,不過是一件會笑的商品。對於我在海報中的形象,我不能表達意見,不能參與他們的討論。現在,眼前的結果可算是合乎他的要求。我是坐在輪椅上的聖母,高雅而和藹,純潔且溫柔。這都是拍攝團隊的技倆,替所有人開的一場玩笑。教堂裡的聖母不會笑,而我按中心的要求地微笑。除了我之外,海報上還有好幾個職員的模樣。站在我旁邊的是一位來自青年外展部的男同事阿樂。一如以往,他看來活力十足,笑容燦爛。我跟他的碰面不多於三次。拍攝當日,他和其他的人都沒有出席。這幅大合照都是後期製作的成果。我們頭上頂著具份量的八隻大字:共融社區,由我做起。海報在風中搖擺,扣著海報的鐵鏈噹噹作響。我凝望著比我還要巨大的自己,感覺它隨時也會墮下來,把我重重的壓死。
三.
人們總把聖誕節和愚人節搞亂了,都愛送一些特別的禮物。這些禮物不但沒有用途,而且還教收件者尷尬。也許,這是它唯一的用途。去年聖誕,我和一班舊同學在派對上交換禮物。因為都是社工系的,思想比較開放脫軌,互相交換的垃圾也引來席上一浪一浪的嘻笑。我收到的是一根假陽具。聖誕卡上寫著:「祝願 此生用不著它 註:會電動兼防水。」我不知送禮者有什麼用意,她或許看準了一個傷殘的女人不會有性生活,亦有可能是幽默一下而已。接下來的才是問題。畢竟這是一份禮物。棄之是一種無禮。即使送禮者不介意,但我的心也過意不去。我也不能堂而皇之放在我睡房的書桌上。我只能夠把它好好收藏在我床下的雜物箱底。男人論性是家常。女人討慾是蕩婦。這班舊同學雖說是思想前衛開通,但說到愛慾也不過是一場玩笑。
農曆新年前夕,我和家人趕上年尾的大掃除。因為行動不便,我妹妹替我打掃清潔睡房。那根假陽具突如其來地從床下碌碌滾來。同時面對著它和妹妹,我感到不知所措,神色凝重。當我想到要把那張聖誕卡抽出來,好跟她解釋時,我妹妹識趣地立即用紙巾把它包起來,笑說:「我還以為姊姊沒有這方面的需要......」她同時把它放回雜物箱裡去,又說:「這個我怕你吃不消啊......」說完這話,她便轉身退去了,沒有留下時間給我解釋。後來,我也莫把事情重提。
也許,妹妹是不會明白的。
我妹妹用兩條腿走路,當然比我走得快。她在二十三歲那年結了婚。她的丈夫是一個體育老師。他擁有典型硬漢子的眼神,配上一對濃密的粗眉,雙眼炯炯有神。鼻骨突出,垂直堅挺,撐起了整個人的志氣。薄薄的上唇以上總是剃不乾淨的鬚根。他的出現固然帶給我妹妹不少的幸福。
每一個寧靜的夜裏,妹妹跟妹夫睡在我的鄰房。我習慣深夜時分在睡房裡埋首電腦前,好好整理從公司帶回家的文件。偶爾間鄰房會傳來一把熟悉而陌生的聲音。熟悉,因為那是我妹妹的聲音。陌生,因為我從小也沒有聽過她如此的呻吟。她聲音徘徊於痛苦與快樂之間,不徐不疾,時而豁亮,時而低沈,猶如黃昏時的潮汐不住地拍打乾枯的岸邊。我無可奈何地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關上了燈,打算早點上床入睡。在漆黑中,漠冷冷的棉被下漫著一陣難耐的悶熱。妹妹的叫聲讓我建構出妹夫光溜溜的想像。我的心房劇烈地跳動,一陣昏眩,立刻吸了口氣,從床上撐起身子,推著輪椅,奪門而去。我被迫躲到浴室裡去,好讓自己慢慢冷靜下來。這時候,我留意到旁邊的髒衣籃有一片令人窒息的紅,是一件男裝運動背心,是妹夫的汗衣。我的心跳比剛才來得更急促。窩在體內多年的火龍掙脫一切的捆綁,這時牠在胸口裡失控地膨脹,彼時牠擠上了喉頭,喉嚨變得特別乾涸。我想起了偉賢的話,身體裡忽地多了一個人格。我深知道,當下我抓不著慾念便會被慾念抓著了。我隨即動身,扭開水喉,棒水洗面,抹去兩頰緋紅。水珠從我的面上,沿著我的頸項溜到胸前,滑到肚臍的下方。轉念間,我的指頭趕到下盤的位置,把水珠阻截。隨之而來的是一陣隱藏在空氣中的雄性味道。我漫不經心地把那件鮮豔奪目的紅色運動汗衣捻到掌心。一份莫明的濕潤停留在我的掌心。與此同時,男性荷爾蒙芬香四溢,彌漫著整個浴室。這份誘人的味道完全地包圍著我、支配著我。腦內泛起妹夫精壯的臂彎,又想起阿樂的笑容和偉賢的五根手指。令人難耐的熾熱不知不覺間轉化成溫暖,給我漫長而短暫的安慰。
天花板倏地吐出一滴冰涼的汗水,滴在我的脖子上,一陣寒噤。我看見聖母站在我面前。她在鏡子裡姍姍脫下了衣服,露出兩個豐滿的乳房。她的身後冒出數個男人的身影。在芸芸身影中,我看到妹夫、阿樂和偉賢,他們竟一同享用聖母身上的淫樂。聖母彷彿跟自己的身體分裂,背後伸出一千對手,不斷向男士們招手,同時,祂面無表情、神情泰然的凝望著我。我看得有點心寒,別個頭便鑽回自己的睡房去。雖然妹妹跟妹夫的睡房已經回復了平靜,可是,我的漫漫長夜才剛剛開始。
我沒有想到,跟阿樂的第四次碰面竟然發生在我失眠夜後的早晨,如常地,我們點過頭來,打個招呼便擦肩而過。因為我知道我是一個安分的女人,而且我必須是個安分的女人。
四.
「我以我的子宮為榮!」
聲音十分響亮,響遍整個禮堂。一會兒的寂靜後,接下來是零星的嘲笑聲和此起彼落的交頭接耳。 我知道,我很快便會跟這個女孩子會面。
「我有說錯嗎?我有做到害人的事嗎?」她倒來反問我。
「對我來說,對與錯並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比較關心你為什麼會這樣說話?你有什麼想告訴別人的?」我問道。
美儀是個轉校生。她有一頭時尚的短髮。女生應有的煙視媚行,她通通都沒有。她卻有一股怪脾氣,愛爭辯,愛出頭。好勝心也不小。在校內,沒有男生是跟她過得去的。她曾經跟男同學爭執繼而動武。雖然如此,那些男同學都被打得遍體鱗傷,而她倒是安然無恙。後來,學校便盛傳她是女同志。她深信,造謠者必然是那班給打敗的窩囊廢,為了敗她名聲,好使學校裏的男男女女都怕她。他們的計劃顯然沒有得逞。 因為美儀本是一個獨來獨往的人。於是,有關她的傳言便轉了向,竟說她是平胸女,沒有陰道沒有子宮的怪女人。
「他們說什麼,我也可以。只是拿我的身體來開玩笑便萬萬不能!」美儀咬牙切齒地說。「有什麼比自己的身體更親呢?」
「可是,校方堅持要你在下次週會向大家道歉,不然你會給記過啊…」
「大過,我怕它什麼!況且我有錯嗎?」她越說越激烈,從沙發上站了起來,彷彿在發表女權運動的宣言,說:「麥姑娘,你怎可能不明白身體被人看輕的滋味啊?如果有人在你身體上吐口水,你趕快會用紙巾把它抹乾淨。為何有人侮辱你的身體,你要接受嗎?我又不是賣淫當妓。我只是尊重我身體!我只是捍衛我身體! 」
「我十分尊重你的行為。其實我也很佩服你的勇氣。但我很想知道你這樣做背後的想法是什麼......」
「我的身體也有她的思想,不是讓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材料。男人就能欺負女人嗎?我爸爸是個商人,賺得很多錢,非常能幹,在床上更「能幹」我小時候經已看過他和媽媽在床上做愛。那又如何?我其中的一個男朋友是個名校大學生,不時在算術比賽贏得獎項。那又如何?男男女女,脫下了衣服也不是一塊肉嗎?我要宣示我身體的主權。我的身體價值不應被社會定型。女人的身體是女人的!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相信只要我這樣做那班男生也會無話可說。」
到底美儀的生理還是心理較為早熟些呢?她說的不就是女性主義的思想麼?我也應該支持她的立場嗎?若然我由衷地支持她,那不就是害她走向社會的邊陲嗎?我的思想墮入一片混沌之際,外頭忽然傳來敲門聲。美儀給我眼神示意便自作主張替我開門。門給打開了。門斗裡困著一個男孩子的身影。他手執盲人杖,我知道那是偉賢。
「麥姑娘,我有急事......」他吞吞吐吐地說。或許他察覺到美儀作為第三者的存在。我沒有理由把他拒諸門外,於是,我約了美儀明天再見,待她離開之後,我再請偉賢進來。他臉色彷徨,像一隻受驚的小貓。
「今天你想分享什麼?」我問道。
他猶疑了好一會兒才開腔,說:「那是發生在昨天的事……」他彷彿在說很久以前的事。「 昨天小息的時候,我到男廁小解。有同學把我的手杖搶走…… 接著又有人從後箝制著我......」他停了下來,整個世界都靜止了。我也不敢多說話,默默地等待。片刻之後,他的嘴唇發抖,額上的汗珠滾如大豆,臉上的白皙都漸變得通红了。
「接著他們......他們......摸我的雞雞......」偉賢的眼睛此時流下了點滴的羞辱。他一鼓作氣繼續說:「他們不斷地玩弄我的......之後...我便尿了出來......他們還不肯擺休......還不斷地取笑我......嘲笑我再不是一個處男了......直到他們離開了,我才可以找回我的褲子......」
面對著這種事情果然是困難的,要回應這種事情也不容易。我陪伴著他,看著他起伏不休的胸膛,我的心也在亂跳。一方面,我要按耐著自己的情緒,另一方面我也要冷靜地分析偉賢現在的情況。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你一邊說,我一邊握著你的手,讓你感覺實在一點......」我提出如此的要求後,他沒有說話,只是輕輕地向我伸出手來。我也溫柔地牽著他的手。他的手十分冰冷,還在顫抖。
「之後呢?之後又會如何?」我問道。
「接下來的數天,我也沒有再遇見他們。同學們也沒有說三道四,全校的話題都轉移到美儀身上......只是......」 他欲言又止。
「……自從那天起,我經常會躲在浴室裏……回想起那天的事,回想起他們怎樣玩弄我, 然後……我會照樣地玩弄自己的…」他停了一停,像在試探我的反應般。
「撒一泡尿之後,我的感覺十分平靜。彷彿所有的心願都滿足了一樣。可是,再過不到一天,從前那份難耐又起死回生了,真教教我失控……起初,我還以為終於找到了消滅另一個我的方法…… 我現在才意識到,那不過是不斷不斷的循環......麥姑娘...我怕...我怕有一天我會走到不能自拔的地步.....我現在很辛苦...請你教我怎樣辦......」
「放心吧,這是成長階段的破事兒。不過這些事情,我認為由一個男社工陪伴著你比較適合......」我本應該這樣說的。可是,我把心裡的說話換了換。我說:「我想給你一個擁抱,可以嗎?」我不斷說服自己,這是為了向案主表達我的接納,是為了案主而做的事。只是我說完了這話後,心裡也有多少忐忑。幸好偉賢及時地點頭,使我心安。我把輪椅推到一旁,改用了拐杖,使力把身子撐起來,一陣暈眩,定一定神,我再把外衣脫下。窩在我胸口的關懷正在熱切地翻滾著。碎步蹣跚的我走到偉賢的面前。他仍坐在沙發上。我請他站起身來。
「你靠過來吧,我的手要拿著拐杖。」他放下了盲人杖,小心翼翼地伸出手來。他首先觸碰到的是我的頸,他再溫柔地往下摸索。
「這是我的肩......」
他再往下摸索。
「這是我的手臂......」
他繼續往下摸索。他的手停在我的腰間。
「不用介懷,你想的話,你可以抱著我的腰...」
他深深舒了一口氣,把我緊緊抱著。我也把頭輕輕伏在他的脖子上,以柔軟的胸部好好地感受著他的體溫。他的鼻息凝留在我的肩上。我們分享著一股幼嫩而且澎湃的衝勁。這股衝勁在他的身上擎著,亦同時間在我的身上。我也因此承受著他一起一伏的心跳。
「這不是你的錯......不是你的錯......」
那個下午是我們共同擁有過的糜爛,也是我日記裡的一片書籤。
五.
後來,我的上司終於給他安排了一個男同事,而我也被調職至一所女童院工作。在女童院工作,我必須要在那裡留守過夜。因此,我把大部分的東西都帶進去,週末才會回家一趟。晚上,住在女童院的女生都要按時上床睡覺。整片大地只剩餘蟬鳴聲。三個月後,我再次回到中心時,才得知阿樂經已辭了職。驀然想起來,他的笑容我早已忘記了。往時的舊同學都斷了聯絡。漸漸地,我在她們當中消聲匿跡。女童院的後庭有一個小山丘,那裡安放著一個聖母像。我把所有的記憶和朋友送的那根假陽具好埋藏在聖母像的腳下。我視之為一個新開始。以後,我會教身邊的女生安分守己,也藉此使我自己安分守己。
偶爾間,我仍會記起當時在學校工作時的片段。
我記得,我在那裡工作的最後一天,我迷迷惘惘地依在輔導室的窗邊。窗外一根枯枝上立著一隻仰天眺望的麻雀。聽說,麻雀總是養不活,把牠硬關在籠子裡也會咬舌自盡。想到這裡,我彷彿變成了一隻野貓,打算向那隻麻雀撲去,把牠捕捉,好關在籠子裡,替這個說法作個求證,要看看牠是否真的如此愛自由。驀地,美儀的身影打斷了我的思路。她的身影出現在窗外的山坡斜路上。在她身旁的是一個穿著鄰近學校校服的男生。那間學校校風比較差。男生也把校服穿得衣衫襤褸,大搖大擺地走路。他們口裡各叼著一根香煙。兩人忽然停下了腳步,旁若無人地在街上擁吻。我想走近一點,把事情看得更清楚。可是,輪椅的鐵枝經已頂著牆邊,讓我無法再靠近。我似個偷窺狂遠遠監視著她。美儀的雙眼輕閉著,沉醉於醉生夢死之中。我看得兩頰發燒。他倆熱吻過後,繼續牽手上路。我從來沒有深究這條路會通向哪裏,也沒有走上這條路的打算。
我相信,這些可恥的年華終有一天會在塵土中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