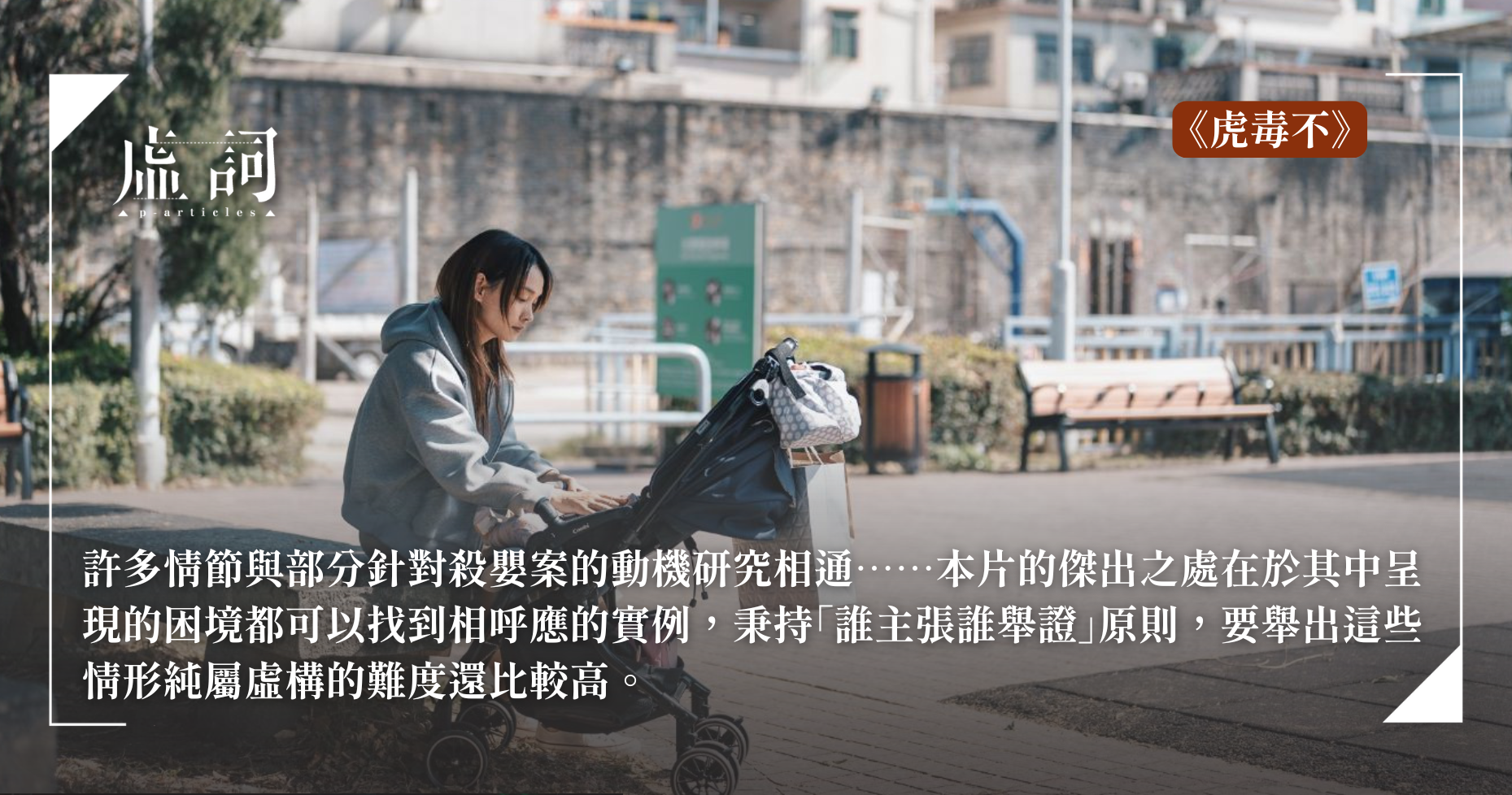淑貞產後怎樣——從《虎毒不》向眾人致意
影評 | by 杜惕若 | 2025-05-06
在進入影評前,讓我們先從一個社會現象提起——殺兒。在昭和後期的日本,國家進入和平年代,經濟奇跡擴大國民收入,似乎社會也會隨經濟復甦而改善。但偏偏在1970年,日本一年內出現近四百宗殺兒案,到1974年更達到一年六百宗的高峯。(1)一時間新聞鋪天蓋地將罪責歸咎於母親缺乏母性,就算殺兒兇手是父親也會責怪母親沒有留在家好好照顧孩子,試圖將殺兒打造成女性離經叛道的不自然行為。(2)
當時的主流社會輿論不能理解,為何他們眼中的「賢妻良母」要殺害親生孩兒,正應了我們熟知的那句話:虎毒不吃兒。
但即使放在香港,殺嬰案(infanticide)也是屢見不鮮。1981年香港立法局已在《侵害人身條例》加入殺嬰罪(47C),將「該女子仍因未從分娩該嬰兒的影響中完全復原,或因分娩該嬰兒後泌乳的影響,而致精神不平衡」的情況納入考慮。香港從2008到2013年間有三十五宗殺兒(filicide)的案例,近兩年每年也有少量案例。(3)即使案例數量不如七〇年代的日本極端,但毫無疑問也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
我要叩問的是,即使目前香港殺嬰案為數不多,那但冰山一角的海面下到底潛藏甚麼因素導致悲劇的出現?這問題與近期上畫的電影《虎毒不》(陳小娟執導,2024)密切相關,尤其當部分觀眾質疑電影導演「虛構、營造與盲目聚焦於新手母親的困境、失去選擇、陷入情緒抑鬱的情況」(4),我必須反駁電影呈現的困境全都可以找到實例佐證,其紀實性(documentary)毋庸置疑,反而是虛構不夠、結局亦不夠開放,導致劇中角色無可避免地走向絕路,削弱了電影在藝術及社會控訴上的能力,觀眾在觀影後即使能了解母職的煎熬,但「What’s next? What is to be done?」的問題要向誰發問、我們又應該對誰懷有更多期望,諸如此類的問題留給了觀眾自行省思,只好讓一位挑剔的觀眾留下意見,拋磚引玉。
「現代母職的拼貼」:反映現實?主觀拼貼?
《虎毒不》的電影標題來自前文提及的俚語「虎毒不吃兒」,標題將「吃兒」二字刪除,讓電影更像是在問:「虎毒不?」老虎吃兒真是因為她心腸歹毒嗎?套用陳導的話則是:「就連兇殘的老虎都不會吃牠們的子女,為何十月懷胎、辛苦照料孩子的媽媽卻會走到這一步?」(5)
但相比電影中文片名,其英文片名「Montages of a Modern Motherhood」更有意思。
Montages指拼貼,我認為可以分兩個層面來分析。其一是電影內部,主角淑貞(談善言飾)在經歷產後婆媳爭端、失業及求職困難、托兒無望、產前後生理變化及育兒要求等等刺激,從她為出發點將所有痛苦及挫敗串聯。這些困難不必然是客觀時間上接二連三爆發,但從淑貞的主觀認知上,這些挫敗仿如連綿雨深刻地打在她身上。電影這種媒介的魅力正在於將主觀時間如實呈現——我的孩子不夠磅,我又泵不出奶,又有家婆冷嘲熱諷,又有老公任由我喪偶式育兒,又因分娩而沒了工作……淑貞的悲劇不在於某一件事,而在於「又」;她的痛苦不單是在某件事受挫,而是「BB又喊了」、「又沒辦法做到所謂的一百分媽媽」,這樣的日子沒有盡頭,絕望油然而生。
另一層面是電影外部,電影創作者對於現代母職的困難拼貼在一部電影內,讓淑貞一個角色承受各種劫難。或有評論者質疑導演藉此「虛構困境」,但本片中許多困境其實都能找到實例印證,近年的新聞也有報道最終促成的悲劇,我留待下部分引證。但我反過來要問,本片拼貼了甚麼?本片可以清楚見到新手媽媽擔任母職的無助、彷徨、掙扎、痛苦、挫敗、怨念、疲倦、自責、絕望,但淑貞的憤怒有沒有充分體現?全片中淑貞少數的控訴在於與丈夫阿偉(盧鎮業飾)的爭執(還沒吵贏),或許這種安排是為了營造當事人的絕望?
電影涉及影音的拼貼,而選擇甚麼拼貼、要怎樣拼貼則屬主觀範疇。目前《虎毒不》的拼貼只聚焦在「現代母職」當中新手媽媽的產後困境,但此外隨着孩子長大的母職就較少提及,只由幫忙照顧嬰兒的芬姨(馮素波飾)及安慰女兒的貞媽(區嘉雯飾)來淺淺提及。陳導想讓觀眾沉浸式體驗新手媽媽產後的絕望,但這種絕望完全依賴紀實事例的拼貼來營造則顯得單調。
同樣將鏡頭對準母親角色的電影不在少數,《82年生的金智英》(82년생 김지영,趙南柱原著,金度英執導,2019)的主角金智英突然以她母親的口吻說話,向家婆提出讓自己節日可以回娘家。又或是《母親》(마더,奉俊浩執導,2009)開頭的母親在稻穗中擺盪雙手獨舞,結局用針刺在大腿上負責記憶的穴位,讓自己忘掉創傷,跟隨旅遊車上的婦女一起跳舞。
雖是虛構,但也合乎情理,魔幻當中有現實,誰能說這些虛構的片段不是指向更深層次的真實?要做夢才能活下去,豈不絕望?《母親》當中也有毒死兒子的回憶,只是最後失敗了,因而在餘生中盡更大的努力保護兒子以求贖罪,形成悲劇。也許《虎毒不》中的淑貞在電影結束後若「僥倖」獲救,屆時的絕望恐怕比目前電影的處理更加絕望。不論要加強絕望還是在不能寸進的絕望盡頭重拾希望,都需要創作者的主觀介入,這是我所認為本片不夠主觀、不夠虛構的緣由。
「淑貞產後怎樣?」:戲內外的女性困境
「淑」指美好善良,通常配詞用在女性身上,如「淑女」、「賢淑」;「貞」有占卜之意,但常用在指女性不失身、不改嫁,嚴守男性眼中的「女性正道」。淑貞作為現代母職的拼貼物,其名字也帶有隱喻的枷鎖,似是老爺(太保飾)把玩的籠中鳥,自我埋葬的結局早有暗示。
淑貞一出場,首先讓我驚詫的是電影的服化道。我上個月曾參加我表侄的百日宴,宴會上見到孩子的母親就像淑貞那樣憔悴、疲倦。片中還有一幕是在鏡子前的淑貞,當她看着自己產後的身體變化,那被丈夫笑話的身體留下深刻的印記及疤痕,她會否也生起身材焦慮?她會否覺得這副身體不像自己的?淑貞不語,我們看着鏡頭中的她,她看着鏡中的自己,一副軀體,兩處無言。
電影中略過了不少懷孕及分娩期間準媽媽會遇到的困難,將重心放在產後,淑貞本已想到養育小孩會很辛苦,但沒料到痛苦遠超想象。
淑貞要求自己要做「一百分的媽媽」,她為嬰兒過輕而焦慮還被家婆責怪,泵奶時乳腺炎,擔心自己不夠奶而向WhatsApp媽媽群組求助,還見到其他媽媽家裏還剩幾瓶奶,自己辛苦泵出的奶卻因嬰兒一時喝不完而被家婆倒掉,當嬰兒半夜哭喊時丈夫只顧着睡,而她卻因鄰居投訴而抱女兒到樓下四下無人處安撫。
上述許多情節與部分針對殺嬰案的動機研究相通,其中「患產後抑鬱的母親對於跟上社會對『好媽媽/好太太』的標準方面有深刻的失敗感,為嬰兒的健康幸福而憂懼,或為自己照顧嬰兒的能力焦慮或質疑。」(6)而嬰兒過輕而強迫自己長時間餵奶、抱孩子落樓避免滋擾,求助無門的情況更與2022年3月一宗殺嬰案極其類似(為免激起事主情緒在此略去細節)。本片的傑出之處在於其中呈現的困境都可以找到相呼應的實例,秉持「誰主張誰舉證」原則,要舉出這些情形純屬虛構的難度還比較高(至於針對不留希望的拼貼則是比較容易成理的批評)。
嬰兒的哭聲也是媽媽產後的噩夢。在《虎毒不》的謝票場上一位七十幾歲的母親憶述:「套戲好似講緊我自己,我個仔又係由頭到尾都係喊,所以個喊聲回憶起好恐怖㗎。你喊個幾分鐘,我係唔知喊咗幾多年呀。」她經歷家婆燒溪錢,餵符水,丈夫一聽喊聲就掉頭走,一見到要換尿片就喚她自己處理,「越睇就越覺得講緊我自己咁。」(7)
片中淑貞找不到托兒服務也符合香港現況。香港在2021-22年度平均每四十個幼兒爭一個位,片中淑貞身處的元朗區的服務名額與幼兒比例達1:78,其中最嚴重的大埔區更達1:271,既患寡也患不均。(8)雖說社會福利署也能分擔托兒服務,但2022年當立法會詢問勞工及福利局托兒服務申請人數時,局方回應「社署沒有備存申請人數、家長重投職場的人數及收入平均數的資料」。(9)
片中美中不足或許是對於淑貞做母親前自己的人生期望沒有足夠篇幅交代,僅僅透過淑貞做麪包、整蛋撻給芬姨、跟姐妹閒聊時提起想開麪包店,丈夫「畫餅」將來給錢淑貞開店做老闆娘。但究竟淑貞為甚麼願意投放十多年做麪包?她的職涯願望是甚麼?她做女時是怎麼想象將來?這些問題指向更核心的大問題——如果不生兒育女,她的人生會是怎樣?
「是誰來自山川湖海 卻囿於晝夜廚房與愛」——萬能青年旅店〈揪心的玩笑與漫長的白日夢〉。
電影還可以深挖的地方還有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經濟模式,當代工作人口過勞,但投身職場的女性回家後多要負責家事勞動。而女性暫別職場的時間越長,重返職場的困難就越大。魯迅曉得說娜拉走後只能墮落或回家皆因沒有經濟權,但當許廣平多次爭取自己要有正當職業時卻換來魯迅反對:「你做事這些薪金,要辛苦一個月,看人家面孔,我兩篇文章就收來了,你還是在家裏不要出去,幫幫我,讓我寫文章罷。」(10)
一百年後,淑貞產後怎樣?失業(片中老闆應已違反《僱傭條例》第III部的「生育保障」,但就怕淑貞沒簽約)、求職困難、家用不夠也要看丈夫面口。一百年了,我們的社會及兩性關係儘管有了不少進步,但當阿偉說淑貞出去工作也找不到那麼多錢時,從政府統計署的數據也明顯可見兩性就業人口的月入中位數差距有所擴大(從2022年相差五千七百元到2024年相差七千元),許廣平也還在期待着。(11)
我暫且說回電影本身吧。
絕望以外:結局足夠開放嗎?
陳導稱本來安排淑貞結局沒死,要上法庭自白,最後從較黑暗的結局改為開放式結局。但電影文本本身也沒太多線索可以支撐淑貞自殺殺嬰以外的結局。電影中在淑貞抱着嬰兒在湖邊,之後是嬰兒奶嘴及淑貞拖鞋在湖邊的空鏡,最後是回到懷孕時對嬰兒的期望。電影與其說是「開放式結局」毋寧說是「暗示式結局」。
淑貞走上絕路是電影不斷累積鋪排的結果。她嘗試過自救——她找過芬姨幫手托兒,但後者因移民而無能為力。她試過讓自己母親來幫自己,但哥哥的孩子也需要幫忙養,就算淑貞已經跟丈夫提出過搬近母親家來讓母親幫忙撫養,卻遭到「孝順父母」的丈夫拒絕搬離要行樓梯上落的家。她試過找工作,甚至訛稱自己沒有孩子,結果也沒有願意聘請她的老闆。一次次自救換來一次次希望幻滅。
電影中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丈夫久違地帶她到海邊散步,本來溫馨浪漫的場景卻聽見丈夫說男孩也挺不錯,讓妻子再生一個男嬰(「孝順仔」應是聽了家婆要湊個「好」字),之後「安心」在家湊仔,他存到錢就讓她去開店做老闆娘。儘管她在片中和丈夫試了六年才迎來孩子,但要是分娩的痛苦不受重視、產後育兒不成比例地壓在她身上,生育就是她無底洞的絕望。
孝順仔沒說的是,如果第二胎不是仔呢?還要生嗎?實在不堪細想。在我母親那一輩當中有生到第四胎才得到兒子的親戚(電視劇《娘道》一般的劇場真實上演),但願我們這一代(尤其是男士們)在面對這種落後思想時必定要反抗到底,任何時候女性的意願都必須排在首位,生育必須自主,讓生兒育女一切隨緣。
淑貞的絕望有太多因素導致,在導演的拼貼下更是非死不可。但要是一個真的開放式結局(死或不死都能成立)會是怎樣?我試着構想:
淑貞在鏡頭中間一步步走入湖中(鏡頭跟隨淑貞背影讓她一直置中),水位一點點到她的腰,在就要淹到嬰兒的時刻,淑貞又聽到手中嬰孩的哭聲,是那令母親無法入眠的哭聲,也是嬰兒來到這世上的第一聲吶喊。她停下來——是要回頭嗎?還是怒從心來直接將嬰孩淹進湖中?我們不得而知。也許在絕望無力當中,她再一次哭了。無論怎樣選擇,淑貞都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是生是死,也是時候好好休息。
面對殺兒潮時,日本女性解放運動(ウーマン・リブ)新宿中心的成員米津知子如此說:「雖然我們認同殺兒是錯的,但我們不想責怪一個母親,反而要責怪的是允許和延續這社會的我。」(12)
「解決它,不全是女性本身,在男性,在社會問題上,我以為都有關係。」(許廣平語)(13)
「偉大的」甚麼?
偉大雖然指高超盛大、正面影響深遠,但為何一想到偉大,我卻只聯想到犧牲?當我們複述着「母親真偉大」時,我們究竟想到甚麼?是那眠乾睡濕的身影?是放棄自己前途而甘心做一個家庭主婦的遺憾?是看不到山川湖海的廚房窗花?我們到底要讚頌甚麼?電影要向誰致意?
當終於有天《虎毒不》變得「只反映某時代的現實」,沒有任何人想到「這部電影就像我的故事」,到其時我們想必已經習慣稱讚——
收工後一同照顧孩子、打掃家務、調節婆媳糾紛的那位「偉大的父親」;
樂意聆聽家嫂產前後憂慮、不批評也不給壓力、不要求子女一定要生仔的那位「偉大的奶奶」;
退休後不倚老賣老、配合子女分擔家庭職務的那位「偉大的老爺」;
體諒需要侍產假和產假的員工,極力調節各員工的工作量而不加刁難的那位「偉大的老闆」;
不冷嘲熱潮、即使不打算生兒育女,但仍會跟計劃生兒育女的人保持聯繫的那個「偉大的陌生人」(我也為你祝福!)。
該不會有那麼科幻的一天,進化的錯誤得到修正,產房傳出雄壯的呼喊聲,門外的實習護士低聲發出歷史性的稱讚:「爸爸真偉大!」
母親!在眾人終於承擔起眾人之事,你從悶熱的廚房和滲人的產房大步走出,不期然對我說起工作中的煩惱,疲倦透露着滿足,你沒有顧慮的笑容中有偉大的真意:你快樂,我也快樂。
致所有人。
- 田間泰子,《母性愛という制度: 子殺しと中絶のポリティクス》(東京:勁草書房,2001),頁71-104,數據轉引自Setsu Shigematsu, Scream from the Shadows: The Women’s Liberation Movement in Jap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23, 207。
- Shigematsu, Scream from the Shadows, 81.
- Dr Dorothy Tang and Dr Bonnie Siu, “Maternal Infanticide and Filicide in a Psychiatric Custodial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East Asian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8, no. 4 (2018): 139-143。
- 莫匡堯,「虎毒不︱評價兩極男觀眾狠批三大問題 女網民:唔恐怖只係好寫實」,香港01,2025年4月25日,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23244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鍾卓言,「陳小娟談善言同理心詮釋 《虎毒不》攤開母親的掙扎」,明報新聞網,2025年4月25日,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250425/s00005/1745511956154。
- Tang and Siu, “Maternal Infanticide and Filicide in a Psychiatric Custodial Institution in Hong Kong,” 140.
- 「【觀眾感動分享】」,goldenscenehk,2025年5月4日https://www.instagram.com/p/DJPLUkHBXQg/。
- 數因斯坦,「托兒短缺|港幼兒中心0-2歲照顧服務嚴重不足 40個BB爭1個托兒位」,香港01,2023年6月27日,https://www.hk01.com/article/909557?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 「立法會十九題:託兒服務」,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公報,2022年11月30日,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211/30/P2022113000218.htm。
- 景宋(許廣平),〈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魯迅風》,第10期,頁6。
- 歡迎自行查閱,數據來自「表210-06314:按年齡及性別劃分的就業人士每月就業收入中位數」,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統計署,發布於2025年4月22日,https://www.censtatd.gov.hk/tc/web_table.html?id=210-06314#。
- 轉譯自Shigematsu, Scream from the Shadows, 24, 207.
- 景宋,〈從女性的立場說「新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