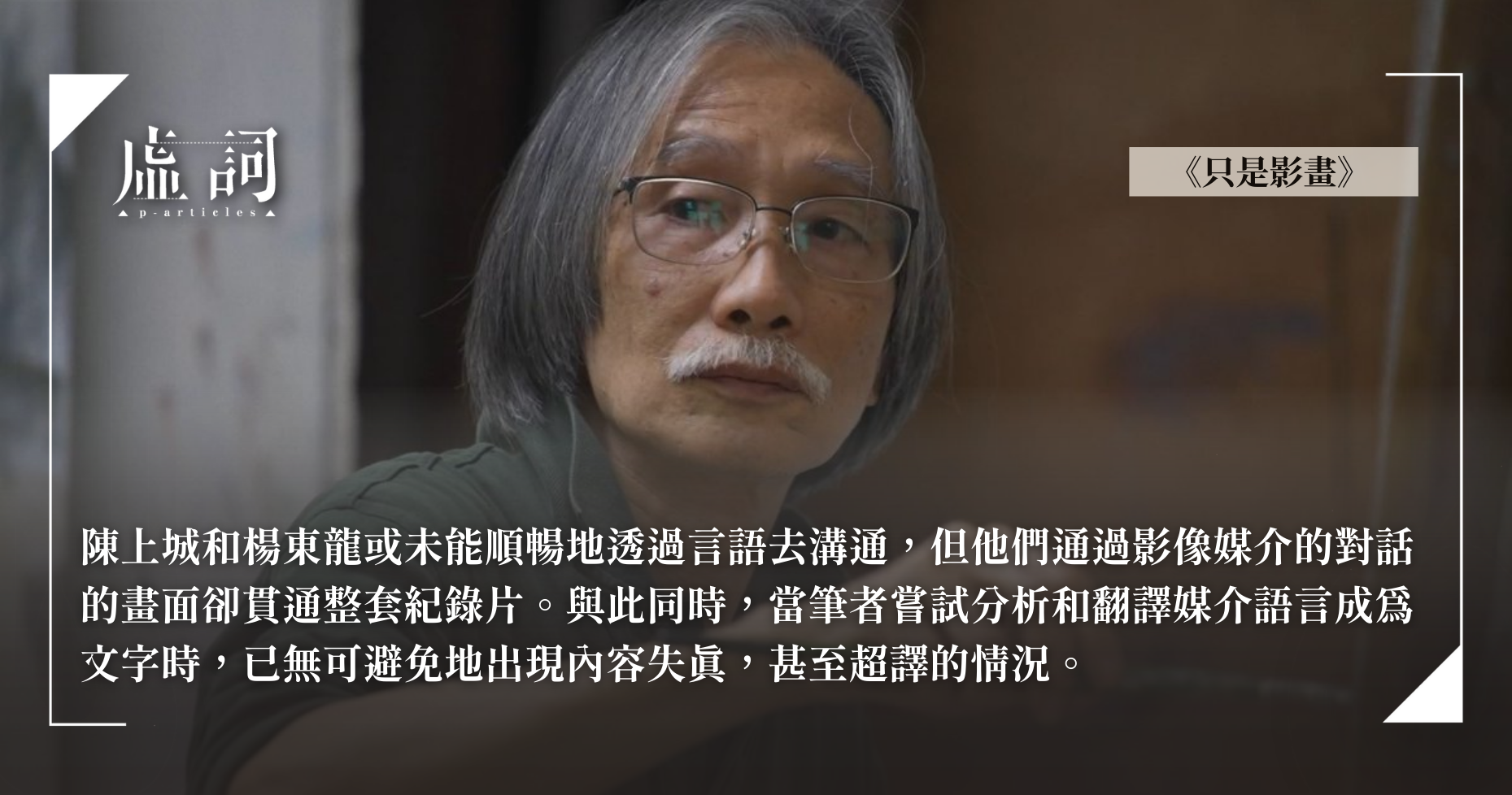《只是影畫》的溝通與失效
影評 | by 搬金字塔的螞蟻 | 2024-09-27
每一種創作媒介都有其自身的一套語言,在其各自領域流通及溝通。這些貫通其自身媒介的語言本來是甚少相通,但若要把他們相連,甚且可被大眾理解的話,需要經過一次或多次的翻譯,並透過大眾的普遍語言——文字去解說和使其成為知識或可用作日常溝通的(新)語言。媒介語言翻譯成文字語言,文字語言之間亦需再翻譯。惟,翻譯期間亦會因地域文化或語言自身的局限性而出現失真或超譯的情況 [1][2]。
藝術和創作本身是難以透過文字去理解的,我們可以利用文字去描述作品的外觀或構圖,或閱讀藝術家的生平和創作自述等背景資料,透過某個切入點去理解作品,但我們無法透過文字去傳遞作品蘊含的意境和氣韻。筆者猜想這是楊東龍在《只是影畫》中說的「如果可以用語言說出來,就不用畫畫了。」和他不喜歡解畫的其中一個原故,另一個原因或許是他的寡言所致。
言語的失效
若觀眾能夠理解文字和影像是兩個語言系統,而東龍是一個不會用文字去解釋畫作和其創作思維的人的話,那麼,觀眾便能知道《只是影畫》並非一套可從訪談內容去了解楊東龍本人的電影。
事實上,《只是影畫》亦出現了大量問了但沒有答案的畫面。上城導演多次提問東龍對於創作和藝術的看法,但東龍均以正在畫畫而避談,或反問用字意思。前者或許如東龍所說的,他不可一心二用,亦或許是他的言語未能把其圖像思維即時翻譯成線性文字,所以未能回答問題;但筆者並不認為後者是避談的一種方式,反而是界定用字意思以便進行深入討論的一種回應。惟電影中未見後續對答內容,未知是拍攝團體未曾考慮過字詞的模糊性,或是討論未有納入電影中,否則觀眾便可一窺東龍的思維世界了……東龍的避而不談和上城的模糊用字顯示了他們的思維領域不同導致言語溝通失效。
語言的溝通
無效的言語溝通在電影中頻頻出現,但他們卻都各自利用了影像媒介去對話。《只是影畫》的早段是一些香港地景的空鏡,例如:過海行車路線的風景、大廈林立、街上行人的生活面貌等,都是東龍大部分畫作的繪畫對象。電影開首的空鏡一般是用作提供背景資料和為氣氛節奏定調,而《只》同時亦是在模仿東龍一邊漫步一邊觀察周遭的日常活動。其後電影出現了兩個「分割畫面」,都是鏡頭在室外,拍攝着室內的東龍,一旁的窗戶反光影照出室外遊人行車。這個室內外景象併攝的「分割畫面」跟東龍大部分畫作的構圖異曲同工。地景空鏡後插入「分割畫面」,亦如東龍觀察日常後把途人拼貼併置在同一畫作內的創作模式。
然而,兩者的畫面存在着差異。東龍的創作是從草圖開始,先設計和描繪人物姿態,然後人物與空間及時間的互動。這個剪接拼貼由想像而起,或沒有真實的場景和人物動作可被回溯,是虛構之人、架空之地。東龍繪畫的並非一瞬的情景,而是日常觀察後消化出的想像與記憶。而上城的分割畫面是他經過細微地觀察東龍的日常生活和空間的片段,是基於現實環境和真實行為的。上城的畫面亦具時間性,除了用於觀察和發現場景所用的日晨,窗戶反光拍攝到光線反映了時間(早上)和天氣(晴天)、緩慢行駛的的士和輕輕飄搖的樹葉亦反映了時間的流動。這些差異是基於媒介自身擁有的特色(靜止或流動),亦是畫家和導演各運用和介入媒介(拼貼或紀錄)的結果,但亦無礙上城導演利用鏡頭和蒙太奇等電影語言去回應東龍和藝術的意圖和成果。
上城利用言語和影像積極地向東龍發出訊息,東龍亦有透過影像去作出回應。在上城播放初剪片段並詢問其公映意願後,東龍提出需要時間考慮,其後向上城寄出了一些影片。東龍對公開放映的顧慮在於影片將呈現真實的他,但亦可能只可反映出他的某中一些性格切面,亦認為影片過於保守。東龍隨後在片段中把鏡頭向着自己,然後自轉一周,這彷彿是一種邀請和允許,讓其繼續拍攝他的周遭和他與周遭事物的關係。
關係於人物紀錄片而言猶其重要,導演與被拍攝者建立怎樣的關係會直接影響拍攝方向和公映意願,從《水底行走的人》(2017)中的關係和角色的角力及缺席和《給十九歲的我》(2022)的爭議中便可窺視一二。作為紀錄片導演的上城處理與各人關係的能力不容少覷,他們行山時的互相提醒及惠問、長時間而融洽的討論氣氛、容納共識及感受的溝通空間等,都顯示了他與拍攝團隊及和東龍的關係均不錯,平等而親近。當東龍拿起手機,利用影像媒介去拍攝自身與環境的時侯,這允許了繼續建立關係的意願,顯示了他對上城的信任,亦是肯定了上城是《只是影畫》的導演的角色。
縱使在《只是影畫》中,上城和東龍或未能順暢地透過言語去溝通,但他們通過影像媒介的對話的畫面卻貫通整套紀錄片。跨媒介的對話稀少而釐珍。這樣的回應相較於利用言語說出的「好」或「我相信你」來得含蓄和模糊,但卻更見當中的決意和信念。與此同時,當筆者嘗試分析和翻譯媒介語言成為文字時,便已無可避免地出現內容失真,甚至超譯的情況。
參考資料︰
[1] Steiner, George. “A Secondary City” in Real Presenc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2] 以電影為例,徐克的《蝶變》(1979)或《英雄本色》(1986)都在描述江湖。然而,「江湖」可有盛載到電影的意境?若「江湖」的英文譯成「Underworld」或「Brotherhood」,當中失去了俠義和風塵滾滾的感覺,而香港電影資料館的用詞是「Jianghu」,即是「江湖」的國語拼音。無論是「江湖」、「Underworld」、「Brotherhood」或「Jianghu」,其實都沒有完全地映照出電影中的意境和畫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