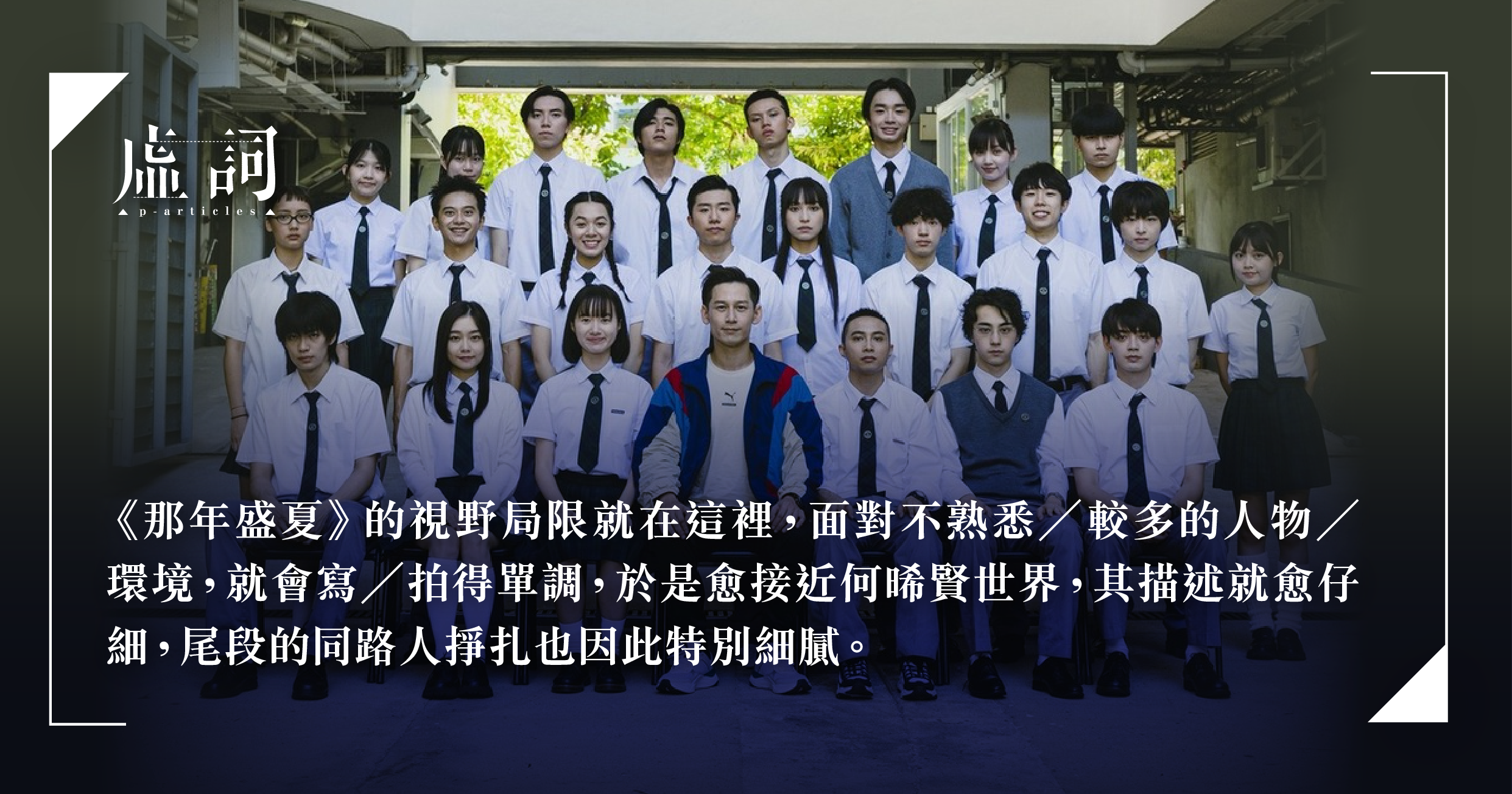《那年盛夏我們綻放如花》從校園到社會的連結與盲點
劇評 | by 查柏朗 | 2023-10-03
美學所追求之「美」除了表現風格、敘事結構等作品內部自足的成分,也尋求真實、真理的價值所在,於是《那年盛夏》的內核必須被檢驗,其說了甚麼,以及怎樣去說,兩者是否有機地連結,其選擇是否有效、貼切的方式。針對上篇提及過的幾項創作特色:校園到社會的兩層主題、「復古未來」的美術策略、群體演出的指導、人物對照的鮮明,在此脈絡下再一一討論。
(以下內容含有劇透)
「請你不要遺下我,請你不要忘掉我」
何晞賢 / 何肇康的原作一大高明之處,乃從其標題,到每日不斷重覆的遊戲規則,已揭露找尋目標人物、群組起源的關鍵線索。已讀不回的三十分鐘時限、發訊息給死者亦需死亡,對應著羅彥輝自殺前收不到朋友回覆的絕望階段,沒有得到及時回覆,或死後才收到回覆,同樣無法挽回悲劇。退出群組就死亡,某程度上也反映當時羅彥輝需要退學,自覺輸掉的心態,在劇集中以一句大意為「錯嘅唔係我,走嘅點解要係我」來點出。
當這情節忠實地改編成第12集時,竟引起了網絡上情緒反彈的聲音,跟連載時一面倒對佈局精彩的肯定,可算天淵之別。質疑的聲音不外乎「欺負人的始作俑者不去針對,反而跟你選擇做朋友,嘗試溝通及幫忙,竟然成為目標」,而解惑的答案就同時通往本作的兩大題旨:一. 社會管治倚靠科技運算的危險:人工智能 (AI) 不可靠,模擬不到人類思考與感受的複雜,只簡單看到先後次序並將其因果連結:四人沒有回覆羅彥輝,然後羅彥輝自殺身亡,於是這四人要負上責任;二. 怎樣面對校園欺凌。受害者對欺凌者沒有期望,卻對身邊關心自己的人有著情感依附,並很容易就感受到被背叛而絕望。惡人繼續行惡,符合其預定人設;但旁觀的他人是否可多走一步,去展現世間尚有善的一面,去給予希望的曙光?然而一旦不能持續,當僅有微弱的光芒都是虛假,才是最難接受。
第二點的大眾觀感見證了《已讀不回死全家》到《那年盛夏》的社會集體心路轉變。當角色說出「錯嘅唔係我,走嘅點解要係我」這句台詞時,觀眾所連結到的心情,從個別的欺凌行為,延伸到日常所感受到的壓制與無力。從而作品的兩個面向重合:學校作為社會的縮影,校內單獨個案的肢體暴力、體制失效,就延展到社會層面,在虛構世界內以MTCC作為代指。
《那年盛夏》比《已讀不回死全家》更進一步提示觀眾將兩者連繫,在於提早讓MTCC登場(先拍何晞賢街上照鏡,再到校內操場與課室皆見其配置,顯示其鋪天蓋地;後來以豪為首的黑衣團隊進入學校,在原有群組爆頭對學生所造成的不安驚恐外,再注入一層陌生成年人介入、卻顯然並非幫助學生的恐怖,也以最後一袋袋的黑色被拋到地下的音效所突顯)。他們盤問Karman,致使其說出群組由來而死亡,除了給觀眾對於該規則留下更深刻印象外,更表現了這群人的威脅,不低於其群組內的遊戲。到該集完場前,群組管理員 (admin)感謝楊悅盈後「完善」規則,雖在原作是一樣的安排,劇集將此動作放到第一集的結尾,卻多了一重預示作用,就是引入之後不斷增添原作所沒有的「特別任務」。
掌控權力者嘗試隱瞞真相的程度更肆無忌憚、規模更廣;admin 逼害學生的花樣增多、新增以何晞媛牽引的記者線亦將逼害對象從無權者、年輕人擴展到異議者。到全劇最後一鏡,楊悅盈拿起電話找何晞賢,不論其拍攝角度及情節安排,刻意與羅彥輝死前找楊悅盈的如出一轍,就完成了這塊鏡像:微觀的校園欺凌、宏觀的強權壓迫。
當讀者在2017年發現目標人物原來不是直接傷害人的一方,而是沒法及時回應受欺壓的一方時,乃2014、2016之後的沉澱,帶著「我們是否有能力做到更多」、「若我們更團結,結果是否可以不一樣」、「中立不表態不行動者比對家更可惡」的想法。到遭逢時局巨變的2023年,劇集詳細交代了楊悅盈鼓勵羅彥輝循制度伸張正義(向老師舉報),卻徒勞無功,甚至被逼害程度加劇,賴智勇繼續積極建議亦換來冷待,而且我們都知悉楊悅盈及賴智勇皆是被欺凌的過來人。於是觀眾對於同一個反轉的設計的第一反應,就變成「我們已經盡了力,你還想我們怎麼樣」、「我明明已表示了站在你這一方,還需要無時無刻去證明嗎?」、「不如一開始就不關心,由得你自己一個,就不會招惹事端」的憤慨。
這其實也呼應了6A班一直針對積極幫助同學破局的楊悅盈,越落力越被誤會,Billy就曾留下一句「勇過你就係鬼呀?」。甚麼也不做,反而安然無恙,於第三集的投票過程間,Elaine/石曉陽已提醒何晞賢不可永遠不表態,豈料到最後一場投票遊戲,竟也因著他不按掣而順利渡過。
「佢哋唔係想講道理,係想搵個人當目標發洩」
不少觀眾認為AI版本的羅彥輝動機無理,與此同時坊間對於周世文這角色有著極不客氣的指罵,及為其死亡叫好。周sir就常聲稱站在學生一方,卻在每一集皆無作為,只講無用廢話,欠缺任何積極行動及思考,而這正可能切合在羅彥輝局限視角下,四個朋友的姿態。於是AI是否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到羅彥輝心底不表露的憎恨呢? 相對Elaine、楊悅盈已是他最相熟的朋友,卻其實也有一定距離,AI 是否有可能比她們更了解真正的羅彥輝?這就回到剛才指AI 不可靠第一點,科學與人性理解的模糊,我們無從判斷,而作品亦沒有再深究下去。
至於周sir幾乎每集都有戲份,但我們好像從沒有認識過他,除了一幕他跟校長的對話,可看到由上而下的管理方針,有份形成他的教學態度。是甚麼促成他在這場危機有如斯拙劣的應對?他在6A班出事前的平易近人形象,是投放了真誠的熱情,還是純粹應付工作需要卻有其敬業的一面?周sir在自己性命倒數階段,動手打何晞賢時,還記得他生涯規劃選科的分享,是其職業本能嗎?我們是否有足夠理據去指控他是「教畜」呢?如果我們認為他「抵死」,跟 AI 羅彥輝認為已讀不回的四人「抵死」,是否同樣片面?最後他是「廢到最後」,敗給時間管理,還是根本沒有打算殺害何晞賢?
按照演周sir的駱振偉在社交媒體直播時所言,他帶著「漫畫化」的演繹,才可解釋他被加入群組前後兩極的態度。當演員都不能相信所飾演的角色為何如此單向地「廢」時,實在反映了劇本並沒有賦予其立體的深度。而「漫畫化」要成立,就要全劇有一致的調性,很顯然幾個主要學生的發展曲線是有路可循,周sir卻是斷裂的。而他是本劇批判偽善無能的主要人物之一,其形塑卻如此單薄,就無法將其對應到現實,無法了解到怎樣的處境才造成這類人的選擇,也就只能淪為情緒發洩的出口。
MTCC最多著墨的Jessica跟周sir的設計有所類近,也是在極權網下處於中間、不受即時影響,或同受壓迫,卻相對地站在較遙遠/安全位置。她比周sir更有幫助到學生的條件,卻不知是劇情使然,還是角色態度主導,總是幫三成,留起七成;表面似很煩惱熱心,實際上卻常拖慢板。有別於原作一直置身事外般冷酷,Jessica變成維護公司利益與親人安危間權衡的「溫和建制」,從不翻桌揭底牌,卻一直暗地調查,干預力度卻看起來極之輕微。
從開首被Ivan削弱權限,到結局似乎於內鬥中終找到奪權契機,到底Jessica 應被視為忍辱負重的「內應」(黑色主調的MTCC總部中唯一的白色),還是將狠下心腸黑化後接手Ivan王國變本加厲?至劇終實仍是未知之數。這樣深藏不露,難怪石曉陽決定至死不原諒,再次申明了最大仇恨源自最親這創作起源的意念。已讀不回比動手欺凌可惡、模稜兩可的Jessica比堅定害人的Ivan更受到劇中人物、劇外觀眾的鄙視。石曉陽與Jessica相隔玻璃窗兩邊的一場戲,正正標示著他們永不在同一陣線的距離。
駱振偉縱不能理解自己角色,也總算找到一套策略去解難;王丹妮則只有尷尬並無從定位,到結局的故事線沒有了弟弟的牽絆,才總算重新掌握女強人的氣勢,而不需被複雜的內心戲掙扎,影響到不知交出甚麼表情才適合。事實上整個MTCC呈現皆屬災難級別,MTCC辦公室場面呆滯拖延的節奏,跟學生那邊的張力,猶如兩個不同的導演/拍攝掌控。
Jessica 到最後儼然變成Ivan第二把交椅,但她卻只有兩個手下,還是豬肉桌三個位置並排坐,以MTCC隻手遮天的地位,竟然節省空間與人手到這個地步?網民常嘲笑這良心企業實在環保,燈也不多開,其實若改成光猛繽紛的佈景,或可能更見反差,而不會像現在視覺上保守刻板。美術組竟然說成本大多花在MTCC身上?學生家中佈置比MTCC有心思也有說服力太多了。對白可能怕涉及太多技術名詞,經常重重複複大量空泛的訊息,例如「你幫我處理/跟進/寫份report」此類無實質推進的內容。若重覆得更極致,倒過來或能突顯內部官僚的荒謬運作,現在則毫無效果。
《那年盛夏》的視野局限就在這裡,面對不熟悉/較多的人物/環境,就會寫/拍得單調,於是愈接近何晞賢世界,其描述就愈仔細,尾段的同路人掙扎也因此特別細膩。陳健朗擅拍豪邁的情義,亦對動作戲的設計更上心,加入了毆打石曉陽一幕,亦完整交代允仔天台殺人一場,於是「四大好人」及洪諾言/Crystal亦比原作有更多記憶點。
在學生裡看到的鮮活流動(率直卻又主導霸凌的Billy、有權力影響欺凌者,同時也與被害者保持關係的Elaine),到了成人世界的刻劃就變得難以捉摸,但明明周sir與Jessica的道德灰色可是一脈相承的。而他們的掙扎若能被觀眾同理,那我們或可以從中發掘現實中更多改變的可能,這其實是劇作最值得探索的一環。
利用影像動作,似乎是陳健朗對於閱讀推理體驗的重心轉移,也就讓《那年盛夏》比《已讀不回死全家》更多衝動,更少冷靜觀全局,無法充份利用既定規則裡的鬥智過程去製造轉折奇觀,也因此要倚靠特別任務去純粹完成推進發展的功能,而並非揭露 AI 更多的資訊。
有好幾場戲似是拍錯了次序,石曉陽應該在「四大好人」打到他倒地不起後,在他們臨走才笑說他受傷的模樣,更易說服同學鎖定目標;楊悅盈在同學發訊息前已講明羅彥輝死了,更是大大削弱同學們仍不理警告照炸羅彥輝的合理性。還有一點,即使是學生的戲份,很多時候對話的節奏也太不符當時情境該有的慌張及混亂,聽完一句後又停頓又再接對白的「演戲」情況於群戲時經常發生。明明生死攸關,怎等到他人不停賣關子都不催促?
架空世界的設計,也使得推想角色行動邏輯變得不可能,因為不清楚其通話程式有何功能,只可被動/抽離地接收,難以主動參與推理。因此原作者想寫柯志恆與石曉陽對決,最後陳健朗卻將焦點轉成石曉陽與賴智勇談情,因前者幾無用武之地(柯志恆最出色的表現只是那種小孩玩惡作劇的快感,幫兩部手機設計對白一場就最傳神),甚至編劇也無法想到讓他們聰明地制定任何有用的策略。《那年盛夏》寫情懷遠高於睿智,而香港的創作往往前者氾濫,後者罕有。
但《那年盛夏》至少在科幻原理一項交出慎密的思考,於談論聲波遙控,連結網絡及通訊軟件上,提供了充分具體的細節,去說明監控科技結合極權管理的無孔不入,可隨時奪取性命或人身自由,其有機會在生活實現的可怕。這不是遙遠的天荒夜譚,看何晞媛送舊手機給弟弟時說會讓他「安心」,再回看過去數年,智能手機怎樣被運用來限制及紀錄一個公民進出特定區域,於畫面上以「綻放如花」去放大效果實在有警世作用。
後記:
我寫這文章時想起《一代宗師》裡的一句話:「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現在香港的創作斷層,在於上一輩精英或減產或北上或無法 / 無意再「說好香港故事」、下一代既是資源所限下,亦是欠缺經歷,往往只能集中「見自己」,當然更差的,是連基本功都未打好,連自己是甚麼都未掌握清楚。
最後兩集播出之後,出現了很多「我們都是何晞賢」的聲音。大概是現在的社會環境,令大家平常太壓抑,太渴望有作品說出自己心聲,《那年盛夏》難得有成熟的框架可以套用。但何晞賢太封閉於自我,太口不對心,流行文化、社群互動卻需要有效溝通的表達,像第五集明明看到柯志恆玩「貪食蛇」,竟只在獨白責罵,而不提示同學。也不求人人去做像楊悅盈這類先鋒,但或許至少可以做賴智勇。
不論從前在學校,或現在處身社會的低氣壓,我自覺更能站在賴智勇的身位。他也被欺負,但他以笑與胡鬧,消解任何惡意傷害。他偶爾會遇到 Crystal 般不願意接受自己的人,但仍不會放棄關心他人,仍願意積極地面對。始終保持樂觀,縱使心底裡如何受傷,都不需自憐,因為無論身處任何境況,只要記得某年盛夏,某地某夜,某杯思樂冰,就能撐住笑容前行下去。
#穿壁引光
(本文轉載自《查柏朗的名單》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chalongl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