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序】《根莖葉花──花墟的記憶與想像》:生死有時,花語綿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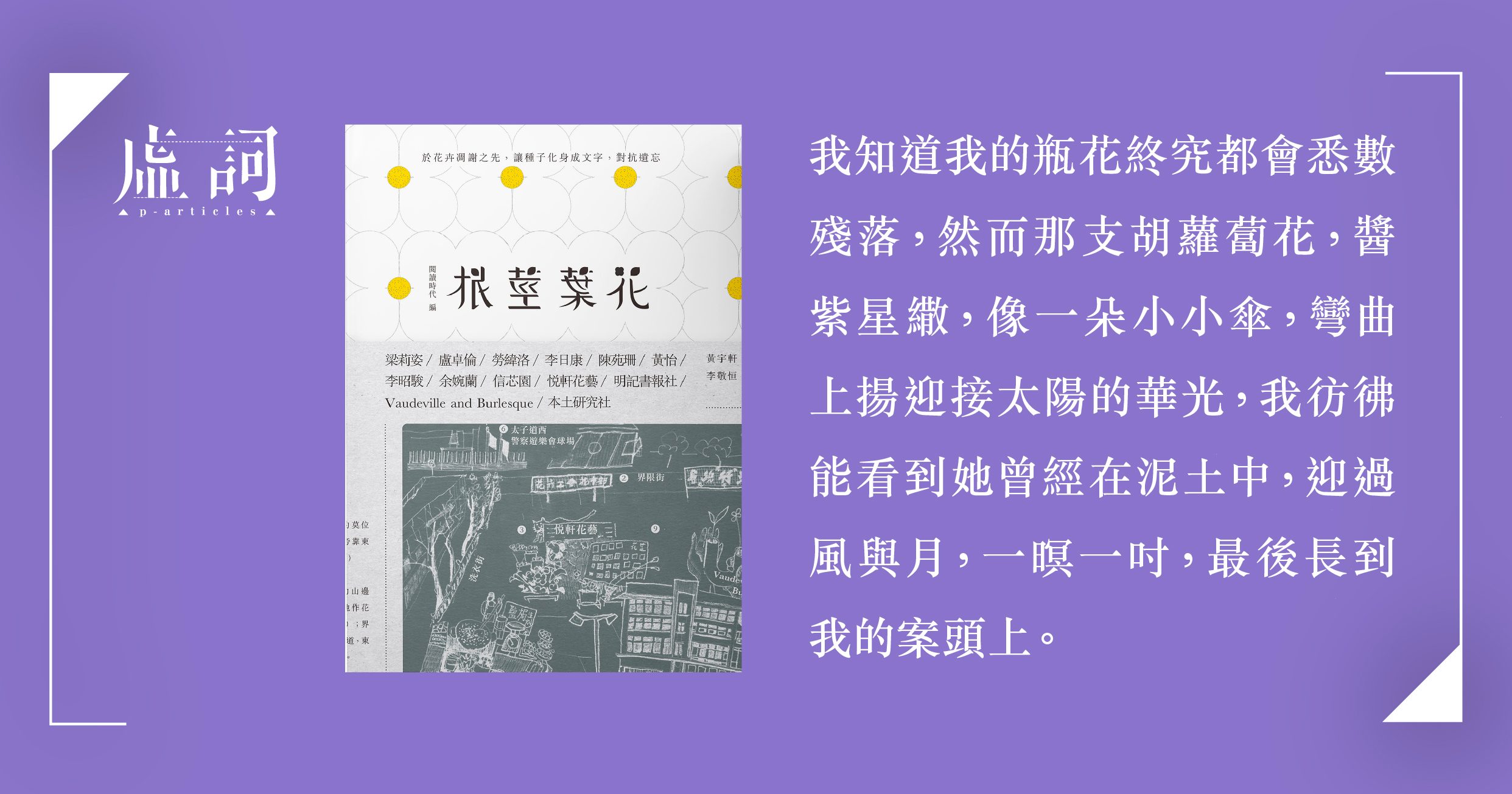
318755165_920629098929960_7900434933399522880_n.jpg
盛夏日子,客廳裡放著的切花一天一天衰敗,本周的瓶花放著朱蕉、鬱金香、桔梗、蠟梅、庭園玫瑰、地榆、小菊、粉雪、胡蘿蔔花、黃花、金合歡與尤加利葉,一大把繁花盛放。我總是以為,一室有花,就能在平凡日子裡平添許些精緻。然而,剪花易謝,鬱金香一晚就凋謝,玫瑰不耐熱,就算每天剪枝換水,還是緩緩垂下了頭,其他的花開到荼靡,散發著濃重的乙烯,一大束花從豔麗到凋謝,不過是幾天之間的事。花瓶從大換到小,一束花慢慢變成一小把,最後剩下幾支最是耐放的,比如菊花,比如乾燥了的尤加利葉。
每日的照護總是讓人神傷,似乎所有的美麗都是那麼一剎。切花不孕育生命,花瓣柔弱,其所有最後都走向死亡,沒有比此更憂傷了。
曾經有一段日子住在花墟附近,深夜便到花墟那一兩間幾乎不打烊的花店買花,抱一把玫瑰回家剪插、除刺,陪伴我的寂寥。後來我一頭栽進花藝世界,想方設法想留住花朵美好的瞬間,我想有許多人都像我那樣,不忍整理必然的殘敗,是以各種乾燥花、永生花,無非都是想留住燦爛。
但鮮花不可取代。尤其在練習插花的日子裡,每次路過太子,都想去花墟走一轉,這樣我才會知道,原來從世界各地來的花在早上十點開始卸貨,前一天賣不完的花按照其衰敗的程度開始減價,從七折、到三折,更慘烈的碩大的厄瓜多爾玫瑰十元十支。
賣不完的花毫無意義。
我曾經見過新界的花農,農曆新年賣不完的蟹爪菊、芍藥、山茶,幾百盤連泥帶盤推上垃圾車,送到堆田區。
《根莖葉花——花墟的記憶與想像》讓我有了不同的維度去理解花的世界——在我教學的時候,我時常拿起一支菊花問孩子,這裡有多少朵花?「一朵」菊花裡藏著無數多的管狀花與舌狀花,許許多多簇成我們所理解的「一朵」,我想生命的有機體便是如此,花墟之所以構成香港重要的地標,無非是其中的微細景貌能折射出一幅更大的圖像,全書考據甚廣,吳卓恆的〈農民告別花墟時〉自然言及香港花市的變遷,從花農與花市的密不可分,漸漸式微、轉移北上,這也是香港整體農業發展在近幾十年的走向。而花墟鮮花的產地,也隨著流行時尚的變動,而越有全球化的傾向,傳統的鮮花大國哥倫比亞、荷蘭自然不在話下,你甚至能在花墟尋得來自北非的花材。
比較起現時在花藝市場大行其道的精緻靈動韓式設計,或是張揚自然的歐式花球,花墟的花藝設計更接近港式平民的繽紛,帶著庶民色彩,大概與花墟的前世今生脫不了關係,吳騫桐的〈界限處的花墟,流變不斷〉爬疏了花墟的歷史,那些萬紫千紅中與中西文化的關係,植卉固然點亮生活的美好,加持喜慶的日子,但花之盛極而喪,在中外也帶有訣別之意,書中屢屢提及西西筆下之花,陳子釧的〈傳統花店的手扎花籃——訪悅軒花藝〉讓讀者一探花藝師趙生趙太以花撫慰亡靈與未亡人的心思。
植物生死有時,離水離根便無法久存,然而花語綿長,梁莉姿、盧卓倫、勞緯洛、李日康、陳苑珊、黃怡、李昭駿、余婉蘭八位文學作家以花寄意,以地貌作敘,在考據與歷史間添足了細膩的情感,一枝花裡看到世界、看到過去,也看到人以花言情,畢竟有時候送花,所求的不過借寂靜之文,傳遞語言之外的各種美意與傷感。
花墟的未來仍是未知之數,近年的活化騎樓計劃,精緻的精品花店與時裝設計進駐花墟,到底會不會成為另一個士紳化的地域,或者像雀仔街那樣被圈劃起來,但植物最讓人嚮往的,不就是其向陽而生,生生不息之姿嗎?
我知道我的瓶花終究都會悉數殘落,然而那支胡蘿蔔花,醬紫星繖,像一朵小小傘,彎曲上揚迎接太陽的華光,我彷彿能看到她曾經在泥土中,迎過風與月,一暝一吋,最後長到我的案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