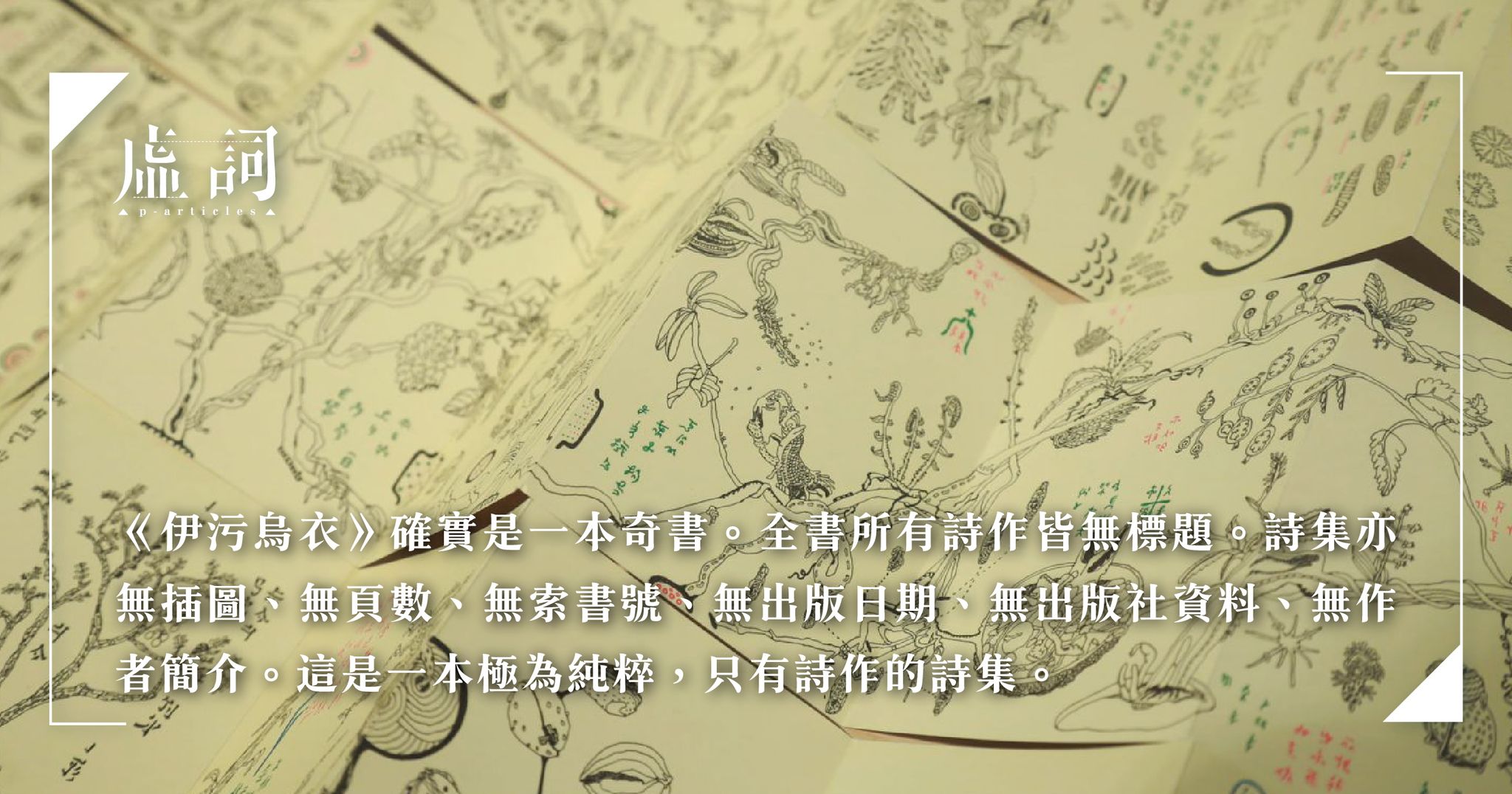香港詩歌激進傳統的暗流———參談:《伊污烏衣⋯⋯》
其他 | by 洪慧 | 2022-01-28
黃燦然於《香港新詩名篇》謂參談其詩其人都非常神秘,有詩集名為《伊污烏衣》,曾在青文書屋出售。除了黃燦然的簡單評介,我還未曾讀到任何文章討論參談的詩作。究其原因,除了是詩風詭秘,不易欣賞,更重要的是其詩集絕難得見,遑論分析評價。林穴回顧展(2021年4月16日~5月7日),展出了《伊污烏衣》,始知參談,即香港藝術家林穴(1968 ~ 2020),本名林峰。
《伊污烏衣》確實是一本奇書。全書所有詩作皆無標題。詩集亦無插圖、無頁數、無索書號、無出版日期、無出版社資料、無作者簡介。這是一本極為純粹,只有詩作的詩集。《伊污烏衣》甚至沒有作者署名。這裡衍生了三個問題。首先,黃燦然究竟從何得知「參談」此名?其次,黃燦然在《香港新詩名篇》的書目中有此條目:「參談《伊污烏衣》,香港:洴看樓,1994。」然則,黃燦然又是從何得知這些出版資料呢?這裡亦當別有故事。再者,觀其封面,乃是「伊污烏衣⋯⋯」,則書名並非黃燦然所記的「伊污烏衣」,而是《伊污烏衣⋯⋯》。「伊」,可以解作「她」,又可以引申為「伊人」、「情人」。「污」,可以解作污垢骯髒。「烏」,在文言文裡可解作「無」,在白話文裡則可解作「烏黑」。「衣」是衣服。四字配合,亦只能強作解人,情人弄污了她的黑衣。又或者是情人弄污了她不存在的衣服。第二個解法比較上新穎有趣。至於第三個解法,則是作者純然將兩組同音字放在一起,構成牙牙學語的感覺。那麼「⋯⋯」就讓人有了一直呼喊這些音節的錯覺。但這個解法只取字音,放棄字義,不及第二種解法,音義俱全。而且全書亦有不少情節,讓極不合理的人事平空出現。故此我傾向第二種解法:情人弄污了她不存在的衣服。然而這樣解法亦只是權宜之計,因為詩集中對愛情的刻劃其實非常少。
《伊污烏衣⋯⋯》的題材不涉政治,全書共二十五首詩作,語言散文化,敍事性極強。詩中不時描寫動物。逃亡,暴力,亦是常見的情節。貫串各種題材的,則是超現實的氛圍。黃燦然在《香港新詩名篇》便選了〈鵝〉來代表參談。這首詩講作者與鵝練習拳擊,雙方拳來拳去。原來在近處看,這頭鵝長著「一張沒有耳朵的小孩子的臉」。這首詩除了與動物有關,又與拳擊暴力有關。而且全詩違反情理,溺漫著超現實的氛圍,黃燦然的選擇是合理而有識見的。從動物入手,更有可能呼應台灣詩人商禽的〈長頸鹿〉。但黃燦然的處理亦有可議之處。觀其詩集,參談並無為詩作加上標題。黃燦然名之為〈鵝〉固然是方便討論,卻未免有僭建之嫌。對詩作比較少干預,而又能方便討論的處理,可以是根據詩作在《伊污烏衣⋯⋯》的先後次序喚之,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如此類推。如以1,2,3等命之,雖然比較簡潔,卻讓人誤會整本詩集是一首組詩。權衡之下,宜採取比較囉嗦的做法。
在無數的動物描寫之間,參談的詩呈現出逃亡、自毀的狀態。且看詩集的第三首詩。
我擠在窗框內。
我往外摔出去,逾越窗外兩支竹杆。
我跏趺,浮騰在空中。
我俯瞰地面。
剛纔的連串動作逆轉回到開始時,然後,又重
新再來一次。
我歡快地沉進持續的凝定裡。
事實上這是一首關於跳樓的詩作。但參談並不是真的寫自己跳樓,而是想象自己跳樓。「擠」的意思,就是窗子很小,但他還是要拼命「擠」出去跳樓,其跳樓之心可謂堅決。於是他終於「往外摔出去」。跳樓對參談然而言就像助跑跳高,「逾越窗外兩支竹杆」。但他並沒有下墜跌死,反而是「浮騰在空中」。參談並沒有解釋這種反地心吸力現象的原因,反而是進一步發揮其超現實風格,「剛纔的連串動作逆轉回到開始時」,再來一次。這個跳樓的過程,對他而言毫不悲傷,反而是「歡快地沉進持續的凝定裡」。參談跳樓的原因是什麼,詩歌沒有交待。我們只知道他非常享受。參談不單在詩中跳樓還有第四首跳船,第九首跳車。且看詩集第九首。
我坐在欄杆上。
身旁有些人。
公共汽車行駛著。
欄杆是汽車的座位。
在飛馳中不停地搖晃。
當汽車轉過急彎,我感到身子被傾側了,好像
要摔出去,於是,我從欄杆上下來。
浪濤攀爬著峭壁又跌下去。
我站在懸崖上,握緊欄杆,眼睛盯著捲疊的浪
潮。
我內心既惶悸,又歡快。
好幾次想著要往外飛跳而去。
第九首的處理和第三首的處理有著相近之處。為什麼要跳車呢?不知道。在這首詩裡,參談確實是在找死。公共汽車的座位,他不坐,而是「我坐在欄桿上」。對他而言,欄桿才是汽車的座位。車子「在飛馳中不停搖晃。」參談已經是搖搖欲墜了。
當汽車轉過急彎,我感到身子被傾側了,好像
要摔出去,於是,我從欄杆上下來。
浪濤攀爬著峭壁又跌下去。
此處極好。原以為他知難而退,終於乖乖坐回座位。才不。原來當他坐在欄桿上,在他眼中,馬路並不是馬路而是洶湧的波濤。公共汽車的車身極高,於是在參談眼中就是峭壁。峭壁極高,浪濤無論如何攀爬,始終還是跌下去,粉身碎骨。整首詩由跳車一變而為在懸崖峭壁前跳海。眼前的絕路反而讓他惶孔又歡快。他必須以極大的耐性才能壓住跳海的衝動。這首詩顯示出,參談詩歌的詩意來自一種完全違反常情常理的情節。詩歌的情節突出,但參談的敍事口吻卻處處提醒暗示讀者,這一切都是日常現實。於是他就會在詭秘的情節中插入一些平凡而簡單的句子,稍為舒緩緊張詭異的氣氛。譬如詩歌開首,「我坐在欄杆上」之後,其實可以直接下去轉急彎的情節。但參談卻先寫「身旁有些人。/公共汽車行駛著。」這種句子既無歧義,又無巧喻,實非好句。但這種日常句子就為著詭異氛圍加上日常的錯覺。明明是不合情理的情節,也就逐點逐點變得順理成章,好像日常般平常。參談不單擁有著將讀者拖進迷幻氛圍的能力,更有著將壞句變成好句,化腐朽為神奇的能力。「我內心既惶悸,又歡快。」這種句子實在是壞句,不但無歧義和巧喻,而且將情感和盤托出,直露淺白。但其特別之處在於,「惶悸」、「歡快」這類情感並不是一般人面對死亡時會浮現的感情。人們對死亡避之則吉,他卻對死亡熱烈擁抱。正因為其感情奇特,所以即使他在這句詩裡用字淺白直露,讀者的目光卻不會立即聚焦於這個缺憾,反而是被他瘋狂的感情所吸引。語言散文化、情感直露,皆是遣詞造句的大忌。但參談是例外。當詩人的個性有足夠特別之處,一切詩家法度都只是旁枝末節。
除了自毀找死,參談刻劃暴力的詩作亦是詭異離奇。在《伊污烏衣⋯⋯》,人和動物互相折磨,動物也會互相殘殺。像第四首(節錄):
一隻老鼠從石縫中鑽出來,又躥進水裡。它的
泳姿很優美;
另一雙老鼠正被猴子追趕著。
岸邊升起一頭龐大的海龜,它揮舞著蛇似的脖
子。
現在,猴子已爬到海龜的頸上。
它獷悍地把海龜的頸往後拉扯,它把整條脖子
撕斷了。
肢體和折斷的頭,安靜地浮在水面。
這首詩寫作者坐船出海。上一秒,參談還在形容海上美景,連老鼠的泳姿也特別優美。下一秒動物之間的廝殺已經隱隱透出兆頭。老鼠、猴子、海龜、蛇互相追逐,貌似童話故事的情節,豈知竟然是猴子「獷悍地」騎著海龜,扭斷龜頸。參談對於動物間的廝殺並不是輕輕帶過。廝殺過後的殘忍現場,他亦仔細描寫:「肢體和折斷的頭,安靜地浮在水面。」即猴子其後還分別扭斷了海龜的四肢。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捕獵求存,這是動物天性,與道德無關。然而猴子的主要食物為水果,吃肉甚為罕見。猴子生活樹林間,海龜在海中生活,兩種動物可謂風馬牛不相及。參談寫猴子殺龜,是全無來由的殺戮,純然的暴力。「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這種儒家的傳統思想,在參談這首裡完全不適用。他的語調就像形容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參談以這種角度去描寫動物廝殺,是「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的殘暴詮釋。天地對世間萬物皆公平,皆平等地以暴烈摧殘。如果一定要為詩歌找一個原因,我只能這樣推論。
有了這個基礎,我們再來看看,參談如何寫人與人之間的廝殺。這是《伊污烏衣⋯⋯》第六首詩。
我把他從門框抽出來。
我忿怒又狂亂。
我和他打架,把他推倒,又撲前去擊打他的膨
脝的肚皮。
而今,他癱臥著,我以最大的力度搯緊他的粗
大的脖子。
他的肌肉失控地、癲狂地抽搐。
我騰升,連同他一起拖上去。
我們分離。
我在一隅默然盯著那變化的軀體。
他陳屍在冷冷的地板上,一束白光往他照射,
而四週黑黑溜溜。
他的雙腿消失了,好像從來沒有長過的。
我盯著那圓滑的下腹。他冉冉浮升,懸定半空
。
連兩臂都消失了。
我看到那巨大的胸脯不斷膨脹、
膨脹,
甚至脹裂了襯衣。
胸脯的陰影投到腹肌上。腹肌像連緜的山脈。
粗糙的黑影藏在肌肉之間。
他完美得像一座鐵彫塑:
堅硬而蘊含力量。
我站在光綫之源,肅然看著他除除往陰森的空
間飄去。
我暗忖:
這就是地獄之門。
要討論這首詩的特別之處並不輕易。首先參談並沒有點明打架的原因。這個「他」是誰?沒有交待。「他」對作者做了些什麼,因而令參談「忿怒又狂亂」?沒有交待。「他」為什麼會躲在門框裡,令到作者要把他從門框裡「抽出來」?沒有交待。參談或者確實有充份的理由把「他」毆打至死,或者沒有。一切都無從稽考。當讀者還在迷霧中疑惑,詩歌已經開始激烈打鬥。參談首先將對方「推倒」,緊接著「又撲前去擊打他的膨脝的肚皮。」對方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但參談並沒有放軟手腳。「他癱臥著,我以最大的力度搯緊他的粗大的脖子。」然後作者再細緻地描寫對方的「肌肉失控地、癲狂地抽搐。」當參談打死了對方後,沒有畏懼、後悔、自責、興奮,而是冷靜、冷酷地觀察著屍體的變化。
或者,我們可以透過對讀類近題材的香港詩作,討論這種寫法的特別之處。對於暴力的思考,在香港詩歌裡,癌石:〈警察〉(1971)最為激進。癌石在詩裡用核子彈殺光所有警察,和他們同歸於盡,「因為他們將我合法地強姦」。癌石亦在後記表明寫作背景是:「給警察打過後/看完「烈火暴潮」後/看完十七期《70年代》後而寫」。因此,就算是香港詩歌史裡最激進的詩人,亦不得不為自己的暴力交出原因,這個原因可以是抵抗殖民統治、可以是捍衞個人尊嚴、可以是爭取自由,但歸根究底,背後一定要有合理、或者起碼能夠自圓其說的原因。若果是單純的快意恩仇,卻在詩裡用上不合比例的暴力,這便顯得道德有虧,然後詩歌就會被扯上作品是否等如人品的討論,沒完沒了。再如淮遠早期的〈賽馬日〉,在詩裡用五色卡車撞向觀眾。淮遠也會在詩裡給出原因,他要拯救被社會剝削的小孩。相比較之下,參談比起癌石更為大膽之處,在於他完全不為自己的暴力提供理由。而且他還要極盡細緻地描寫自己如何虐殺對方、觀賞對方的死亡。香港詩歌中,處理這種狂暴失控的情感,本就不多見,在詩中寫自己痛毆他人更是少見。參談刻劃的狂暴,盛怒,在失控中卻又帶著冷靜冷酷,此即其有別於眾人之處。他的暴力描寫,可說是無視世俗道德成規,絲毫不以讀者為念。
另一方面,他的暴力亦是無視現實邏輯,貫徹其超現實的寫作氛圍。人死後,屍體便會腐朽,根本不會變出紮實胸肌腹肌。參談卻寫屍體的胸脯在死後「不斷膨脹」,各種肌肉之間互相配合,「完美得像一座鐵彫塑」。由此可見,這場虐殺是一次想像。這又隱然帶出,暴力對於參談,不單止並無壞處,更是達成「美」的重要過程。因此,詩中的「他」被作者虐殺後,肌肉才變得有層次和線條,猶如藝術品般,「堅硬而蘊含力量」。參談對暴力的擁抱,因此也就能解釋了他完全不介意讓詩中的動物互相殘殺,在詩裡一次又一次自毀,甚至虐殺其他人了。他就是想看看「地獄之門」的風景。
明乎此,我們便可再讀第二十三首。
她站起來。
她的臉驚人地蒼白,而一對沉溺的眼睛,恍恍
惚惚
四週黑黲黲。
我閃避一個男子,然後,他掉頭逃走。我追趕
他。
他變了一團肉蟲,在敞亮的空間裡。
他藏匿在葉叢之間。
我揭起純粹的葉片,我看到他藏在葉背後。
他又變成一隻麻雀,在空中躞蹀。
他飛進人群熙攘的城鎮裡。
他黏著牆壁。
我舉起獵鎗,子彈穿越沉默的人群。
子彈毫不偏差地擊中他的心臟。
二十五首詩中,這首詩和壓卷之作才有《伊污烏衣⋯⋯》的「伊」。詩歌開首便是「她站起來」,她滿臉病容,「蒼白」、「恍恍惚惚」。三句之後,筆鋒一轉便是「我閃避一個男子」。「她」、「男子」、「參談」三人關係如何?不知道。只有「閃避」一詞指出,這個男子正在追捕參談,對參談構成威脅,因此作者才要「閃避」他。但不過是「然後」一詞,二人已經主客對換,攻守易位。參談反過來變成追捕者。參談完全不打算交待當中大量的空白。巨大的跳躍和超現實氛圍旋即掩殺而來。猶如二郎神追捕七十二變的孫悟空。他由人變成「肉蟲」、再變成「麻雀」。這首和第六首類似。在第六首裡,參談將對方虐殺。在這首裡,參談亦將對方趕盡殺絕。無論他如何逃跑,參談也要將這個威脅追殺到底。
我舉起獵鎗,子彈穿越沉默的人群。
子彈毫不偏差地擊中他的心臟。
暴力不單可以帶來美,更是拯救自我,擊退威脅的利器。於是參談也就「舉起獵鎗」,「擊中他的心臟」。這種毫無憐憫的反擊,以武制暴的思維,不單可以接上癌石、淮遠、邱剛健、還有溫健騮的〈真蹟〉、〈和一個越戰美軍的對話〉。再如第三首,以日常口吻敍述超現實的跳樓題材,可對讀淮遠:〈一個沒有體育精神的人〉。香港詩歌的激進光譜是一條隱而不宣的文學傳統,而參談更是地獄之門下的暗流。在詩歌的敍事風格,參談類近淮遠,以日常口吻敍述超現實題材。在思想意識,參談亦有其特別之處。他的激進立場在於將暴力視為世間運作的邏輯,將暴力視為美的開端,將暴力視為捍衞自我的方法。參談從根本上肯定暴力的前衞思維,此即其在香港詩歌裡別樹一幟之處。
完
2021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