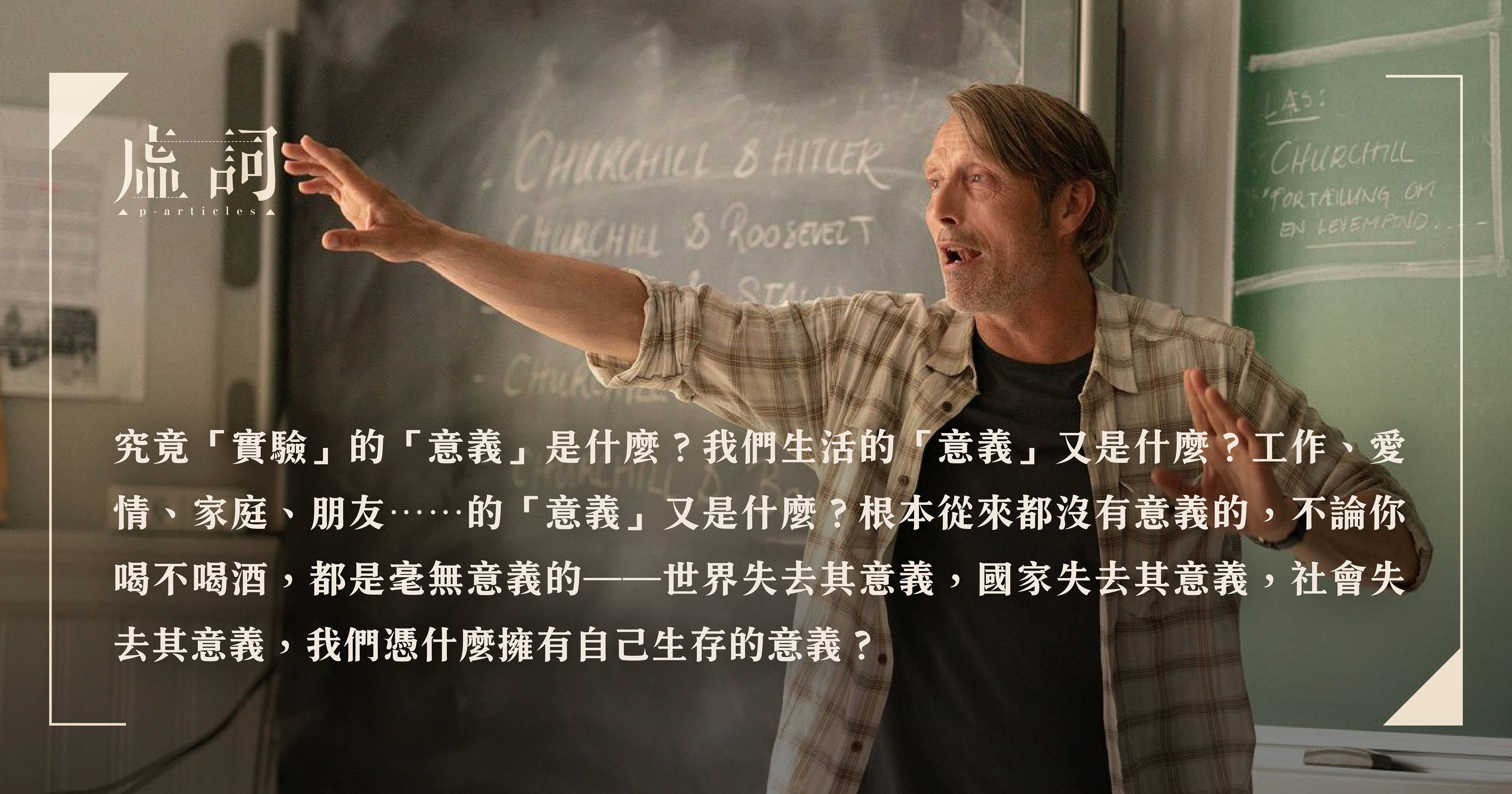懸在半空的Another Round——有關實驗、顛覆與批判
It's okay, it's okay
That we're living, we're living this way
Don't know where I'm in five but I'm young and alive
Fuck what they are saying, what a life
電影以澎湃反叛的丹麥年輕人玩Lake Race鬥喝酒的「傳統」開始,鏡頭來一個男男濕吻,然後陷入亢奮的衝進車廂,把地鐵職員鎖起來,聲畫突然一黑,製作人員片名才慢慢淡出,這時唯一的聲音是一個人安靜往杯倒酒的清脆聲音。這種戛然而止的美麗青春年華、自由奔放,已呈現《醉美的一課》(Another Round)整部片要去表達的主題——世間的歡樂與自由並不會長久,而我們往往寂寞憂愁,需要倒一杯酒,才得以生活下去。片名之後第一場就是校長點名指責學生在地鐵玩得過火——「Fuck what they are saying」,喝酒作為一種對抗規矩的行動,醉酒作為一種不理束縛的行為,酗酒作為一種脫離世事、放棄理性、拒絕正常的狀態。
Another Round之所以受到這麼多人歡迎,或許是因為那種放蕩、真摯而陶醉的感覺在銀幕上很久不見。但我看完後總覺得像最後主角懸在半空,我不知怎樣把整個故事拉回地面——電影完結後,它所實驗、所稍為顛覆的價值觀,好像都只是一直懸在半空。
在Thomas Vinterberg拍攝第一部Dogme 95的電影《家變》(Festen, 1998) 中,各個家人親戚、數十位宴客千里迢迢來到父親一家經營的豪華酒店慶祝父親六十大壽,當所有人都坐好於餐桌前,酒杯都盛好酒,弟弟便用刀大大力敲響酒杯,站起來,拿起杯祝酒,指著生父說起那位早前在酒店自殺的姊姊——她在童年時被父親性侵的經歷。他說畢,坐下,在座有人竟然「冇聽書」的拍掌,一秒後才發現氣氛不妙;但最令我佩服的,是大家假裝沒聽到什麼、若無其事地繼續享用美酒佳餚。之後,弟弟又再起來,指向父親說:「敬這個殺了我姊姊的人。」事情發展至一發不可收拾,弟弟就如一個正在實驗階段的計時炸彈,全酒店裡的人成為了他的人質。電影中,鏡頭不斷跟拍著弟弟神情恍惚的臉,我們卻一直不知道他每次說的到底有多真確,不知道他上一刻和下一刻正在盤算什麼:其實,他每次在所有人面前敲響酒杯,都是一種顛覆「敬酒」、顛覆這班偽善中產、顛覆眼前所有的——「即興實驗」。而這對他來說是必須的、正確的、不得不做的。
即興實驗——Another Round裡,四位白人中產中年直男老師在生日宴會中開始,「即興」決定以維持身體0.05%酒精濃度的飲酒「實驗」,試圖「顛覆」眼前早已枯燥的學校生活和家庭生活。「實驗」在Vinterberg這部2021年奧斯卡最佳國際長片中,去到最後卻是「無意義」的——就只不過是四個男人在白天工作時喝酒,學校家庭生活變得有趣、豁然,慢慢他們喝得爛醉如泥,把生活、家庭關係弄得一塌糊塗,最後放棄「實驗」。他們看似很學術性,有著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等等的名人理論支持其飲酒「實驗」(電影更非常直接地以全黑畫面輸入白色字來顯示Nikolaj每次書寫實驗的論題和成效),實際上是一個「偽命題」——我不肯定這樣說是否準確,但所謂要以「飲醉」來換取生命熱情和幹勁,很可能是個笑話:如果所有枯燥乏味的東西可以靠酒精來變得充滿能量,如果所有關係之中的問題可以靠酒精解決,那麼世界豈不是應該很美好?全球人類一起喝個爛醉後就可以成為文學大師(海明威)、戰爭中的領導者(邱吉爾)、音樂家(Klaus Heerfordt)?導演其實也在問這些問題,也有在批判他們實驗之目的,但整個過程有點流於形式、流於表面。那種關於酒精的狀態變化本應自然而生,在電影中卻顯得做作,或者說,四位任教不同科目老師所產生的變化,真的單純歸功於酒精嗎?有這麼兒戲嗎?
就此,導演或許有意無意地觸及到(但沒有深化)——教育的本質和意義。
究竟怎樣才算是一個有趣、讓學術深受啟發的好老師?教歷史科的Martin喝酒前自己和班上的學生都悶如死屍,他喝兩口酒後教學突然變得生動有趣,而學生竟又突然變得非常投入;教音樂的Peter喝酒後讓學生閉眼、拖手,經驗感受再高唱曲調,學生的歌喉好像突然之間變得很動聽;教體育的Tommy喝酒前是坐在地上向跑步的學生發出指令,喝酒後鏡頭非常生動的表現足球場上四眼仔入球的勝利感;片中教心理學的Nikolaj則只有喝酒前毫無生氣的段落。我與一位做藝術教育工作的友人談論此片時,他直指:「其實一位本來無心教導學生的老師,即使喝幾多酒,他/她都不會變為真正有心去教的。反之,一位本來真正有心教導學生的老師,即使滴酒不沾,也能讓學生學而不厭。」他不喜歡這電影,覺得整件事很無聊而沒有拍出深度。我沒反對他的看法——其實身為人師,不是本來就應該像喝酒後如此熱誠、讓學生投入嗎?為何電影好像要將「喝酒帶來教學熱誠」、「喝酒能激發知識」非常直白的合理化了?(當然導演其後是以批判、反諷的眼光表現Martin和Tommy迷醉地撞到牆上或在校長的會議中倒下來。)當Peter見到Sebastian哭著逃離口試,他叫他喝酒,當他不知道說什麼,又叫他喝酒,然後他就突然表現自如——作為這種戲劇式、虛構性、表演性的電影作品,Sebastian當然可以喝酒後暢談齊克果,但現實真的如此嗎?
如果這電影是一部紀錄片,真實紀錄四個人的飲酒「實驗」,沒有劇本,會不會更「好看」?因為現在整部電影的結構基本上直接得不能再直接,我們都好像只不過在等待這四個男人飲到仆晒街,等待他們因為這樣而停止「實驗」。(從小到大,文明國家社會已灌輸我們「飲酒過量是不好的」、「適可而止」這些事實。回顧歷史與藝術,酒精,一如此片中,只不過是一種極不穩定的催化劑。如煙草、大麻或各類毒品,吸取一些後變得滿胸激情、解放,吸得太多就反之失去激情、解放。某程度上電影竟用了大概三分二的時間來說明這些「道理」。)因為我們從一開始已經知道他們這個「實驗」是根本沒有好結果的,甚至可以說,他們四個人從一開始很可能都已預料這「實驗」是根本註定失敗告終的。(最為明顯的一幕是,當Nikolaj說要提升實驗的酒精濃度,Martin拋了一句「不了,是時候回到家人身旁」,但在他要離開時他受不了那杯中物的誘惑,喝至嚴重宿醉——可憐的Martin違反自己所說的話,應驗了這個「預期結果」,他這時回不到家人身旁了,因為喝太多酒。)
所以說,「酒精」、「實驗」,在Another Round裡也許根本是「偽命題」:「酒精」是整部片的敘事重心,但其實不需要是(導演實在太鐘情於表現美麗好笑的醉意、酒精的多樣性、享用酒精的消閒樂趣、調教一杯美酒的技藝等等);「實驗」是整部片的骨幹結構,但又不會實驗到些什麼,這本來不是問題,導演也有用著批判心態,但其過程實在流於淺薄,沒法推展更多意義。我當然了解,這個「實驗」的真正「成效」,在於停止「實驗」後的一切——如何重拾倒下的自己,如何接受苦難,如何面對愛你、你愛的人。生活日常。這「實驗」來到最後成為「失敗經驗」,甚至促成Tommy的死。Tommy最後在酒醉中往海離去,留下唯一的愛狗。他之前對Martin說過,「不值得的」。「不值得的」究竟是什麼?「值得的」又是什麼?
如果說此電影是以中年男人的角度反思人生,我會覺得頗悶的,其反思並不獨特,沒有對其處身的世界、時代作任何更深層的論述。當然可能他們真的沒有什麼事情可做了:重拾的青春本來就是及時行樂、揮霍無度、頹廢、迷失。他們其實即使醉到盡頭,都只不過是在超市胡鬧、掉進水裡等「好好笑」的行為,都只不過是傷了額頭、瀨尿、被家人學校發現、主角與妻子爭執⋯⋯這些事件在自稱為「世界上飲酒率最高的國家」中根本每天在不同酒吧、不同家庭、不同街道上發生,導演是把這些日常人物的處境心境真誠敘述了,但之後呢?Martin在餐廳求Anika回來,最後在Tommy喪禮後她傳短訊給Martin:「我非常掛念你。」(電影對於配角的筆觸幾乎是純功能性的,如Martin的兩個兒子、Nikolaj的妻子、校長,他們在故事裡的重量太輕,令電影的人物關係弱化。)電影竟然只用了黑底白字的形式呈現他們「復合」的對話和敘事,然後就好像一切將會變得美好、問題將迎刃而解,真的要這麼兒戲地呈現嗎?最尾一幕狂歡,Martin終於放開一切狂舞,飛上天。對,很有能量,很有節奏,但作為一部這個時代的電影,導演真的有新的觀點嗎?
導演有嘗試作出更深的批判:在片中剪入一段各國不同政治領袖喝醉的畫面、醉醺醺地發表演說等醜態。導演似乎要指出:醉酒不是失敗者的墓誌銘;所有人都喝酒,世界也許是由醉酒者建成的。也許,我們的世界從來沒清醒過。
究竟「實驗」的「意義」是什麼?我們生活的「意義」又是什麼?工作、愛情、家庭、朋友⋯⋯的「意義」又是什麼?根本從來都沒有意義的,不論你喝不喝酒,都是毫無意義的——世界失去其意義,國家失去其意義,社會失去其意義,我們憑什麼擁有自己生存的意義?我想,這些問題都是電影向我反射出來,但Vinterberg未曾好好探討處理的。
在Lars von Trier拍攝第二部Dogme 95的電影《白痴》(The Idiots, 1998) 裡,一班沒有心智障礙的「正常人」決定做一個「實驗」:假裝自己是個「白痴」,並聚在一起生活一段時間,以尋找自己內裡的「白痴」,得到解放。他們假裝有心智障礙地滾下山坡、開車撞來撞去、玩一些極「白痴」的遊戲;他們更一起走到餐廳、泳池等地方,周圍的「正常人」以奇異、反感的目光待之,亦有如社會對待有身心障礙人士般被歧視。有一幕,他們在餐廳扮演著時,遇到幾個滿是紋身、很高壯的男人,當他們向一位「白痴」釋出善意,如帶他到廁所、甚至幫他小便,之後,那位「白痴」像被徹底羞辱似的憤怒跑走。另一幕,當他們野餐時遇到一班真正有身心障礙的人士時,他們有人忽然沉了臉色、無言而對——他們發現自己巨大的無知,假裝做的一切原來是那麼白痴,面對真正的「白痴」時被看穿了自己的虛偽;他們在這些人面前只能做回「正常人」,和他們一起笑一起玩,那是他們真正反思所謂「白痴」究竟是什麼。這個「實驗」卻慢慢發展成群體性交、失去目的之放縱。他們之中有個領袖,他決定把「實驗」再推大一點:回到自己的家庭和日常生活裡假裝「白痴」。然後,非常諷刺地,沒有人肯願意這樣做,除了Karen——原來她失去了兒子,這段假裝「白痴」的時間她沒有聯絡過家人,當她在家人面前假裝「白痴」地吃著蛋糕時,旁邊的丈夫一巴掌打到她臉上,與她一起來的Susanne(已做回「正常人」)哭了出來,起來向Karen說,「夠了」,最終她帶Karen一起離開家裡。
Lars von Trier對於「實驗」的使用、過程和效果,在The Idiots中除了是充滿歡樂、遊戲和即興,也同時是充滿黑暗、懦弱和愚昧。電影在整個「實驗」過程中充滿不同意義上的深刻批判性,特別重要的是電影能呈現出這「實驗」放在不同處境裡的效果/反效果,而非單一線性進行的表現方式(Another Round的黑底白字:第一章,喝至0.05%;第二章,喝至0.10%;第三章,暴飲至極點)。這當然與其參與實驗者的背景有關,The Idiots裡的實驗者根本上是置於社會邊緣的「無政府狀態」,而電影以此狀態來建立一種獨特、叛逆、針對固有保守價值的反思和行動。「實驗結果」最終原來是這麼殘酷,又可笑,Lars von Trier彷彿一巴掌打到觀眾臉上,要我們認清自己究竟有多偽善。
容許我稍為比較這三部電影:Another Round的「實驗」應用是虛偽,因為它根本不是電影的核心;但核心的中年危機描寫在整部片一直依賴著「實驗」,這就衍生出問題了。The Idiots的「實驗」目的是虛偽,但它從其應用和過程中產生反複、相對的辯證,成為電影的核心同時,「實驗」者本來的生活藉此拉闊了電影的深度。Festen的「實驗」是最危險、最戲劇性的,因為它就是電影的所有核心轉折點,而「實驗」的發展把處境推向極端,「實驗」終於不再是實驗,而是赤裸裸的證據、告白和表態。
Festen和The Idiots同樣在1998年康城影展首映,Thomas Vinterberg和Lars von Trier作為其中兩位代表Dogme 95的人物,在攝影、鏡頭運動和剪接上已有明顯區別:Vinterberg會刻意晃動、置低鏡頭來營造荒誕感或顯現角色的情緒,會剪進角色回憶碎片;von Trier的鏡頭則沒有靠刻意營造的動作來建立荒誕感和情緒,而剪接非常接近紀錄片。我並不是要說明優劣,而有關Dogme的各項規則其實到底也只不過是一個「實驗」——它雖然無法完整的延續,但它已成為一種滲進往後不同電影的表現方式和風格,兩位導演往後的作品也深受其影響。Another Round的手搖鏡頭、影機運動都是來自Dogme的,但Dogme開始時的那種敘事和形式上的顛覆性,Vinterberg似乎沒有好好延續、轉化、昇華起來。
縱然我認為Another Round是被過譽了,但它也有著讓我回味之處——音樂。除了Scarlet Pleasure青春無敵的What A Life,電影選用從Rococo、Classical到Romantic Period的音樂,也不時唱起丹麥民謠《我出生在丹麥》(I Danmark er jeg født) 。在Tommy的喪禮時,四眼仔領著其他孩子一同唱起丹麥國歌《有一處好地方》(Der er et yndigt land) 。(試想,一部電影能把其國歌如此自然地放進日常的景況和調子中,顯得美麗,真的不會是香港電影——現時香港在私人喪禮奏唱國歌是觸犯了國歌法的喔⋯⋯)畢竟,「國歌」本應屬於人民,而非屬於當權者。
若沒有了這些音樂,Another Round就真的只是一個毫無新意、極為做作的娛樂性片子。在開首晚宴喝酒的那幕,Martin聽到不遠處的合唱團唱著Carl Michael Bellman的Drick Ur Ditt Glas(從你的杯子喝),歌詞第一句已直指酒精與死亡:Drick ur ditt glas, se Döden på dig väntar(從你的杯子裡喝,看到死亡在等著你)。Martin眼泛起淚,拿著酒杯,歌聲掩過對話,他彷彿感受到一種毀滅性的解放,而這種感覺是不能沒有其音樂的——
即使註定被毀滅,也要在毀滅中得到最美的酣醉,得到真正的生活和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