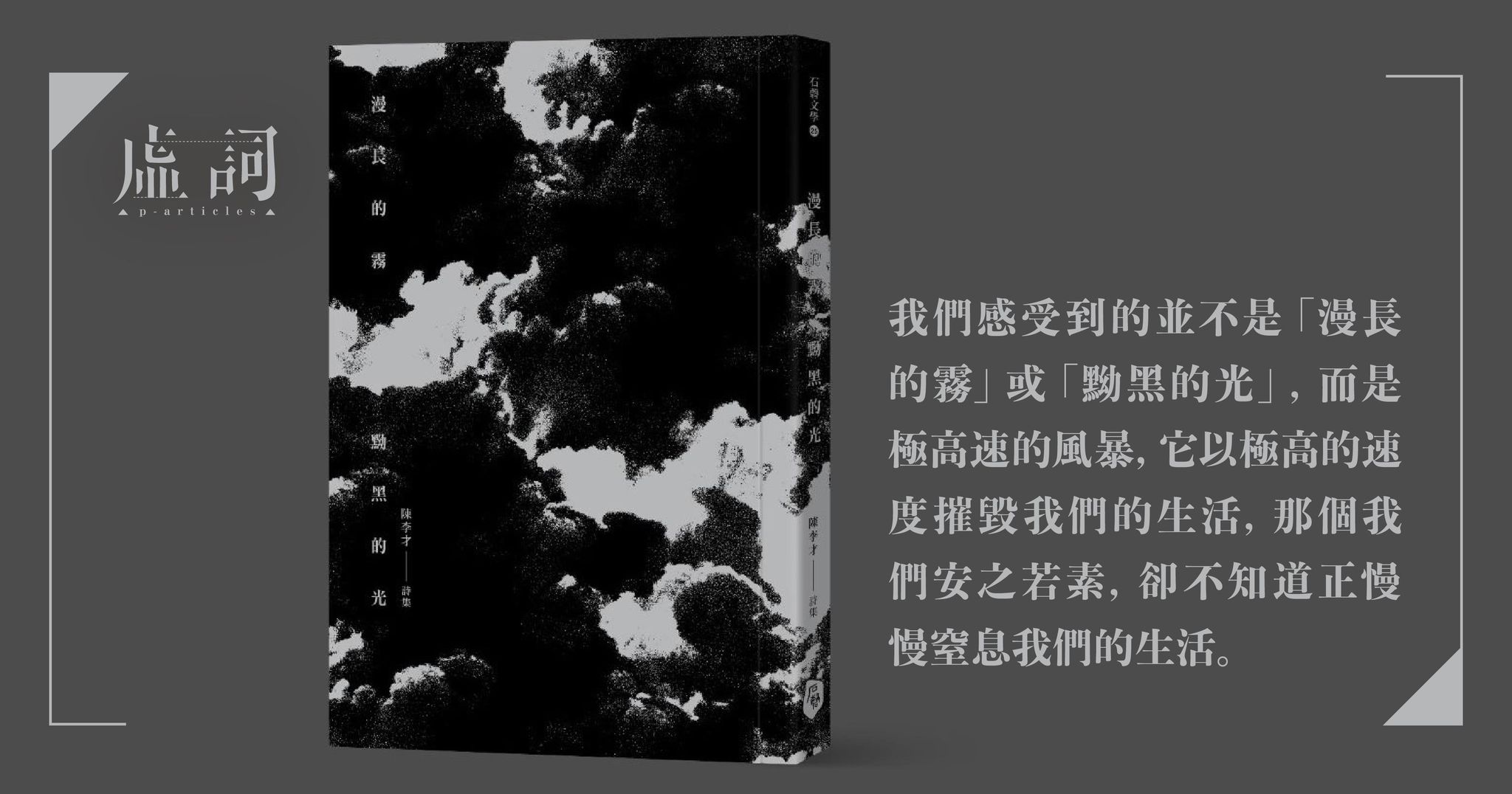從棄樹到鐘聲,或一場風暴的來臨——評陳李才詩集《漫長的霧.黝黑的光》
書評 | by 彭礪青 | 2020-12-21
2019年,反修例運動爆發,警察與抗爭者對峙,然後是風靡全球的大流行病,全城因為抗疫而陷入蕭條。詩人陳李才將他在這兩年寫成的詩,輯錄成第二部詩集《漫長的霧‧黝黑的光》。
關於陳李才的詩,似乎沒有太多評論的空間,因為他的詩並沒有經歷過甚麼探索或預備階段,他從一開始就確定了方向,也很清楚陳李才這個人寫詩意味著甚麼,就像一面旗幟在某個醒目角落的高空中飄揚,絕不含糊,也絕不溫吞。
2017年,陳李才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只不過倒下了一棵樹》,畢業於中文大學哲學系的作者,運用最簡單的文字,表達出最深刻的詩意。不少讀者對典型的香港詩有一個刻板印象,就是詩中必須呈現出紛繁的生活細節,陳李才的題材也來自對現實的觀察,但往往刪去過多的細節,直截了當地道出他的感覺。〈只不過倒下了一棵樹〉寫政府一部門草率地把一棵百年老樹鋸下的事件。本來對於政府,我們都毫無好感,而詩人一開始就道出問題的關鍵,源於我們對生命毫不憐惜﹕
一棵老榕樹多一棵不多
少一棵不少
砍樹的人完成最後的姿勢
這種不憐惜或許源於經濟價值掛帥的邏輯,而且它的存在「佔去了一些(有經濟價值)的空間」,可是,經濟價值並不是由市場決定的,在看似無形之手的市場背後,仍是有一隻追行政高效的有形之手,這隻手會摧毀一切妨礙其發展計劃的障礙物,因為這隻手擁有整個建制的力量,所以這棵樹「對於偉大的東西而言/本來就微不足道」。但這首詩並不在此結束,接著,作者探討了這座城市被略去的冗長身世,想到有些人在哭,但就只有一兩個人。然而他亦領悟到「應該過去的東西/必須過去/應該到來的東西/必須到來」而且「世界有着世界的秩序」,相對這客觀的歷史發展邏輯,個人有個人的日程,而最後,歷史被分成值得被哀悼和不值得被哀悼的兩半,而那不值得被哀悼的一半,「在博物館以外靜靜死去」。
讀者很容易就會想到關於發展、進步與及以此為名實施種種高壓統治的悖論,甚至班雅明在〈歷史哲學提綱〉裡,早就描繪歷史天使所目睹的進步,事實上是一場吹向未來的風暴,這場風暴把過去的碎片堆疊成直抵天際的斷垣殘壁。這些說法都很老掉牙,關鍵是,歷史上的進步向我們的世界索要代價高昂的犧牲,以完成它對我們的承諾,這個承諾所實現的卻是一個殘破、被截肢的世界。
在歷史的進程中先是無價值之物被犧牲,接著是犧牲不涉法律責任的動植物,最後是人,各個族群、團體、階級,乃至整個社會。在他第二本詩集裡,我們依舊能讀出他對人類麻木的描寫,以他慣常那種近乎冷漠的哀嘆語調﹕
灰色椅子
在灰色高牆之下
終於不再轉動
而歷史這樣簡潔——
日光燈年代,他們重覆
坐下,喝水,思考
有如永遠旋轉的硬幣
——〈被棄之物〉
或者描寫風過,行人樹木斷肢或滿地垃圾的無動於衷:
有人如常行走
繞過斷樹
倒下的棚架
許多無法辨認的垃圾
也無法辨認我們
——〈其後〉
灰色椅子是被扔在街角的一個被棄之物,它因為「墜落/使坐墊下陷/無法復原」,而人不單如常坐下、喝水、思考,他們亦只能「沿陰影前行/經過沒有日照的窄巷」,惟獨灰色椅子暴露在日光曬着的地方,在對比以後,詩人最後的形容肯定了這件「被棄之物」比「他們」更有價值的地方﹕它「在灰色高牆之下/靜止,像一個清醒的人」。在讀者心中,灰色高牆或許意味著暴政、體制,或許意味著某些刻板、陰沉、固定不變的結構,也許灰色椅子突然墜落是一種犧牲,或許是一種抗議,可是,因為它存在的狀態,它比任何人都要「清醒」。
另一首詩〈橋〉透過乘小巴的感悟,道出現實世界那種近乎無情的運轉﹕
對岸無臉的樓群
還在構築自己的表情
只要繼續往前
沒有東西將要崩塌
而橋,抖動如常
這種運轉成為它存在的惟一理由,人對它的冷漠不一定來自於無法改變它的無力感,而在於人本身也依靠它的穩定生存。災變既帶來顛覆,也意味著危險,但其實災變一早潛藏在這種現實運轉的邏輯裡,因為現實也是會被風化的﹕
地面開始傾斜
經過工廠,茶餐廳,墳場
直至失去平衡
再次掉進
日久失修的現實
不過這也是人生活在日漸崩頽的現實中的一種預感,預感世界將要搖晃,將會有事情發生(或許期望的事最終不會發生),但現實將會不一樣:
預感一切將要發生
預感一切不會發生
像那時候世界
搖晃,為了不至於倒下
——〈其後〉
但現實終歸會發生災變,對於未來的某種不祥的預感,有時會成為一種有預言作用的詩。這些預感與我們的經驗並不遙遠,相反,它就像遙遙呼應着無數歷史上已經發生的災變,即使我們身處一個截然不同的經驗世界,也不可能抗拒經驗世界以外的「潛力」應合「預感」,把我們認為不可能的「事件」呼喚到現實世界裡。這個世界不是一個to be,or not to be的世界,而是一個潛在事件可能隨時發生的世界,因此詩的想像力才變得有份量,才能像颱風一樣隨時搖憾世界。
而全本詩集分為三輯,每輯背後各自涉及一個「事件」:超強颱風襲港、反修例運動和抗疫,有自然的,也有人為的強權和抵抗者。第一輯雖較多涉及颱風,然後第二輯(涉及反修例運動)最有一種tempesto的氣氛,令人想起馬勒第五號交響曲第二樂章的狂飆暴風。其第一首詩〈鐘聲〉也令人想起蕭士塔高維契的《1905》交響曲,有一個名叫〈警鐘〉(ocsin)的終樂章:
我們都害怕
所相信的,像洋葱般被層層剝開
九月,之後另一個九月
漸忘卻,不尋常的街道
有人跪地而哭,有人徹夜未眠
有人完成陳詞
有人拒絕
落入暴君的手套裡
「休想捏碎,那些看不見的,遼闊的
而又堅實的」
我們聽見漫長的鐘聲
在沉靜夜色之中
——〈鐘聲〉
作為涉及一首政治事件的詩作,〈鐘聲〉的簡潔讓它免於淪為最低層次的政治詩。「九月,之後另一個九月」呼應以後年復一年市民對警察鎮壓行動的記念,記念的目的是不讓自己忘卻那些真正的例外狀態時刻:「不尋常的街道」、「有人跪地而哭」、「有人徹夜未眠」⋯⋯「暴君的手套」本來讓人聯想到一些陳腐的情景,但下一句的「休想捏碎,那些看不見的,遼闊的/而又堅實的」又彷彿是對着暴君作出的吶喊。「漫長的鐘聲」也許亦會成為陳腐的比喻,但整首詩到這裡就戞然而止,留下一串在「沉靜夜色」中,在「漫長的霧」、「黝黑的光」裡繚繞的鐘聲。
而現場發生的恐怖並不是最恐怖的,剎那的血光轉瞬即逝,但它破壞了那個我們習慣的日常世界,日常世界即使慢慢癒合,也無法恢復正常的運作,因為已經無法回到日常:
問題從來不是如何逃脫
而是如何回去
無處容身的日常——橋的另一端
〈橋上的人們〉
「橋上」寓意警民對峙的現場,有催淚彈的軌跡,有死鳥的亡靈,有壞掉的種子,但也有民意彰顯的剎那,正如詩中也籲求守住橋上的當下:「守住橋,守住/一把年輕的聲音/古老的吶喊」,這裡有一個反諷的含義:年輕人的聲音,原來不過是重覆一個古老的吶喊(也許是重覆「五四」或「二二八」時的吶喊),即使是「尚未誕生的人」,也會「把耳朵貼近欄杆鏽蝕之處」,為了更仔細聽見並學習歷史裡的吶喊。
當然,聆聽水深火熱的歷史之聲,最終也只能從民眾的反抗中獲得短暫的幻想,目下的世界,已是一片廢墟,一艘破船,沒有再出發的可能。班雅明的「歷史天使」,目睹進步的風暴刮起,強行把過去時間的碎片,掃進未來。詩人以為時間被定格在這個災變的當下,未來永不到來:「今晨天色特別灰暗/彷彿未來缺席永不到來⋯⋯」(〈入口〉),但班雅明說,來臨中的下一刻,不過是過去時間的碎片化,一切確定之物的形相扭曲,一切堅固的關係變成齌粉,甚至自我亦不可辨認,不可信賴。而這並不只是幻覺:
幻覺,大概幻覺
就像以為樹木是數據燈柱
就像以為麻雀是航拍相機
看著別人眼睛難保不是錄像鏡頭
手機關掉時黑屏如鏡只見自己
臉容扭曲,難保那個人
有天終於告密或背叛
——〈入口〉
如果一切變化、瓦解的速度越快,則根據相對論的定義,時間會變得越慢。我們感受到的並不是「漫長的霧」或「黝黑的光」,而是極高速的風暴,它以極高的速度摧毀我們的生活,那個我們安之若素,卻不知道正慢慢窒息我們的生活。如果詩歌在這場拗手瓜的競賽中能夠戰勝速度,那麼詩就是我們延續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