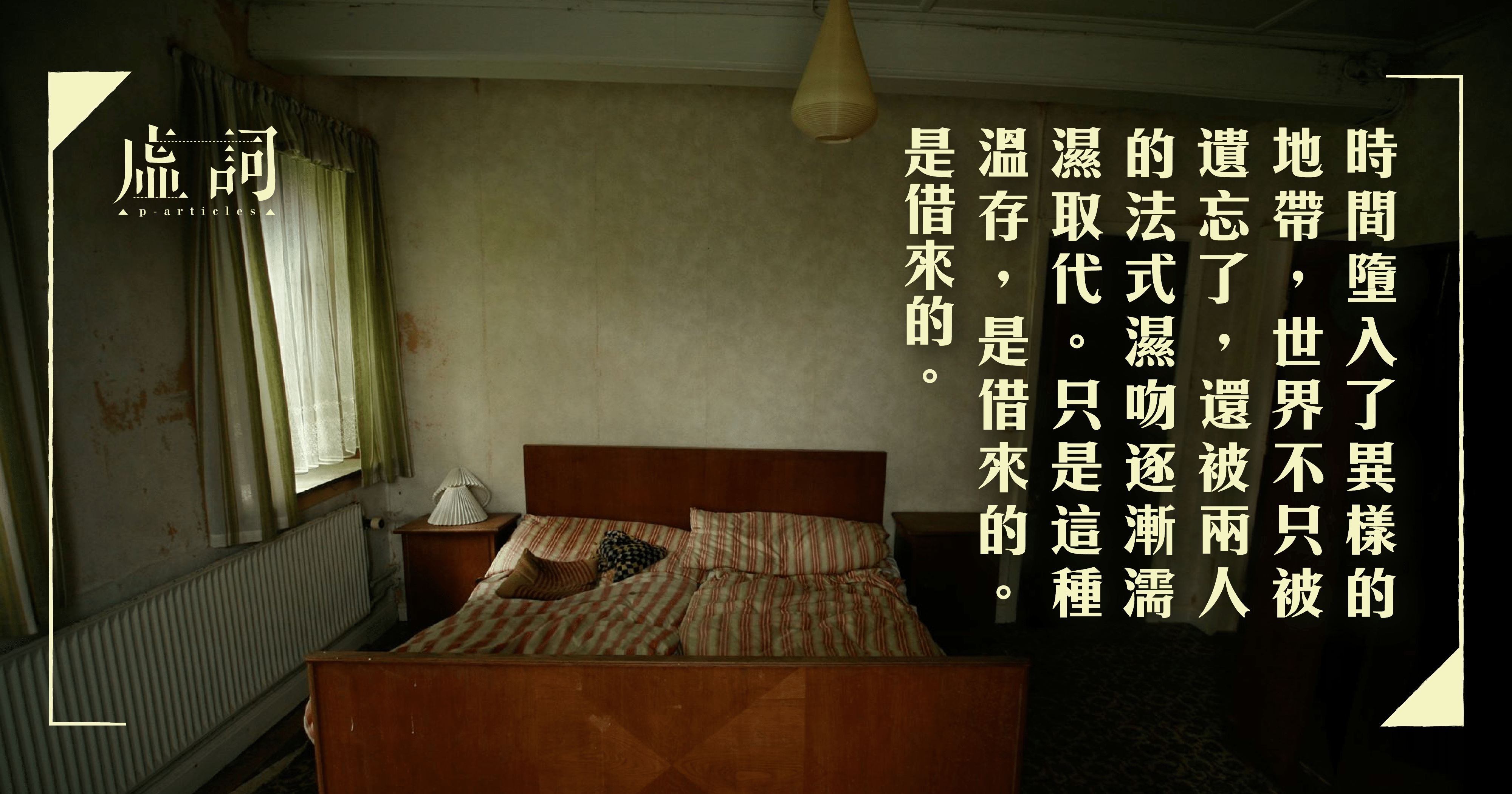【虛詞.酒店有落】酒店有落
1
等了大半個小時,車終於來了。女人先上了車,男人走上車廂後,才把撐在外面的傘收進來。兩人並排坐下來。雨水沿著雨傘流到地面,繞過了男人的黑色皮鞋,在女人紅色高跟鞋的鞋跟聚了一圈,又向不知道甚麼地方流去。雨點不斷打在車頂和車窗上,是因為戴著口罩還是絕望?整個車廂沒有人說話,所有人都像車廂中的幽靈,聽著雨水在乘車。兩個人將注意力放在各自的雨聲上。車子在黑夜中飛馳,成了某人相機中的一道光軌。
「酒店有落。」
2
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新村市確診第一萬宗新型病毒感染個案,確診個案比醫護人員的總人數還要多;病毒致死率三十個百分比,這座城市處於各種意義上的崩潰的邊緣。下午八時零九分,趁著檢疫人員晚飯換更的空檔,寶儀從隔離營中逃了出來,拋下了確診新型病毒的丈夫,轉了幾程車之後,找到了一間叫做佩拉達蘇的酒店,在一個不太起眼的路口矗立著。穿著保護衣的保安從寶儀進門起便一直警覺地看著她。因為不能用自己的身份證租房,她便在大堂沙發上坐了下來,打開手機上的社交程式,急躁地一直滑下去,時間像不規則地跳著倒退。大概誰也沒有想過,情況急轉直下只需要一架二十八座的旅遊巴,和依賴誠實系統的檢疫措施。多少人從此對人類更加深痛惡絕了?
寶儀在對話列表裡看到一個陌生的名字閃過,手指便停止撥動,慢慢滑回去。
兆輝。
那是在兩年前,城市還在製造地獄般高速運作著的時候,在一個叫做「沒有未來的讀書會」中認識的男人。一個月一次的聚會中,寶儀和兆輝永遠坐在桌子的對角,性格也彷彿生在對角,經常針鋒相對,激動起上來,空間便從兩邊對角延伸,連結成一個完全排斥所有人的意念的結界,任你辯才再好也無從插嘴。在聚會外兆輝也常常和寶儀分享喜歡的書的摘錄,她多數回覆一兩句,有時看到有感覺的篇章,便會打一大堆感想,一句接一句想到哪說到哪,毫不修飾。某一次聚會人很多,寶儀的未婚夫亦第一次出席。聚會之後,兆輝傳送了一篇文章的選段給寶儀。寶儀剛和未婚夫回到家中,兩人急不及待的擁吻著,聽到手機的提示聲響,她看了一眼,按下已讀,就把手機丟在床上。未婚夫壓在她身體上的時候,也一併壓住了她的手機。那天是他們兩人最後一次聯絡。
一分鐘後,傳來了「ok」的訊息。十五分鐘後,戴著黑色鴨舌帽、穿著黑色外套、黑色褲子和黑色運動鞋的男人從酒店大門走入來,全身上下只有戴著的外科口罩和手套不是黑色的。兩個人都花了一點時間才認出對方。兆輝沒有多說甚麼,走到櫃台登記了一間雙人房,便把鑰匙交給寶儀,說要幫她預備些替換衣物和食物,便出去了。一上到酒店房,寶儀馬上倒在了雙人床上,疲勞、或者筋疲力盡也不足以形容她確切的感覺,那是像磒石在隊列中辛苦地自轉,圍繞著偉大恆星無力地前進了幾千光年的感覺。她一閉上眼睛便陷入了深沉的黑暗裡去。
雨點悄悄降落在酒店房光滑的玻璃窗上,淅淅瀝瀝的爵士樂逐漸奏起,直至慢慢變調成海頓的驚愕交響曲。一聲狂怒般的雷鳴「轟」一聲響起,寶儀嚇得叫了一聲。她睜開眼,矇矇矓矓看到坐在扶手椅上的一個男人,定睛望了一會,才認出那不是她的丈夫,剛才也不是他的聲音。那是個她已經一年沒有聯絡過的男人,而此刻他們身處同一間酒店房內,隔著三百厘米的距離。雖然兆輝全黑的衣服不太看得出來,但他的頭髮、口罩都濕透了,褲管滴著水。桌上放著兩袋衣物和一份外賣,袋子都很乾爽,只是外賣的飲料漏了一點。
「你想吃東西了嗎?我怕放久了麵會糊。」
「我應該先去洗個澡。」寶儀有氣無力地從床上爬起來,走向桌子旁。
「對喔。衣服在這邊,買了不同的尺寸,你看看哪套適合。我到走廊等你,你好了便......」「別走,好嗎?」寶儀像隻受驚的兔子那樣,銳利地轉身看著兆輝,臉上盡是不知道驚恐還是哀求的神情。他不知道該怎樣反應,過了好幾秒才呆呆地答了一聲:「哦」。
3
「哦。」他說。
「哦。」她說。
「哦甚麼哦?」
「哦就哦咯。」
「你在學我說話?」
「沒有啊。誰叫你整天只會說個哦字。」
「不,說到書,我不會只會哦啊。」
「好像也是。那麼,你最後跟我分享的那一篇摘錄,你有甚麼感想啊?」
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八日,車子顛簸地在上坡路行駛著。城市滿目瘡夷,大概有八成的道路都被憤怒的民眾破壞了,社會幾乎陷入完全的停擺。這條上坡路一共有四條行車線,兩條堆滿了磚頭、瓦礫、垃圾和廢棄傢俱等雜物,另一條則被人用鑽頭在石屎路上弄出了個大坑,伸出來的裂縫像直達地獄深淵。整條上坡路只剩下一條行車線勉強可以讓車通行,不過也沒有多少車在走。
兆輝以突然平伏起來的語調反問。「你呢?」「我,其實還未看啊!嘻!當時好像有甚麼要事,看了兩眼就放下了手機,之後就忘記了。」寶儀調皮地回答著,兆輝一邊聽,一邊微笑著,眼睛像落在了很遙遠很遙遠的地方。過了好一會,寶儀都沒有說話,一直看著街景的兆輝便別過頭來,看到她在看手機屏幕。裡面是他在社交程式裡發給她的熟悉的最後一段訊息。
「以後開始來寫不一樣的小說吧,淳平想。黑夜過去,天色亮起來,相愛的人在那光明中緊緊擁抱,就像有人一直作夢期待已久的,那樣的小說。不過現在暫且必須在這裏,守護這兩個女人,不管對方是誰,都不可能讓他裝進莫名其妙的盒子裏去。就算天塌下來,大地轟然裂開也一樣。
——村上春樹《蜂蜜批》」
「嗯,我沒有看過這部小說喔。」寶儀慢慢抬起頭,眼睛骨碌碌望向上方,像正在一步步走進小說的世界中去探索一樣,兆輝將眼前的景像和在讀書會中遺留的記憶碎片重疊在一起,幾乎完全貼合。「不過,我能夠感受到,主角淳平是一個悲傷的靈魂。悲傷得不得了。但是,悲傷在他身上卻綻放成了溫柔。最無堅不摧的溫柔。」一直仔細地聽著的兆輝,瞬間,他深處的甚麼被觸碰到了,就像大坑不再是空洞,隔離營不再飄滲著慘白,新村市突然轉向,向著和以往完全相反的方向移動著。雖然只有短短一瞬間,但他的眼眶確確實實地紅了起來。自某個奇異的時間點起,他的人生就變得截然不同,好像在活另一個人的人生似的,他已經忘記有多久沒有流過眼淚了。「對,不過還有你不知道的事,這個故事是講述一個錯過了他心愛的人的呆子,終於......」
「市東隔離營自從上個月有與病人緊密接觸者逃離隔離檢疫後,已經加強保安安排。政府發言人指,市東隔離營運作行之有效,有關人士絕不會對社區構成重大健康危機,並呼籲任何有二十八歲女子,馮寶儀消息的市民,盡快聯絡檢疫部......」電台從業員沙啞的聲線沒有透露出一點生氣。
米黃色外牆的佩拉達蘇酒店低調地聳立在下個路口的轉角處,像個謙敬而忠誠的僕人。兆輝和寶儀拿起盛著作為今晚晚餐的蕃茄、蘑菇、意粉和醬料的塑料袋,叫了一聲:
「酒店有落!」
4
二零二零年六月十二日。
兆輝從後環抱著寶儀,壓在寶儀身下的一隻手折了起來,溫柔地放在她的乳房上,另一隻手放在她的小腹,無聲地傳遞著溫暖。酒店房的窗簾為他們擋住了所有飄浮在空中的鉛般的死氣,兩人有默契地帶著對方逃離,一同遁入了某個古老的結界裡去。
「因為這個病毒,現在每個人都不願意跟情人親熱了。你會不會有一天不再吻我了啊?」寶儀嘟著嘴小聲地問。
「笨蛋!這病毒可是會死人的,卻還在想著親吻的事。」兆輝假裝生氣地輕輕拍了她的大腿一下,卻暗自慶幸,在這個癲狂的時代裡,居然還能夠有打情罵俏的平行時空。「不過也是,有誰想得到,政治決定竟然會最終影響到個人的私密幸福?」
「真的!我都已經不知道要怎麼講死亡了,但我一直覺得,即使世界再像地獄,只有有愛,人們便能夠活下去。世界相安無事的時候,有沒有愛反而未必是大問題。但現在新村市卻成了徹徹底底的地獄。你不這樣覺得嗎?」
「你有我啊。」
「你不怕傳染我哦?」
「我應該更怕被你傳染吧,畢竟你不久前才和確診者有親密接觸。」
「我其實和他一段時間沒有接觸。」她的聲音接近聽不見。
酒店房裡靜默了好一會兒。兆輝打著瞌睡,寶儀張著眼睛。
「誒,我跟你說。」
「甚麼?」兆輝有點慵懶地回應。
「我啊,唔......不太能夠處理『愛』。」聲音從背對著他的寶儀的口中說出來,就像從未知地方揚起的語言,聽起來更加脆弱。
兆輝有點醒了過來,問,「那是甚麼意思?」
「就是字面的意思。所以,我希望你也明白。我們都要學好期望管理不是嗎?就像當初我們誰都不應該對這個政權還抱有任何幻想的。否則的話,就不會這樣了。嘻。」她說完了之後爽朗地笑了一聲,雙肩隨著動了一下。兆輝刻意地睜大眼,精神乾巴巴地看著酒店房間的窗簾,試圖讓自己盡快清醒過來,然後想清楚她說的「期望管理」到底是甚麼意思。他現在根本不想去想那個見鬼的政權和更加見鬼的世界。窗簾隨風擺動,投射在窗簾上的窗花的影子跟著變化,牢牢地抓住了他飄泊的意識。
「哦。」結果這是他唯一能夠吐出來的字。
寶儀吃吃地笑,笑得和以往的任何時候都一樣令人窒息。她轉過身來,又將嘴唇印在兆輝的唇上來。時間墮入了異樣的地帶,世界不只被遺忘了,還被兩人的法式濕吻逐漸濡濕取代。只是這種溫存,是借來的。是借來的。兆輝心底裡這個不安的念頭不斷迴旋,直至在空中捲起一陣暖風,把窗簾吹得紛飛。
5
二零二零年九月的某一天。
寶儀的丈夫死了。他和同一天死亡的同營的七個人的屍體放在一起,每具屍體都罩著一模一樣的白色屍袋,像死神在傲慢地宣告著他的最終勝利。印象派畫作、爵士樂、期權、巴黎鐵塔、印章、人工智能、讀書會,一切關於人的東西,終究都變得一式一樣。兆輝從社交程式上,得知了這個消息。他們低調地去到一個,可以遙遠地觀望火化儀式的地方。寶儀看到了丈夫的家人都站在數十米外的鐵絲網外面。他們身上穿的保護衣物明顯不足,附近的其他人的家屬都一樣,像回到半年前病毒剛剛被發現時一樣單薄,他們瘦削得和枯枝沒有太大分別。從她們都指著同一個屍袋哭號,寶儀大概知道哪一個白色屍袋中,裝著她的一部份。
一具接一具的屍體被推進焚化爐。每完成一具屍體的程序,負責打齌念佛的道士便穿著一身古怪的保護衣,在火葬場邊團團轉、潑灑著不知道甚麼液體、大喊大叫。兆輝覺得是他們把地獄帶來了這裡。六具屍體被火化之後,終於輪到寶儀的丈夫。他被推進火葬爐的時候,兆輝攬緊寶儀的肩膊,他早已決定要守護這個女人,就算天塌下來,大地轟然裂開也一樣。只是,沒有絲毫回應。他傳遞過去的能量好像接觸不到任何實體似地、瞬間就散向了空中,讓他產生了極大的眩暈。寶儀一動不動,直直盯著焚化爐上關上了的閘子,直至看到了裡頭的熊熊火焰,火苗還倒映在她死灰的瞳孔上,不斷吐出因為離開火源而瞬間熄滅的火屑。她看到熟悉的丈夫的嘴唇被濃煙蒸乾了水份,變得乾癟癟的;皮膚從每隻手指或腳趾開始向軀干燃燒,她嗅到了濃烈的燒焦的味道;她還想起了惹笑的頭髮著火的卡通人物的影像。那個人就躺在那裡。永永遠遠地。她完全地出了神,直到她突然想起了,在上坡路上看到的下個路口的佩拉達蘇酒店,那個喊「酒店有落」時定格住的四四方方的畫面。暫住的酒店,慢慢凝結成定格的菲林照,讓她覺得有甚麼也同時跟隨著定格,永遠也不會再改變了。
「陪我回酒店。」寶儀雙眼一直對著焚化爐的方向。兆輝看著她的臉,她的雙眼流露某種異樣的堅決,當中有某種從溫柔中催生的不祥暗示。他絲毫介入不了,她的決定本質就是要將他排除在外。
「哦。」結果這還是他唯一能夠吐出來的字。
6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某一天。
熄掉了燈的酒店房,窗簾依舊透視著魅惑的光影,男人早些日子把窗關了起來,因此窗簾不再隨風飄動。男人把還在滴水的傘打開,撐在浴室內,然後脫掉自己的黑色皮鞋,再有風度地為女人脫掉紅色高跟鞋,並換上酒店拖鞋。兩人輪流洗過澡消過毒之後,女人坐在床上,臉泛著酒精持續作用的紅暈,雙眼瞇著熱切地注視著男人。男人從胃底湧出一種難以形容的嘔吐感。他常常以為,世界滅亡之際,必然是充斥著狂歡作樂的這個模樣的男男女女。
「你住在這裡很久了嗎?」女人熟練地打開話題。
「你認為,兩個人擁抱是不是不一定代表相愛?」男人定睛注視著女人,眼神誠懇得任誰也不會怪責他無禮。
女人嫵媚地笑著,「甚麼嘛,怎麼突然說這些。我現在只想要你啊。」女人吸了一口氣,被浴袍包裹著的身體隨著呼吸收緊又再展開,像做愛時身體傳遞能量的律動。
男人依舊冰冷,「即使想守護對方,不論天崩地陷,對方仍然可以不領情嗎?因為她可能根本不需要誰來守護?」
女人看著男人認真的神情,便稍微配合起來。「是這樣沒錯啊,愛情關係向來都需要兩個人的期望一致。」期望,男人想起了一點事。「不過...... 」
男人抱著最後一絲拯救自己同時拯救她的希望問,「不過甚麼?」
「愛情不是定格的,因為愛情也是暫時的。暫時的東西,有暫時的好處,就是它有變壞的可能,也有變好的可能。明白不明白?」
「要怎樣才能變好呢?」
「有時候,起碼得有天崩地陷、赴湯蹈火的覺悟才行哦。就像要除下口罩、親吻明知帶著病毒的情人一樣。哈。那麼,講經大王,你肯過來了嗎?」她扯下了浴袍的一角,露出左邊雪白的乳房,豐滿而富有彈性,沿著乳房底的曲線刺了一朵玫瑰的紋身。
兆輝吸了一口氣,空氣從氣管流過肺葉,激活著數以十億計的外來物。「你快點走吧。」
「甚麼?」女人仍然傻笑著。兆輝轉頭注視放在桌上的一部收音機,那旁邊還有一本貼滿了剪報的筆記本。
「我是帶病毒者。」
兩人沉默了好一會兒。有誰把世界的音量逐漸調低。女人的表情慢慢崩潰,彷彿正在以十分之一的速度慢鏡播放著五官的扭曲,清晰看得到一根根肌肉纖維的拉扯。在她的一片狼狽中,房間變得寂靜無聲。兆輝記憶裡的聲帶在房間裡環迴播放。
「於三月三十一日從隔離營逃跑之二十八歲女子馮寶儀,於今日主動向檢疫部投案。政府發言人表示,事件反映檢疫部工作行之有效,並指涉事女子已確診感染新型病毒,呼籲緊密接觸者盡快與檢疫部聯絡...... 」
兆輝默默在心裡盤算著,整個新村市超過五十個隔離營,她到底在哪裡?他不知道,但他決定過不可能讓她給裝進莫名其妙的盒子裏去。
雨點悄悄降落在酒店房光滑的玻璃窗上,淅淅瀝瀝的爵士樂逐漸奏起,直至慢慢變調成海頓的驚愕交響曲。一聲狂怒般的雷鳴「轟」一聲響起,佩拉達蘇酒店還是一樣靜靜地矗立在那個路口。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