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酒店有落】貝殼
小說 | by 盧真瑜 | 2020-0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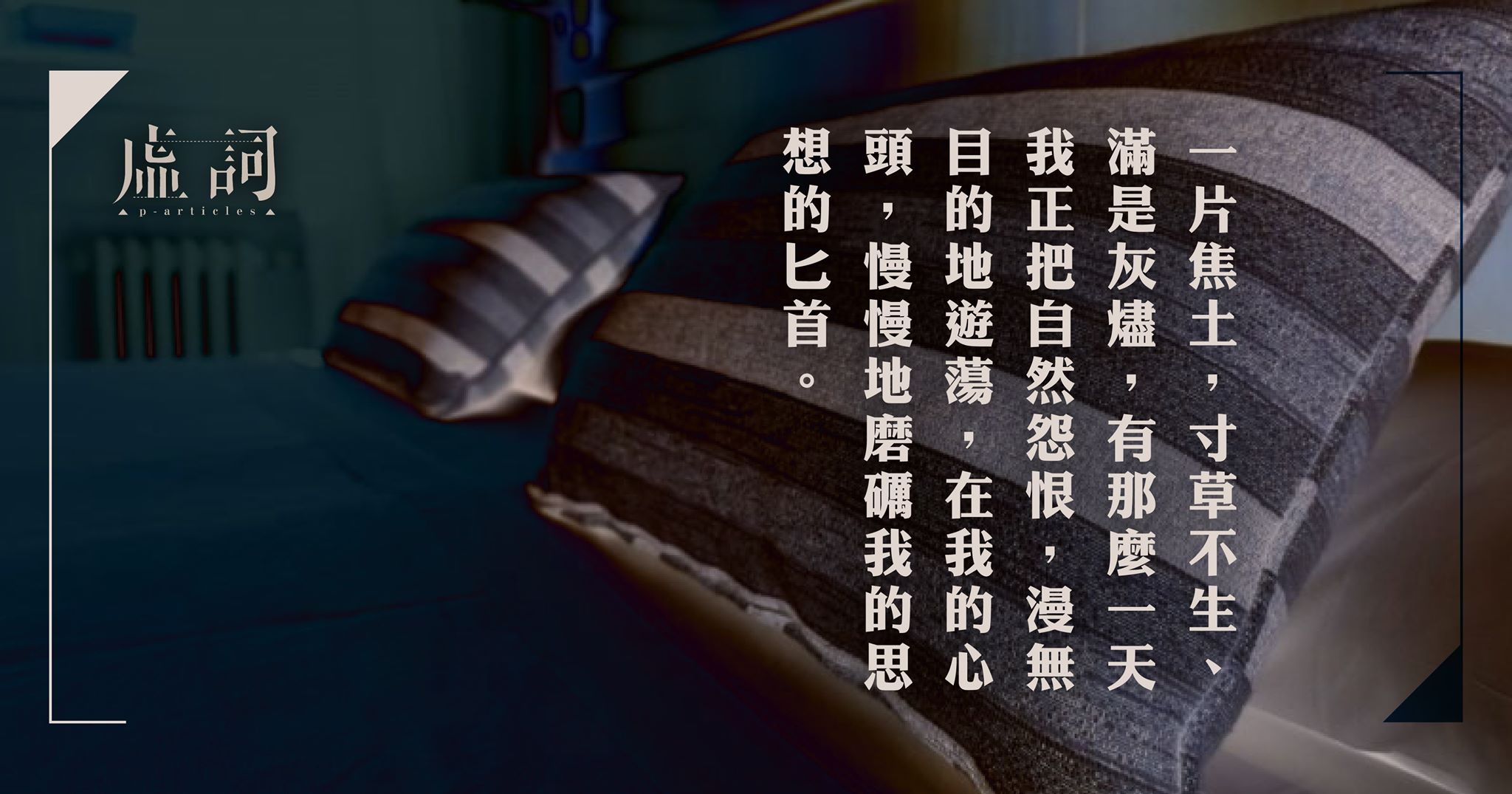
84946347_201142697672044_2575808495773286400_n.jpg
「她也一起嘲笑我陰鬱的痛苦,有時還給它們些淫穢的愛撫。」——〈貝德麗采〉波特萊爾
每次道別後,安都會在酒店大堂裏呆等一會,嘗試觀察這個繁榮盛世裏任何活著而且微笑的生物。她發現,人類的笑容相較犬類更為虛偽,有些弧度上揚很不自然、有些過於柔軟、也有一些堅強得過分。她曾經觀察過八個城市、三十多間酒店,近乎無一例外。除了有一次,香港的半島酒店大門外不知為何彌散著許多煙霧,它們張牙舞爪散在空氣中,彷彿下一秒便會一陣又一陣湧入這所歷史悠久的酒店。
香港半島酒店的大門算不上富麗堂皇,從外表上看來,那高矮不一一如歐陸洋房的米白色格子樓,並非是霎眼可以令人驚艷的設計,但因為歷史、也因為各種對名人的情意結,Peninsula 是香港的 luxury hotel。安是挑剔的,總覺得Ritz-Carlton 那種華美比起半島更為出色,但朋友都不認同她的看法令她有些苦惱。
嘆氣時,絲毫不察覺旁邊有兩位衣冠楚楚的侍應,正以一種挑剔的眼神打量著她。他們站得隨便,身體的重量隨著重心向後傾斜,竊竊私語時的眼睛輕微的咪起,好像在等待些甚麼突發事件發生。
淚水以一種昂然而入的姿態流過,所有人都忍不住瘋狂眨動眼睛,讓刺激、有毒而且過期的物質流出。安也是其中一員,但她忍不住聯想,當精液和性愛同為譬喻,三者的特點是否能夠互通。
*****
貝剛剛在太空館外跑過來,經過急速而且純熟的換裝之後,她與簇擁著的示威者打扮上不再一樣。銀色幼跟高跟鞋叩叩地敲着大堂地板的聲音,令她回想昨天上午她斜斜靠在浴室洗手盤時的表情——滿臉的潮紅在冰冷大理石下急速冷卻——這時跑得氣喘,好不容易躲進大堂的人們,臉色由紅轉白也不過是一瞬間,他們禁不住彷徨失措,再光鮮的表象在這一刻掩蓋不了內裏的混亂。而門外走過的那些人,眼神內含凌虐的笑意,使場景與地位與平日有著微妙的倒裝。
「叩叩」、「叩叩」,又是高跟鞋的聲音,這個清脆的聲音,來自一對昂貴的高跟鞋。酒店職員失去往日鎮定自若的表情管理,他們的眼睛裏滿是恐懼,不再帶有恰到好處的笑容,所以更顯得真實。安很不喜歡酒店職員那種毫不真切的笑容,但卻享受高級酒店無微不至的服務。
「開門啊!」陳經理看着眼前那位穿著限定Jimmy Choo 的女子似乎將要高聲尖叫,他便下意識以最快速度打開大門。讓她和她身後那些人都能夠走到酒店避難的命令,來自一顆長期馴化的腦袋。大部份人都到達酒店後,他又忙不迭地按著那些顯貴的要求把大門關上,以免有毒氣體攻入。老實說,陳經理是典型的香港人,他並不支持藍,但也不支持黃。香港地所有事情都有利可圖,他很清楚自己只是需要大量的金錢才會來到這個金融城市、國際都會。這時一邊推著沉重的大門,他一邊想,以半島酒店的聲譽和主要目標客群的高要求,一但氣體薰到大堂,所有東西都得徹底重換。他這樣小小的一個經理,一個會因客人有丁點不滿意和投訴便要收警告信的小職員,在這種情況下想讓自己脫身並且兩不得罪,聲稱為了保障住客和貴賓安全而把大門關上,便是一個最好的方法。大堂上方的閉路電視,仍然盡忠職守在運作,他知道這將是最為客觀的證人,能令他免於災厄和苦困。
更何況——他隱晦地看了一下那一位坐在沙發上休息的女子,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這位可是一位大人物的情婦⋯⋯
*****
高級酒店最美妙的地方,是你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有這樣的服務。安忍不住拍照留念——眼前兩百平米的套房裝潢華麗,隨處可見的刺繡和花紋,從地板一直延伸到椅子,精巧是這間酒店的第一概念,然而這間房間的名字是奢華。她平日住的也是套房,但是套房不是suites,不是這種光是一個洗手間也比她所租借的地方還大的應許之地。酒店是公平的也是不公平的,安略略將寂寞和慨嘆置放一起,明明是同樣的訂房,為何貝預訂一兩千元的房間,卻能升級到價值四萬多的雙臥室高層套房,而別人卻只能繼續窩在樓下小小的套間?
貝真能幹,只是在短短數年間便創下這樣大的一分家業。
安繼續拍照時,不忘繼續吹捧著貝。她眼含笑意,像一位成熟的少婦,充滿著母性的憐愛。微微側著頭,她鍍金的耳環在髮間若隱若現,認真聆聽貝略有些炫耀的,她和她的形容都像一枚被好好珍藏的鈔票,價值視乎於主人如何訴說它的故事。有時價值連城,有時很容易便棄若敝履。
敝履,或謂之曰,也不過是破鞋。
而貝繼續喋喋不休地介紹,一切彷如未覺。這次帶你來的澳門麗思卡爾頓酒店,以青花瓷為概念設計,你過來摸摸看這一套床品,現在對外銷售應該是三萬多港幣一套。安摸上去,感覺這套昂貴的床具,像是絲滑而柔軟的皮膚質感,和貝那一身嬌貴的美人皮一樣,便忍不住浮想聯翩。貝認識安和安認識貝的時間一樣長,但她們都說不出來她們在何時認識,只記得何時應該適合纏綿。
安的耳環末端綴有一粒温潤柔和的珍珠,同一貝母孕育的另一粒珍珠正釘在貝的耳骨。耳孔在剛釘上去時時常發炎,流出來的血有些紅得艷麗,有些晦澀無言,像淺淺深深的梅子色唇膏。曾經有一次,安柔柔地轉動貝已骨上的耳針,看着鮮血和已乾涸的血塊融成一片,竟然覺得莫名地熟悉,更莫名地令她想流淚。最後她輕輕地吻去耳朵上的血,輕輕地舔著,一如任何一隻落寞而孤獨的母獸。
貝的手慢慢和安的手交疊起來,同樣温軟可人,但安的手柔若無骨,貝的手有些時候卻棱角分明。
你知道嗎?我見到妳時總想起寶姐姐和花珍珠。
為甚麼?
為了我們疲倦的雙眼。
珍珠晃動著,像她們一樣的珍珠,也曾被温暖地包裹在不同的殼裏,那些價格也晃動著。遠遠有一抹雲融入了那一抹雲,它們都空虛,所以具有結實的可能。房間內的空調安靜地蠱惑,令戀戀不捨的貝和安捨不得離去,她們繼續參觀彼此的內部,一如遠處共同染上瑰麗的紅暈。
*****
習慣了暫居在酒店後,安的心態一下子悠閒起來。St.Regis的管家服務再貼心,也只能在一開始令她感到好奇,但在習慣之後,這種每個房間都有一名管家招待的酒店噱頭,其實也不外如是。
安撥弄桌上的鮮花時,總想起貝。窗外的天空澄澈明朗,而安和貝的相識始於微時。她們曾一起去日本旅行,住在便宜的APA酒店,夜裏要輪流整理行李箱。因那屋子太小,小得無法容納她們以外的任何物體。冬天時,她們會窮得只能同時共用一個暖包,放在其中一個人的衣袋,然後另外一個的手就會與她形影不離。她們曾經以冰冷的手指和温熱的手相互取暖,像她們在四季裏共生。
聞說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安便把花冠與花瓣逐一剝下。她知道這裏的鮮花隨時更被替換,所以也無所謂要珍惜。
反正這是住在St.Regis的最後一天了,她百無聊賴地想。貝在做甚麼呢?貝現在還在那裏嗎?如果我看見貝最不堪的表情,她又會有甚麼反應?安知道,她是惡劣的,像任何一朵在泥濘之中長出的鮮花,根系在腐朽的同時也隱隱約約發出惡臭。她不像貝般可以出污泥而不染,在當情婦的同時,仍能保有那種淫穢的天真。
妒忌,她無法否認自己對貝的妒忌,但妒忌於她的同義詞便是,愛。她愛著妖野而純潔的貝,不是對小女孩的憐愛,而是每次對望心臟都會怦怦直跳的愛慕。那一次會面之後,她和貝的情夫有一種無言的默契,她負責滿足並蠱惑她的精神,牽引著她柔軟而仍然天真稚氣的內心,而那個可悲的男人,則必須要在動心的時候適時回到家庭,讓他那位精神有異的太太一無所覺。
隔壁傳來陣陣細碎的呻吟,即使是這種酒店的牆壁也沒有辦法瞞過有心人的耳朵。安想,這時候貝的耳朵應已充血通紅,眼眶盈滿淚水,臨花照水,動人一如往日。但那男人,應該一邊把持不住,一邊拉扯不定,在痛苦的時候感悟快樂,在快樂的時候更感空虛。
好了。這支花的花瓣盡落。安滿意地看著眼前可悲的孤獨的花莖,開始被她在狹窄細長的瓶口中抽插,與隔壁的韻律同步。
繼續、加快、停下,繼續。
坐下、起立、鼓掌、敬禮。
電視開始響起樂聲,不論澳門和香港,在晚間新聞前總會播出國歌:
三⋯⋯二⋯⋯一⋯⋯
繼續、加快、停下,繼續。
坐下、起立、鼓掌、敬禮。
直到一切散場的時候,她才放下花莖,並把它剪成許多小段,連同發黃的花瓣,一起藏在天青色的花瓶深處。
******
一片焦土,寸草不生、滿是灰燼,有那麼一天我正把自然怨恨,漫無目的地遊蕩,在我的心頭,慢慢地磨礪我的思想的匕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