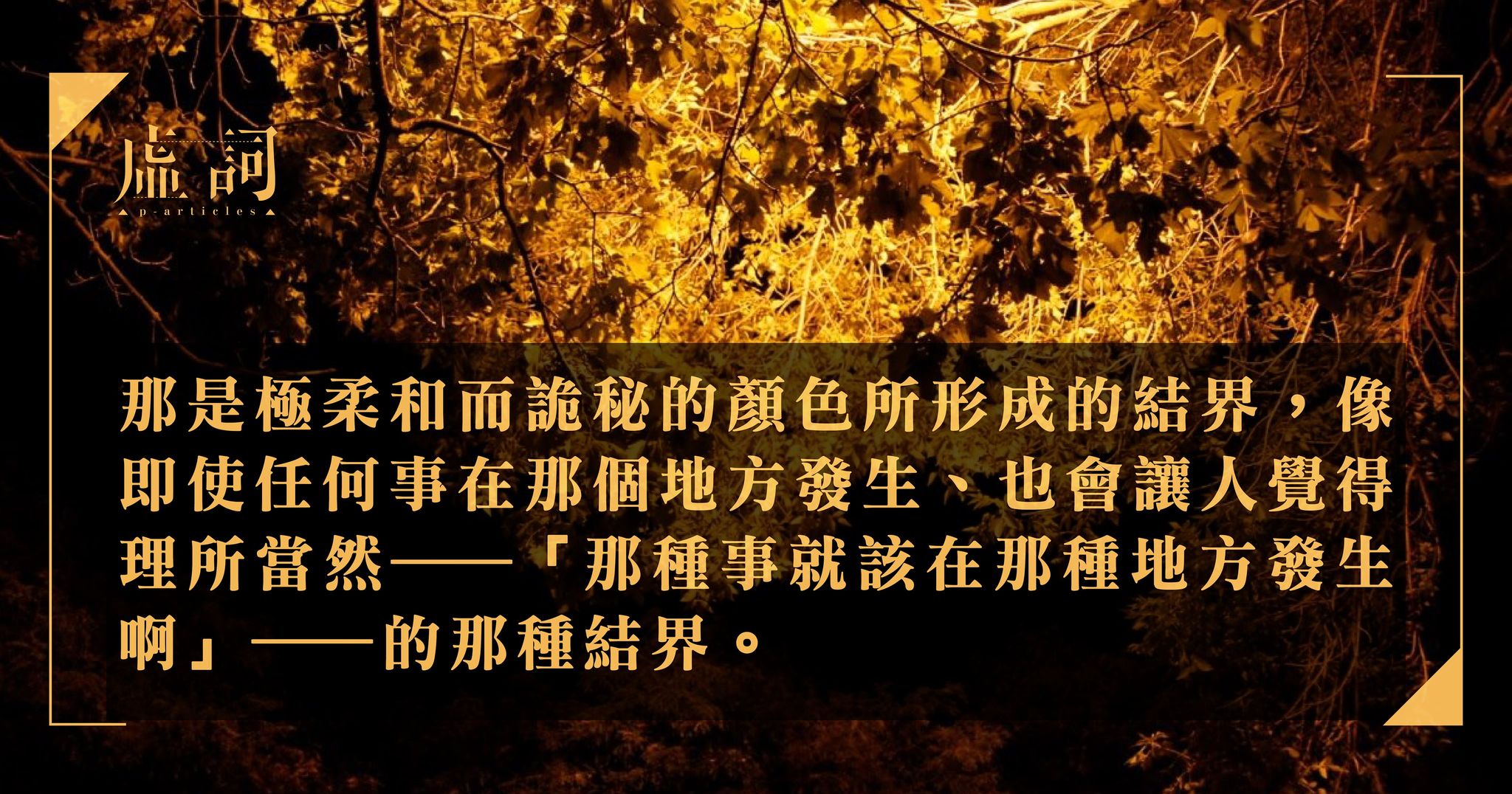昏黃燈光
那是秋原山的山腰的位置。整座山,或者說,整條圍繞秋原山而建的柏油路,就只有在那一個位置有街燈。一到傍晚,整座山就只有山腰位置的那一部份亮起了燈,天還亮的時候是不太顯眼的,天一黑,就只有那一塊的樹蔭和山之靈被照出一片昏黃。那是極柔和而詭秘的顏色所形成的結界,像即使任何事在那個地方發生、也會讓人覺得理所當然----「那種事就該在那種地方發生啊」----的那種結界。像個只投影給孤獨的人的電影窗口。
玲子生命中最後的幾個小時,走到了這個特殊的地點,然後一直沒有走開過。她幾乎甚麼也沒有帶著,背囊只是她習慣了的類似安全感的屏障;裡頭有一本看完了的書----她喜歡文字;還有一包不容易碎開的紙巾----她喜歡乾淨。都是習慣了的東西。這個地點也是她的習慣:每逢失眠而男友又不給她唸故事的晚上,她就會挨著床尾的櫃子,靜靜凝視著窗框中黑漆漆的秋原山中的唯一一點燈光。那種特定的、介乎於黃色與棕色之間的昏黃,輕易而舉地就抓住了她的靈魂,她怎樣看也不覺得累。這些時候,她入睡的方式是每次都一樣的:毫無預兆之下,她的意識會突然中斷,然後沉沉睡去,就像靈魂被山之靈借走了一般。醒來的時候,秋原山又重新是一整座的山,甚麼也不留下痕跡。除了偶爾會有一些奇怪的夢。
玲子上山的前一晚,她的男友因為工作的緣故,不能夠唸故事來哄她睡;玲子看著那片迷矇的昏黃色,直至突然睡著----她發了一個相當奇怪的夢。醒來後,她第一件事便是打電話給男友。
「你聽我說,我作了一個夢。」
「......甚麼?」
「是一個好奇怪好奇怪的夢哦。」
「可是我在上班耶?」
「我知道。可是真的是太奇怪了。我夢到你了。你在夢中對我做種一些猥褻的動作。」電話一頭傳來關門的回音,大概是玲子的男友走到後樓梯或是甚麼其他地方去了。
「唉,可那是夢吧。我可不會無端端那樣做呀?」
「那可不是重點。然後呀,你的生殖器突然迸發出紅色的光,是像針一樣銳利的紅色燈光!你能想像到嗎?生殖器突然像雷達一樣,發出刺眼的紅色光點!」
男友不禁苦笑了起來,「這到底是甚麼奇怪的夢啊......」
「我發了狂,像小貓想要抓住雷射光點般東撲西撲,可始終沒有抓住那個光點。你完全沒有表情地凝視著我,像被亂跳的待宰的鮮魚所吸引了目光一樣的神情,讓我氣得把全身力氣都使出來了。終於,我在某一次跳撲時,落腳點的一片瓷磚憑空消失了,我掉下去了。我一直掉落,並不越來越快,反倒是越來越慢,像掉在水中逐漸減速的狀態,雖然始終沒有停下來。我向上望去,紅色的光點離我越來越遠,像隔著水般逐漸化開,而你的表情完全看不見了。下一個場景,我已經身處布靈頓的海灣上。」
玲子一口氣說完一大輪之後,像突然意識到甚麼似地停了下來,等待男友的答覆。電話另一頭一片寂靜。三秒,五秒,十秒。
「我害怕極了,周遭一個人都沒有,海灣的後頭是陌生的山林,好像隔好遠的地方才會有人。我知道那是布靈頓,是因為海灣上有一堆被海浪捲來的垃圾,當中有一個舊的告示牌,上面的字看不清楚了,下面是"Brighton" 。也許只是從布靈頓漂來的也不一定。總之......那感覺真是可怕極了。空曠、靜止的一片沙堆與自然物,自然以它自己的節奏在行進,那是與我完全無關的節奏,那是近乎於死亡的感覺。我想找你,找不著;我還嘗試找了好多人,但說找,這行動也僅止在腦海中苦惱而已......」
「嗯嗯,然後呢?」男友在最差勁的位置略顯粗暴地打斷。他在工作與女友的來電中兩邊跑,大概也是盡了力才勉強兼顧得了;可對玲子來說,這種斷層的割裂感仍然無比真實。她無法應對這種感覺。
「然後...... 嗯,然後我往回走,走啊走,走到接近山邊的地方有一個洞穴。即使那是看不到內裡深處的一個洞穴,我還是進去了,像是非進不可那樣。那讓我覺得非常、非常的踏實哦,那個洞穴,和它所通向的地方。你明白嗎?」玲子的男友回應了數句,又問更多的詳情,又講他有多麼了解那種踏實的感覺,可玲子只感覺到了孤獨。
玲子在後山發現了一個和她夢境中出現的一模一樣的洞穴。
那是在她掛上了和男友的通話後幾個小時後的事。她到了附近的後山散步,她已經走過同樣的路數十次了,可卻是第一次發現這個山洞,它就像昨晚被藍鬼大王用鐵棒捅出一個窟窿似地憑空出現。玲子站在不遠處凝視洞穴,它確確實實地曾在夢中出現過,連從洞穴頂部垂下來的一根乾枯的藤蔓,都是一模一樣的灰褐色。當第十二個若無其事的鄰居經過之後,好像被驗證過是安全之後,玲子走進了山洞,一直走,走到了那個地方。那是她第一次以這樣的視角去看這個地方,既陌生又熟悉,更像是把記憶托展得更立體。幻想和現實強烈地碰撞在一起,玲子一到達,就像全身心都被溫柔地接住了,像一陣薄膜緊貼住她的每吋肌膚、和需要呵護的內在部份......她覺得自己走進了那個凹槽,那個只屬於她的軀殼的完美凹槽。與其說她動彈不得,不如說她根本不想走。她沒有這樣的需要:她的任務已經完成了。